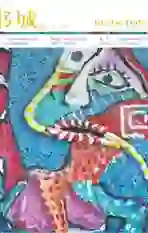刘元:看镜子里的命运
2016-10-12李辉


经董乐山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刘迺元先生。认识他,才知道“迺”是“乃”的异体字。
大约在一九九○年秋天,董乐山打来电话:“我这里来了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你现在有空来一下吗?”我说,好的。我们相距很近,从金台西路报社到团结湖公园,不到两公里,骑上车,直奔他家。
走进董家,一位个子高大的先生站起来迎接我。说“站起来”其实不准确,他艰难地支撑着站起来,我伸出手去握,握住的却是指头弯曲、手掌变形的手。两手相握,我颇有些不知所措。
董乐山介绍说:“这是刘迺元,我们新华社的同事。他看了你写的胡风集团的书,说很想认识你。”与董乐山一样,刘迺元当年在新华社负责外文翻译,一九五七年,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想,这是他读胡风一书感触良多并想见见我的一个原因。
“你这么年轻呀!”这是刘迺元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年,我刚刚三十二岁,站在两位长者面前,的确显得年轻。那一天,我们聊了很多。董乐山告诉我,刘迺元是新华社的右派里最悲惨的人,九死一生。他先后到过半步桥监狱、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北京南郊团河劳改农场、天津清河农场,年富力强之际的二十一年光阴,消磨殆尽,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回到新华社。
之后,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说来我也是与刘迺元一家有缘。刘迺元一九五○年离婚,三十九年过去,他才在一九八九年与虞琴老师结婚。虞琴是著名哲学家、书法家虞愚先生的女儿,巧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曾与虞愚先生有过交往,发表过他的诗,记得他还送过我一幅书法。见到虞琴,谈到这一往事,她也为之感叹:世界真小!虞老师任教八中英语老师三十四年,他们相互恩爱体贴,受尽磨难的刘迺元,终于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宣武门新华社宿舍去看他,与他聊天。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英语。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刘迺元,英文讲得好听极了,他也一直为此而自负。我口语几乎不大会,于是,每次去他会把录好的BBC慢速英语新闻录音带交我带回,那些日子里,每天中午我都会听上一个小时,一边听,一边按照他的方法,将之写在本子上,以此加强听力,增加词汇量。下次去,便念上几句请他指导。无奈年纪太大,南方口音L、N永远分不清,反复纠正也无济于事。刘迺元都是无奈地摇摇头。他表扬我的听力比说好得多,我当然把这作为一种安慰。不过,每天的练习还是有所长进,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到瑞典访问,一个半月的时间,磕磕绊绊的口语多少帮了一些忙,这要算我认识刘迺元之后的第一个收获。
见面多了,总是要听刘迺元讲他的经历:一九二四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五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国共谈判期间在马歇尔军调处任美方翻译,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担任美国国际新闻社(合众社前身)南京分社记者……正是这些经历,导致刘迺元无法摆脱坎坷命运。
一次偶然机会,听他说接受一位美国朋友建议,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此时我正在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策划“沧桑文丛”,便鼓动他不妨改写成为中文出版。他被我说动了。大约用两三年时间,刘迺元口述,夫人记录,中文回忆录终于完成。
拿到回忆录,一页页翻过,我不大爱落泪,有时竟然也难以控制情绪。
平反之后,刘迺元才得知自己为何空有一身好英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多次不被录用,不断被宣布为“美国武装特务”。原来,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他所在地方当局的最初档案里,留下一句要命的话:“为美国通讯社服务期间拥有非法武器。”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在外国人纷纷逃离大陆后,刘迺元租住了一个美国人的房子,里面碰巧有一支没有撞针的废旧三八大盖枪,被司机发现后放在杂物亭子间。就是这把废弃的枪,成为刘迺元非法拥有武器的罪名,尽管当时已被搜走上交,刘迺元哪里想到,它竟然会殃及自己后半生。历史的黑色幽默与荒唐性,就在于此。
这种档案与命运的关联,并非刘迺元独自一人的亲历。君知否,曾有多少人因为档案里的某句不合适的话,厄运从此降临。
被打成右派之后,未曾低头的刘迺元罪加一等,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三十三岁的刘迺元被关进位于北京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
半步桥监狱我不陌生,我熟悉的好几位前辈,“文革”期间都被关押在这里。我写过新闻界前辈刘尊棋的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与薄一波、刘澜涛等六十一人一起被关在草岚子监狱,“文革”期间又被关进半步桥。我写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传记《人在漩涡》,“文革”期间他们先关押在此,然后关进秦城监狱。我写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画传《一同走过》,“文革”五年时间,他们都被关进半步桥,虽同在一处,却彼此不知道。故而读刘迺元叙述半步桥狱中生活,有了更多感慨。
意外地读到音乐家莫桂新的叙述。莫桂新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萧乾介绍后,我曾多次去看望张权,曾一度想为她写传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夫妇从美国归来,曾是歌剧舞台上的明星。一九五七年,夫妇都被打成右派,莫桂新关进半步桥监狱,后来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一九八八年,我曾去过兴凯湖农场,在那里听说过农场发生的惨剧,回来后,与张权谈及。张权去世后,我写过《静听教堂回声》一文,写到他们夫妇的故事。我没想到,刘迺元居然与莫桂新一起关在半步桥,之后,两人又一同发配兴凯湖农场。
在刘迺元的回忆录里,我读到迄今为止关于莫桂新最详尽、最令人心痛的叙述。一九五八年五一节来临,半步桥举办联欢会,一百多位被关押者,第一次集体带着马扎,在院子里坐下,围成一个圈。队长说:“你们知识分子很多是能歌善舞的。谁会,可以主动出个节目,也可以举荐别人。”听到有人说:“莫桂新在这里!”刘迺元望去,看到坐在尽头的一位中年人,他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刘迺元写道:
莫桂新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剧演员张权,享有比丈夫还高的声誉。反右中夫妻双双被划为右派,现在莫桂新在劳动教养收容所,而张权没有被拘禁,大概是因为对女性宽大些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听过张权演的《茶花女》,水平很高。莫桂新的歌声也是大家所熟悉的。遇到他我感到高兴,要不是大家都同样地倒霉,怕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呢。他年纪刚过四十,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头戴一顶蓝布帽子。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在这种环境中被人认出来是有些尴尬的。
一位曾是俄语翻译的健壮的年轻人,率先用俄语演唱一首苏联歌曲:
春天里的鲜花在怒放
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
傍晚在花园里跟我爱人相遇
生活就会立刻变了样
接下来,莫桂新出场:
“我唱什么呢?”他问。接着他自己回答:“这样吧,我也唱这支歌吧。但可惜我不会俄语,只能唱译出来的中文歌词。”于是他用中文唱起同样的一支歌。在这样的场合,像他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是决不会企图去征服听众的;但两个人紧接着唱同一支歌,我们立刻听出专业歌唱家和业余的之间的差距。莫的调子较高,非专业歌手是达不到的;节奏比较快,显然符合歌曲的感情。大家熟悉这支歌;我学俄语时为训练发音,还学会了用俄语唱。但我从未听过谁把这支歌唱得像莫桂新这样好听。他唱出了春天的温暖和年轻的心的跳动。大家都被歌声迷住了。按照歌词他一共唱了三遍,重复一次加快一些节奏,听众的情绪也随着歌声逐步高涨。唱到最后,他重复唱了结尾一句,提高了八度,最后一个音符拖了一下,渐弱下去,然后停住。听众不由自主地静场一两秒钟,然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再来一个!”有人喊,大家立刻高声附和,忘记了这样喊在当时的场合是不合适的。莫桂新谢了大家的盛情,但不肯再唱了。
对刘迺元来说,这恐怕是他狱中生活最难忘的一个场景。不期而遇的人,在那一时刻,沉浸在少有的兴奋之中。
只在半步桥关押了三个多月,同年六月,刘迺元与莫桂新等人,一起从北京发配至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
我去过兴凯湖农场,位于类似半岛之上,只有一条公路与内陆连接,隔兴凯湖与苏联接壤。当年正是中苏关系良好之际,如果有人跑走,苏方会将之遣送回来。刘迺元叙述说,刚到兴凯湖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听到一阵枪声,第二天早晨传来消息,才知道一位难友越过警戒线而被击毙。“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有四十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这句话,刘迺元写得看似平静,内心的波动却可以想象得到。
刚到兴凯湖,莫桂新的悲剧就来了。刘迺元回忆,莫桂新分配在七分场,很快那里传染急性肠炎,也有人说是痢疾。二百多人几乎全部病倒,不少人再也没有挺过来。刘迺元说莫桂新是他所认识的右派中去世的第一人:
莫桂新的病情一开始不甚严重,他和另外几个人被送往总场部医院诊治,这算是特殊照顾。不久以后他感到肚子疼,很快便痛得难忍,医生诊断是肠穿孔,已经没有办法了。遗体火化以前张权赶到兴凯湖,据说她看到丈夫的遗体时悲痛得昏了过去。张权后来住在上海,因为她自己也是右派,不能演出。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年纪大了,不再登台,只做些教学工作。张权一九九三年去世,比丈夫多活了三十五年。她虽然活得长些,但艺术寿命是在一九五七年和丈夫的一起被埋葬了。当时俩人刚过四十,在艺术生涯上像是在盛开之时就被掐掉的花朵。应该说他们的艺术生命都是短暂的。特别是莫桂新,在给予一群不幸的听众一次震撼心灵、永生难忘的艺术享受之后便溘然长逝,这更给他的死抹上了一笔悲剧的色彩。
仅仅两年过去,中苏关系紧张,发配至兴凯湖农场的这些右派们,回到关内,换至天津清河农场,后又转到北京团河农场。刘迺元曾在兴凯湖患过肺炎,几乎丧命,他还一度想自杀,但最终还是挺了过来。如今,他回来了,与他同去的一些难友却长眠兴凯湖。
自从第一次见面,握着刘迺元弯曲的手掌,我就一直想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偶尔提及,他只说是在天津清河农场因自行车车祸造成。读回忆录,我才了解来龙去脉。
历史场景中的人与事,命运捉弄与老天造化,一句话哪里说得清楚?
“文革”期间,刘迺元从待了五年的团河农场又转到清河农场,负责管理葡萄园,与管理桃园的敖松成为挚友。敖松喜欢文学创作,一九五七年开始劳动教养,“文革”爆发后,又将他的手稿抄走,准备批判他,他曾一度想自杀。他们同在一起,交谈颇深,敖松不断讲述自己的失恋故事,刘迺元鼓励他将之写下来。敖松真的开始了创作,并将完成的部分手稿交给刘迺元阅读。岁月难熬,敖松一九七三年最终放弃了生的愿望,两人私下见面,告诉刘迺元:“我要结束了。”这令刘迺元为之一惊:
“我要结束了。”我永远记得他讲这句话的声音和神态。说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地面,脸上甚至略有笑意,声音不高,但那种坚定的调子令我很清楚:一切都完了。
我的心一沉。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我望着他,想继续听下去。他接着说:“我不想再受他们摆布。听说茶淀西村的日子不好过,去了以后又要回到解除以前的状况。我不想再受这个。我厌倦了,厌倦极了。”
那个夜晚,恐怕是刘迺元一生度过的最艰难的一夜。明明知道朋友要自杀,如果报告上去,敖松的结局更惨。直到天明,他一分钟也没有睡。他作出了最艰难的选择:“如果强迫他留在这个对他只有绝望和痛苦的世界上,那才是荒唐的。他想走,就让他不受干扰地走掉吧。敖松信任我,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敖松自杀,留下一张纸条:
第一,我自杀是因为失恋,不是政治原因。
第二,自行车留给大刘(指我)作个纪念。
第三,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不要忘了喝酒,酒可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
第四,收我的尸体时,请拉绳子,以免弄湿你们的鞋。
按照敖松的遗愿,他弟弟要我留下那辆自行车。这个弟弟也是右派分子,在东北农村劳动,经济情况和我不相上下。我听说敖松在世时曾想把自行车卖给一个姓马的,索价三十五元,姓马的还价二十元,没有卖成。因此我和敖松的弟弟讲好,我给他三十五元,把车留下。我当时只能付二十元,余下十五元是下一个月汇去的。
朋友们劝我不要用这辆自行车,说这车是不祥之物,骑它会倒霉的。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说:“我不在乎那些。我已经倒霉到底了,不怕更倒霉。我要这辆车做个纪念,也符合敖松的意思。”
说也奇怪,三年以后这辆车果然出了事,几乎要了我的命。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清河农场的清河中学教书的刘迺元,果然出事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左右,我推着自行车,隔窗向母亲说:“我去找王大夫,时间不会长的。”说着话我忽然发现车把有些不对头。……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我这样做了,一场惨祸就可以避免。但我还是没有管它,骑上车就走了。这一去便再也没有能骑车回来。
忽然我感到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极重地打在我的脸上,那力量大得像是把我的脖子折断了。但它来得极为突然,快如闪电,我没有来得及觉得疼痛,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祸不单行。刘迺元被送到天津人民医院救治,仅仅三天之后,唐山大地震突如其来,医院只接收地震伤员,刘迺元被送回北京三哥家中,听天由命,终于闯过一关。他坦然乐观,谈及自己的这次车祸,与那些地震中走掉的年轻人相比,他反倒为自己感到庆幸。
他的回忆录目录,不断出现“死”:第八章,我没有死;第九章,我又没有死;第十五章,大难不死。
大难不死的人,活到了平反之日。
回忆录的书名最初为《镜子》,一个不错的名字。在镜子里,看一个时代的艰难行程,看一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悲欣交加。不过,出版社编辑觉得以《历劫不悔》为书名更好一些,刘迺元几乎与编辑要谈崩,最后还是勉强地同意用这一书名,其内心当然相当不快。
《历劫不悔》一书,列入“沧桑”文丛第二批,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这一批书目中,还有《在漩涡的边缘》(龚育之)、《青春岁月》(胡绩伟)、《秋风背影》(袁鹰)、《蓦然回首》(徐友渔)等,共十种。在十位作者中间,对许多读者来说,刘迺元是个陌生的名字,但他的回忆录却有着格外沉重的分量,读他的故事,感受一个人的生命力竟会如此坚韧、坚强,在二十一年的磨难中,他从未低头,从未放弃,他依旧仰天长啸!
二○○五年一月,得知刘迺元病重住院,我赶去看他。躺在病床上,他的手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说话也近乎细弱无声。令他庆幸的是,英文版回忆录已在美国出版。书名为“MIRROR”(《镜子》),他的一生,的确是面镜子,为历史存照。虞老师拿出一本,递给他,他用残疾而无力的手,在扉页上为我题写最后几行字:
送给
李辉
应红
刘迺元
二○○五年一月于病榻旁
这一次,我为他拍照,留下最后的身影。
两年多之后,刘先生因心衰于二○○七年九月去世。爱他的虞琴老师,与他厮守十八年,一直守护身旁,他有了平静与幸福的晚年。刘迺元早在回忆录中写过一句话:“我半生坎坷,晚年有了美满的家庭,我的一生算得上是先苦后甜。”的确如此。
今年四月九日下午,我在厦门纸的时代书店做讲座,谈我眼中的沈从文与黄永玉。没想到,虞琴老师来到现场,原来清明时节她正好回到厦门为父亲虞愚先生扫墓,得知消息,放下其他重要事情,特意赶来。在她的故乡意外相逢,我们兴奋不已,拥抱再拥抱。那一时刻,我们共同谈到的是刘迺元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他却一直活在我们记忆中!
写于二○一六年六月三日至五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