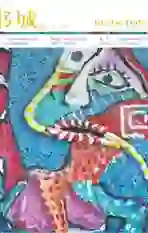《天涯》杂事琐记
2016-10-12蒋子丹


转眼《天涯》改版已经二十周年,《天涯》杂志社在海南博鳌开了一个小型纪念会。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放映了几段前些年媒体报道《天涯》的视频,还配了非常怀旧的音乐。不知怎么回事,当屏幕上刚一出现当年的我们,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杂志,我们的海报,泪水哗地就冲出了我的眼眶,心跳也随之加快。在此之前,我对参加这次会议并未做什么准备,就欣然接受了主办方要求我第一个发言的安排,或许因为我觉得凡是有关《天涯》的往事,点点滴滴都珍藏在自己心头,并且那么丰富和厚重,信口开河都不会无趣,更不会平庸。而且回忆《天涯》,对我而言通常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没有什么障碍,也不曾有什么难度。没承想,这回还真就出了偏差。
一开腔,我就哽咽了,停了好一阵才勉强发出了声音。当时我很尴尬,心里直对自己说,瞧你这点出息!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毫无节制地当众动情……说实话,本人的个性原本不属于婉约抒情派,写出的文字也少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篇章,当下遇到的这一幕,着实让我有点手足无措。这时候,我听到了掌声。
掌声代表着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理解,而期待和理解正是我们在改版之初求之若渴的东西。在这穿越了二十年时光的掌声里,我真恨不能把过往经历的点滴方寸都一一再现,娓娓道来。众所周知,《天涯》的成功改版得益于明确的定位和成功的策划,得益于众多名家的力挺和新锐的加盟,得益于广大读者的青睐和粉丝的追捧,可当这一切将来未到之前,有多少怀疑、蔑视、窘困,甚至是屈辱,横亘在前方等待我们,尚不可知。然而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已经做好了准备,社长韩少功为杂志撰写的改版方案中,这样的宣示可以证明这一点:“《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这样的话语,即使在二十年后,当我双鬓已经斑白,已经远离了所有以工作的名义聚集的人群,还能让我的心闻之而激荡。更不用说在当年,以一个边缘的甚至是弱小的团体,向着泥石流般汹涌而来的精神消费主义大潮,发出抵抗的宣言,那种勇敢和豪迈,那种为人所不为的个性,是如何激励了我,吸引了我。我想,也许这才是我做出放弃自己的写作,去接手这个前途未卜的主编职务的内在原因吧。
不消闲,不娱乐,不求畅销,不追新闻,拒绝低俗……在当时,许多杂志都在艳俗的滚滚红尘之中,为了生存改弦更张被迫易帜,《天涯》如此高调地逆袭潮流,到底凭的是什么底气?显赫知名度,丰厚财政拨款,巨额企业赞助……诸如此类被视为办刊法宝的背景一概没有,凭借的只是一种勇气,一种被某些聪明的同行们所不屑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以《天涯》所处的边缘地境,以它拿不上台面的“出身”,这种宣告似乎有点蚂蚁打呵欠的意思。没人理解,也没人期待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活儿来。
果然,我带着那份尚未实施的改版设想去谈发行,马上就栽了。我通过朋友约见邮局发行部门的头儿,碰了一张不冷不热的脸。人家说,《天涯》我们原先也接触过,完全是一份地摊儿杂志,档次低得很。我被对方说得直脸红,之前《天涯》为解决生存问题想过一些办法,其中也包括卖刊号,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正式出版的刊物默默无闻,卖出去的几期却产生了这么大的“名声”。这让我意识到,杂志现在的处境还不仅只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爆炸期过去之后,当年许多发行量达到上百万份的刊物,都逐渐下跌到了十万份以下。从百万份降下来和从零升上去,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天涯》肯定要经受长时间的低发行量的考验。
改版后的前三期,因为它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质,因为它惹眼的豪华作者阵容,《天涯》倒也在媒体上赚取了少许喝彩之声。这一切并不表示《天涯》已经被市场接受了。一九九六年年底的时候,虽然《天涯》在邮局的订户,在第一年极小的基数之上,上升了一倍多,但在零售方面却受到了很大挫折。邮局零售公司一下子给我们退回了一堆过期刊物,结算的钱几乎为零。尤其让我们不快的是,退回的杂志中,有不少是整捆整捆都没拆封的,另一些经过长途运送雨打水浸已经成了废纸。邮局方面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把刊物办成《海南纪实》的样子呢?像这样办下去,读者不会感兴趣的。面对这种行家里手的指点,我们只能付之一笑,读者不可能成捆购买杂志,我们也不可能在仓库里了解到到底有多少读者真正接触到了《天涯》。原本指望通过零售把刊物送到全国的报亭里去,因此发往零售的份额比订户还要多,而在零售方面邮局与我们的协议为代销形式,剩多少都得杂志社兜着走,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想到要把这些凝结了全体同仁辛勤劳动和期望的刊物都当废纸卖掉,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开辟书店零售渠道,并把一九九六年的一部分退刊订成精装合订本。没想到这两项应急措施,后来竟成了《天涯》的正常业务,导致了我们跟全国几十家精品书店的长期合作,精装合订本也成为每年必须制作的常备产品。二十年之后,与《天涯》合作过的书店因为各种原因生生灭灭,数起来不下百十家了,而如今再想买一本创刊之初的合订本,哪怕是出高价已然一书难求。
发行是杂志的生命线,发行上不去,别的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以《天涯》的定位,它只能通过分散式小批量发行的办法来扩大影响。作为双月刊,它一年只发行六期,每个书店一年下来,卖得再好也就三五百本,到了结算的时候,除去退刊,能收到的款子少而又少,回款就成了大问题。记得那时候,我不管到哪儿去出差,总是带着《天涯》的样刊和账单,为的是找合适的书店设立零售点,或者跟正在合作的书店结账。一九九七年,我到新疆的喀什参加笔会,居然跟那里的一家书店谈了个每期零售二十本的合同,数量少归少,一想到从此连中国西部最遥远的边城都能有人看到我们的杂志了,心里还挺有成就感呢。当然,数量小到了这个等级,结算的时候只能靠店家的自觉,收不回来权当给杂志做广告。对大城市里的大书店,结算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有家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连锁书店,杂志卖得尚可,总爱欠款不结。有次我到北京开会,愣是拿着账单,找到书店老板娘软磨硬泡,非得让她给我当场结算,其实不过区区七千多块。像这样的交道,我跟不少名声很大的书店都打过不少次。既要拿到钱,又还指望人家继续帮你卖,说起话来真好比捧着沾了灰的豆腐,轻不得重不得,好费思忖。
为了减少杂志社的心理压力,韩少功曾以作协主席而不是社长的身份表示支持说,海南作协会倾尽财力帮助杂志度过困难期,他认为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办一份好杂志是最有意义的项目,其他的工作都应该为这个实体服务。应该说,这种宽松的政策在其他兄弟刊物大约是很难争取到的,他们或多或少要跟主管单位为经费的事情讨价还价,盈利的为上交,亏损的为开销。事实上,在《天涯》改版之后的若干年里,海南作协压缩了一切可能压缩的经费,转移支付给杂志,才保证了它在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困境中得以生存。
海南省作家协会是全国作协系统中体量最小的一个,一九八八年建省初期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行政方针,使它的编制受到挤压。主席是实职,每天须坐班,不设专业作家,没有文学院,凡是能写作的机关成员,都是业余作者。经费当然也非常紧张,韩少功身为主席,就算把《天涯》杂志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也不能把扶持本地文学人才的任务弃之不顾。于是他想出许多办法,让作协的经费能一鸭两吃,例如:杂志开笔会的时候,请重点作者们集中开讲座,既满足了刊物的组稿需求,又让本地作者能接触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著名作家和学者,拓宽了大家的视野,同时提高了学养;作家协会的会计,也是杂志社的会计,作家协会的打字员,同时要担负杂志的稿件录入,甚至排版;杂志社有客人来了,主席大人也成了滴滴快车司机,并且一次次站到机场出港处充当迎宾先生……
对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心中明白既然杂志开源的成果需得假以时日,节流的任务已是刻不容缓。于是采取了一些如今听起来似乎过分苛刻,当时做起来却顺理成章的措施。例如,编辑部的三次校样,都用自来稿中的废稿背面打印;外边寄来刊物和稿件的大牛皮纸信封,一律拆开来用作邮购寄书的内衬;样书带来的纤维绳,尽可能接起来再用;凡属于近距离面交的文稿书刊,只用旧信封不用新信封……记得杂志社曾印过一批带LOGO的信纸,编辑们常顺手写个电话号码或记个什么事就一撕一张,想到每张纸的工本费差不多五毛钱,我一再提醒他们这种纸仅限于给作者写信或联系公务。为了节省成本,我们把杂志安排在长沙印刷,这样不光印费低廉,向内地寄运也较为快捷便宜,每期只要将上千册样书运回岛上就行了。那时候火车只通到湛江,要过海,最后的几百公里得另外走汽运,又贵又慢。我听说作协一个理事的家人在邮政局工作,就找她疏通,想请邮车顺便捎带。那理事办通了交道回来问我,一期能省多少钱。我说四百多块呐。她听了眼睛瞪得牛大,这么点钱,还不够喝一次茶呢。
《天涯》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以后,接待任务也越来越重,客人中还有不少名家大腕,并且是远道而来。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法),《白银资本》作者贡德·弗兰克(美),《新左翼》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英),社会学家德里克(美)、斯克莱尔(英)、特本(瑞典),以及国内大部分著名作家、学者,都曾到《天涯》来做客。以杂志社的财力,要维持起码的礼貌和体面都成了难题。于是我们玩起了“小花招”,小型会议多半在办公室开,一来省去了外租会议室的开支,二来顺势让来宾们共进盒饭午餐,也不会太别扭。当然,必要的迎来送往还是需要上饭馆的,如何点菜就成了很有讲究的事情。
记得一九八○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大爆炸的时光,一本文学杂志只要办得好点,发行量随便就能上五十万,再好点一百万大关可破。各省的著名作家们挂着主编的衔,只要出面开开笔会,碰碰酒杯,给老友新朋写个信,带个话儿,也就齐活了。那时候,他们哪里想得到,文学风暴呼啦啦就刮过去了,不过十几年的工夫,杂志主编的工作跟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光得组稿编稿,还得管排版搞发行,并且像个管家婆一样管住每分钱每张纸每个信封。有一次,某报一位记者来采访我,顺便推荐自己的一篇长文给《天涯》(或者两个目的主次正好相反),篇幅不能满足要求,就在报道里编排我。大意是他到达编辑部的时候,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拎着糨糊桶在那儿刷糨糊寄样书,当他知道此人就是杂志主编,心里别提有多失望了,真情愿主编是旁边那个长裙飘逸长发披肩的年轻女士。我看见这篇文章一笑了之,心想谁要是以为在《天涯》做主编,只要潇潇洒洒地跟大咖们聊聊天,风风光光地接受读者的敬意,就大错特错了。《天涯》的口碑是用心血和汗水,用长年累月的辛苦一砖一石打造出来的。作为主编,非得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得给予关注不可。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甚或神神叨叨,都可能是一种常态。而且我相信,一个人无论你的相貌何如,年龄几许,能用自己的劳动实现认定的理想,就是你一生最生动最美丽的时光。
当然,这些边边角角的活儿,实是主编不得已而为的副业。主编的主业不光在于团得住好作者,抢得到好稿件,更在于稿子到了手,能看得准采用,看不上枪毙,不能拖泥带水。采用了还有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大则删文,小则调整字眼,得跟作者沟通默契,不然可能合作了却不愉快,甚至产生隔阂。枪毙稿子看起来简单,好像写封措辞客气的退稿信就一了百了。如果是个好主编,不能毙一篇稿子就得罪一个作者,要做到“买卖不成交情在”,对看准了的作者,须得让人家感受到,不是稿子不行,只是不适合本刊而已,这篇不用了还期待着下回再赐稿呢。只要你的态度真诚,言之有理,杂志又确实办得好,大部分作者都会理解你,尊重你的意见,退稿退出真交情也并非毫无可能。
刚开始的时候,编辑们都很怵退稿一事,尤其怕给自己的熟人“报丧”。有个编辑干脆跟我要求说,他怕枪毙了稿子让作者不服,只好对他们说稿子初审还是通过了,最后被枪毙在我的终审环节。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要求有些可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不想韩社长得知此事之后,不轻不重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他说退稿是编辑正常的职责,你这样无原则宽容这种无理要求,实际上有碍于他们的成长,纵容一种不正之风。我听了觉得言之有理,马上在编辑部收回成命,并告诉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的威信是在退稿的过程中建立的。其实每个作者对自己稿件的好坏多少心中有数,你去夸奖不达标的稿件,然后说可惜被主编给毙了,说不定作者反倒认为,还是主编有眼力。
然而这并不是说,每次枪毙稿件我这个做主编的人就没有任何压力。记得有一回,时任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叫秘长投来一篇散文。我看了以后,觉得放在哪个栏目都不合适,明摆着就是要退稿。在退稿之前,我也很费琢磨,宣传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万一因为退了一篇稿,引得部长同志不悦呢?可要是开了这个先例,《天涯》的纯粹性又如何保证?思前想后,我打算冷处理,瞅准机会再跟他本人面陈道理,可能比生硬的退稿信效果要好。后来在一次小范围会见的时候,我果然有了这样的机会,闲谈中我有意说起《天涯》退稿的一些趣事,他听了说,你的原则性很强嘛。有了这样的评价,他自己的稿被退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后来在好多公开场合,这位被退过稿的部长,还总是帮《天涯》说好话呢。
有位作家跟我是老朋友,在国内外文坛名声了得。有次寄了个小中篇给我,希望尽快安排发表。的确在当时她的小说一直被文学杂志抢着发,她给谁就算是高看谁一眼。可读过之后,我决定要给她退稿,理由是小说虽说发挥稳定,保持了她的一贯风格和水平,但并不太适合在《天涯》发表,因为每期刊物前边是“作家立场”,后边是“理论与批评”,两个栏目都需要用心阅读,故尔我希望借中间的文学部分来调整一下节奏,增强些可读性,再发表这么长一篇文风沉郁的小说,会让读者觉得费力。不出所料,她接到这封信后很是生气,不止一次跟别人控诉我说,没想到蒋子丹现在已经堕落到了只发通俗小说的地步。从此我们基本上断了来往。
《天涯》的编辑大都是文学作者出身,常常各有好稿出手,而杂志社的取稿原则是,编辑们的作品与外来稿在质量上一视同仁,但在同类备用稿过多的时候,外来稿优先发表。那回有位新调入的编辑的中篇小说被取用,而他正是当期的责编。在编辑稿件时,我跟韩少功都曾过目他的小说,并将其中的一些片段作了处理。那编辑很心疼自己被删节的部分,居然在校对的过程中偷偷恢复了原貌。我听到相关的反映之后,先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警告说要是这次删节之后,再行私自恢复,我就要撤换稿件。当时刊物四校业已完成,交付工厂的时间迫近,对方以为我不过说说而已,未必真要撤稿,仍然没有改正。这让我觉得不管不行了。作为刚刚调来的主力编辑,假若第一次当班就坏了规矩,先对自己的稿子网开一面,下次就有可能发展到发关系稿,发人情稿,影响刊物健康的风气。虽说他那篇小说写得的确不错,我还是坚决地撤了下来,并告知他请将这篇小说另投他处,《天涯》再也不可能采用。我想当时他一定很意外,也非常不高兴。但是在几年后他调离杂志社的时候,却对我说:子丹,当时你那么做是对的。这回该轮到我意外了,心里着实还有几分感动。
要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从内心尊重对方,不管是相熟的名家,还是陌生的新人,都一样。《天涯》地处偏远,编辑与作者的交流主要靠通信和电话完成,回信的节奏,意见的虚实,说话的口气,甚至书写的格式,都可以传递截然不同的感觉和信息。有次,一个远在青海的老教师,将她在解放初期与女同学的一组通信,投给《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编辑审稿后决定采用,并且写信通知了对方。没想到这个好消息的告知,反而引来了一封投诉信,信里还附上了编辑信件的复印件。那封信字迹潦草,格式也不对,抬头直呼其名,没有任何问候语。老教师直言道,我真不能相信这样一封信,竟然出自《天涯》编辑之手。社长韩少功收到信后,立即专门为此召开了会议,严肃批评当事人,同时责成编辑部对此类现象全面检讨。韩说,虽说这个作者投稿只有一次,而且很可能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其他的后续稿件,我们也要像对待重点作者一样,充分地尊重人家。这样的信寄出去,是写信人的耻辱,也是杂志社的耻辱,这说明我们的员工教养不够,与杂志社的品格不相符。
会后,我以主编的名义给作者写了道歉信,又要求当事的编辑郑重承诺,在没有练出工整的字迹之前,一律用电脑写信打印签字的方法跟作者联系。
韩少功就此向编辑部提出了许多增进与作者关系的工作要求。比如缩短初审稿件的回复时间,减少备用稿件的留存量,在重要的稿件发表之后,尽可能推荐给各选刊和报纸转载选摘,对有潜力的新人,给予超常规的版面,并组织有威望的名家同时进行推荐。他把这些事务比喻为产品售后服务,顶级品牌都有最优质的售后服务,没有优质的售后服务绝不可能成为顶级品牌。经过这件事,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其实在很多作者眼中,编辑对他们的诚意和尊敬,并不仅仅限于你是否采用了他的稿件,或者是否在目录中排名靠前,以及你对文章评价是否足够之高,而是在你做出这一系列动作时,有充分的合理性。合理了,恰当了,怎么做人家都服气,就算退了稿,人家也会再来,反之,稿子发了头条,稿费也挺高,效果却不一定好。
一本好的杂志,不光要有自己最基础的读者群,还得有相对固定的作者群,这两个群落都需要精心培养和呵护。比起那些财大气粗的刊物,《天涯》的财力肯定相当薄弱。用拼稿费的办法去吸引作者,肯定不是我们的强项,而且我们认为,单纯以稿酬高低决定投稿取舍的作者,肯定也不能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作者。《天涯》的强项首先是它的眼界和包容性,努力使它呈现出对人类社会最尖端问题的关切,并且让这种关切以最有穿透力、最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达。仅这一点就会使真正有精神追求的作者产生兴趣。从这点而言,《天涯》很幸运,那时候国内的学者远不像现在这么风光,拿着课题费到处开会,被媒体记者追得团团转。当时他们一般都很寂寞,对作家们的知名度很好奇也很羡慕。但正是这种寂寞给了他们厚积薄发的可能性,“作家立场”和“理论与批评”这样的栏目,使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学者们的加盟,给《天涯》添上了一道文学之外的思想风景,而且“质优价廉”。
……
二十年转眼过去,倘若不是杂志社组织了这样一个纪念会,我又被安排在会上发言,这些琐细的陈年旧事似乎已被岁月的尘埃遮蔽。那天,在人数不多的会场上,我就那么跟着感觉和记忆,几无逻辑地讲述零零碎碎的故事和细节。我所经历过的选择,以及这些听上去有点傻气的作为,对于在座的青年人来说,是不是有意义,或者说有意思,并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作为过来人,我觉得只要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过往,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释然了。让我惊喜的是,会议结束之后,我听到的称赞之多始料未及,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和学者,对我们经历的艰苦和努力,表现出的惊讶、敬佩和感动,狠狠地温暖了我的心。至少让我觉得,纵然物是人非,我们所有的经历和付出,仍然以它们自有的方式存在着,默默地生长在人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