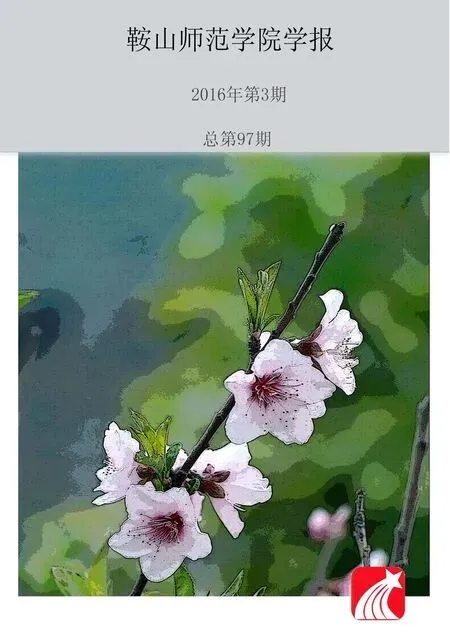明代辽东方志中的社会教化
2016-10-12张晓明
张晓明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明代辽东方志中的社会教化
张晓明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明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大量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等成书刊行。《辽东志》和《全辽志》是辽东地区方志的代表。明代,辽东大部已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一步向边地传播。“化民成俗”“稳固边疆”是辽东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辽东志》与《全辽志》中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流寓等内容,介绍边地实行社会教化的具体情况,阐明辽东文化与中原的相互关系。
明代;辽东地区;地方志;社会教化
教化,一般指代“政教风化”,也指教育感化。《诗·周南·官雎》云:“美教化,移风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并存。统治阶层利用道德教化,维护政治秩序[1]。《荀子·劝学》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强调环境对受教化群体的重要性。在民族成分复杂、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以道教民”“以教化民”对于统治者稳固边疆统治尤为重要[2]。本文通过梳理《辽东志》与《全辽志》中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流寓等内容,阐释了明代辽东地区实行社会教化的具体情况,以期为今天德育教育提供历史借鉴与素材。
一、明代辽东社会及前代社会教化
明朝承袭元疆,先后于东北设置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奴尔干都司。都司下设军事卫所镇守边地。辽东都司有二十五卫、二州,辖境东起鸭绿江,西达山海关,南抵旅顺口,北接奴尔干都司,相当于今天辽宁省大部(今朝阳一带归大宁都司管辖)、吉林东南部(今四平、双辽一带)及内蒙古东部(今通辽、科尔沁左旗一带)。本文中的“辽东”便指上述地理范围。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辽东地区设置郡县,中原人口不断向此迁徙,中原礼教开始影响辽东社会。特别是管宁、王烈避难于此,“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传播中原文化。但其影响仅止于乡邑,辽东“榛狉之风”改变不大[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割据政权不断更替,汉族文化思想进一步向辽东地区传播。融合儒家教化思想的佛教、道教成为塑造辽东社会封建礼教的重要途径。金代以前,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虽数控辽东,但均以军事占领为主,戎马之外没有余力推广道德教化。然而,渤海、高句丽等少数民族颇慕华风,汉学儒家典籍得以大量引入辽东地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辽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创制文字,推广中原文化,儒学影响日益加深。元代史籍未见辽东礼乐教化的记载,但我们从《辽东志·建置》中依稀可见辽东教育的发展状况。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辽阳行省正式设立,辽东地区儒学、医学、阴阳学等渐具规模。黄庆二年(1313),元仁宗设“辽阳行省儒学提举司”,辽东地区官学、私学繁盛一时[3]。地方有德望者积极创办私学,使“长幼皆闻孝悌忠信之言”[4]。元代辽东地区传统教化体系已粗具规模,佛、道文化广泛传播,辽东“雄蓝巨刹,楼阁相望;家庠户序,学校如林”[5]。
明代,为防止行省权力集中,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理一省之民政、司法及军事。辽东因地近胡虏,仅设军事卫所,不设州县。民政、司法事务划归山东布政使司和山东按察使司管辖。都指挥使司为辽东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其军事防御功能居于首位。明军于洪武四年(1371)进驻辽东,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代,约60年时间,辽东战略防御体系形成。辽东人口以卫为单位,明初约有50万[6]。辽东地区的军民围绕卫所、堡寨、墩台等军事据点筑城设防,形成规模不一的城镇与村落。《朝天录》中,朝鲜使臣渡过鸭绿江以后所见城镇多为军事卫所及驿站、递铺,村落分布在城堡周围。明代中后期,辽阳以西至山海关一线城墙、墩台、壕沟等防御设置增多。五里置一烟台,台下有小方城;十五里置一小铺,三十里置一大铺;居民在城旁垦殖,城子渐广而人居者渐众[7]。明代中期以后,明廷政治环境恶化,辽东地区屯田遭到破坏,边患日益严重。例如,成化时期流民运动对辽东产生巨大的冲击;以“高淮乱辽”事件为代表的豪强剥削与奴役使辽东军民大量逃亡;嘉靖以后女真、蒙古族对辽东凤凰城、汤站、叆阳、通远堡、甜水站、广宁卫、锦州卫、宁远卫等边地大肆劫掠。简言之,明朝后期,赋役加重、征索无度、少数民族侵扰等因素,使辽东地区人口不断下降,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辽东志》与《全辽志》成书以前,辽东地区边静无警、土地丰腴、居民生活丰足,为社会教化的推广提供了条件。
二、《辽东志》与《全辽志》中的社会教化
正统八年(1443),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等修《辽东志》9卷,分别为地理、建置、兵食、典礼、官师、人物、艺文、杂志以及外志。嘉靖十六年(1537),左佥都御使任洛巡抚辽东时续修《辽东志》,此版本流传至今。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使李辅因《辽东志》“舛讹脱落甚多”,开馆重修,改名为《全辽志》。《全辽志》较《辽东志》在内容上有所删减,在纲目上进行了重新更定。具体来说,《全辽志》“增嘉靖十六年(1537)以后之事迹”,与《辽东志》命名虽异,“实即辽东志第三次刊本也”[8]。本文选取《辽东志》与《全辽志》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一方面因其为记述辽东整域的通志;另一方面因其成书年代为嘉靖朝末期,书中收集了辽东边患严重以前社会稳定时期的珍贵史料。
(一)明代辽东地区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
据《辽东志·建置·学校》的记述,明代中期辽东地区的儒学教育体系已基本完备。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于辽东设置都司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金、复、海、盖四州各设学正1员,训导4员。儒学附近立孔庙祭祀先贤,政府给祭器、乐器。正统二年(1437),辽东都司医学建立。弘治六年(1493),辽东建辽左、辽右两所书院。明代中期以后,辽东都司学已具有其他十三省府学水平,是辽东地区规制最高的教育机构。辽东二十五卫基本均设儒学、社学,但辽东方志中有文所载仅有卫儒学14所,社学6所。同时,建有辽左(辽阳城)、辽左习武(辽阳城)、崇文(广宁城)、仰高(广宁城)、辽右(锦州城)、蒲阳(蒲河城)6所书院。明代流寓到辽东的江南儒士及本地学子、士绅,在谋取生计的同时收徒讲学,教化乡里[9]。
学校是社会教化的主要途径,其由官方支持兴办,以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教育宗旨。学校组织完备、教育目的明确,以儒家思想培养出的士子是社会教化精英主体,可谓是社会教化的源头。社会教化均以“学”为始,所以“学的内容”“学的方式”对于社会教化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朱元璋指出,“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及者衣事,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在与劝农,明教化在于兴学校[10]”。明代辽东地区社学、私学蒙馆等启蒙学校的教材除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启蒙教材外,还有“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经启蒙教育后,“俊秀通文义”可入卫儒学。儒学生员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生员们多数研习《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也有只专习其中一经的生员。术数、书法、“御制大诰”“本朝律令”也是生员必修课程。在学生员有月考(每月一次)和岁考(三年两次),一等、二等可参加乡试,走科举仕途;亦可通过贡举入国子监读书,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生员累试不中,年逾50岁,朝廷“给予冠带,仍复其身[11]。明代中期,辽东生员中共有进士85人,举人191人,贡生 901人[12]。入仕为官、为吏自是统治阶层的脊梁;落地生员成为当地士绅,或“舌耕”乡里,亦是教化乡民的重要力量。
(二)乡饮典礼与社会教化
从教化实行的组织和途径上来看,教化是一个“化民成俗”的过程。乡饮、乡射、乡约、节日公式等典礼,是辽东社会官方推广教化的重要方式。乡饮,乡饮酒礼的略称,始于周代乡里举行的尊老尚贤礼仪。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诏谕天下:“上以海内宴安,思化民俗以变于古,乃诏有司举行乡饮,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之制,又取《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10]。”洪武十六年(1383),明廷颁布《乡饮图式》,规定:“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乡饮酒;里社春秋社祭会饮毕,行乡饮酒礼。”乡饮由各州县年老有声望者主持,众宾以年老者上坐。“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是明代乡饮酒礼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即系顽民”[13]。洪武十九年(1386)颁行的《御制大诰》再次申明乡饮酒礼“崇老有德”“谨守孝悌”“扬善惩恶”等教化乡里的儒家礼仪。
乡饮酒礼一般在学校或孔庙举行,因为这些地方是讲明孝悌、礼义的特殊场所。既可以向青年学子灌输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又可以引导民众养成尊卑有序的生活习俗。《辽东志·典礼》载,正德十四年(1519),巡按高钺、参议蔡天祐最初在辽东举行乡饮,“岁正月、望十月朔行礼如仪式”。正德九年(1514),巡按刘成德亲自教诲诸生,“遵大明会典所载参以旧仪行”乡射礼,以“尊王制便士习也”。无论乡饮还是乡射,均是辽东官员关注礼教事宜、教化治民的措施。“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为坠,以忝所生[11]。”除乡饮、乡射典礼外,辽东地方官员在庙宇等公共场地举行乡约宣讲。如“辽阳以西多有关羽庙,庙前闲敞可以会众”,由政府官吏或乡社耆老“会其约中之人相与为礼,而讲其所听之教,所教者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勤作农桑,不为非义等事”。宣讲内容完全符合社会教化内容,即将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融于儒家礼仪伦理,使“高皇帝所定之教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间多有列书于墙壁而相与诵习”。地方官员集中宣讲后,“又令里正执铎徇路而遍晓之”[7]。
(三)宗教信仰与社会教化
相对于学校的直接教化方式,政府祭典与宗教信仰则通过间接的方式逐渐促使受教化对象内心发生改变。祭祀与信仰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诉求,通过天地、神仙、因果等精神寄托以达到内心的平衡。政府倡导的祭典给人们提供虚拟的惩恶扬善、镇保一方的超自然力量,佛、道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可以唤起民众对未来的期盼与追求。《辽东志》与《全辽志》中均将“祀典”列入典礼范畴(见表1)。《辽东志目录序》载,“兵食足既,教化式崇。敬天而重时,隆德而上龄,始于尊君,终于邦好,生人之教明矣”。在边疆稳定、百姓生活富足时,祭祀天地、名山巨流、贤臣武将等庙坛及相应仪式是教化的重要内容。

表1 明代辽东法定祭祀典礼
《全辽志》中增加了真武庙、火神庙、二郎庙、东岳庙、龙王庙、关王庙、马神庙、三官庙、天妃庙、飞天无敌之神庙(辽阳城东)等官方祭祀庙坛;同时又增置花将军祠、广威将军祠、邓将军祠、褒公祠(《辽东志》中已载)、旌功祠、忠义将军祠、忠节遗爱祠、群烈祠、王忠烈祠、阎忠愍祠、贾忠壮祠、黑忠勇祠、杨忠壮祠、缐都督祠、杨都督祠等功臣名将的祠坛。政府主持祭祀的目的是为了报功崇德,使“民知敬神,则知忠君”,朝廷敦促辽东地方官员应“利导”之[8]。各级官员各祀其事,不得僭越,强调祭祀官员身份亦是强化教化内在的尊卑、长幼等封建伦理。明代,辽东地区的佛教、道教文化逐渐兴盛。辽东都司境内有寺观120余处。据《辽东志·地理·寺观》记载,截止嘉靖十六年(1537),辽东地区寺观数量如下:盖州卫有28处,广宁有13 处,宁远卫有11处,辽阳卫有11处,广宁前屯卫有10处,海州卫有10处,复州卫有7 处,锦州卫有5处,金州卫有6处,铁岭卫有6处,沈阳中卫有 5处,广宁右屯卫有4处,义州卫有2处,开原有1处。寺庙与道观分布多集中在农业文化发达的辽南地区。百姓的婚丧嫁娶、节庆民俗与佛、道文化息息相关。宗教的济世度人、劝人为善、因果循环等教化内容为统治阶层所提倡,其通过宣唱通俗的劝世故事等教化方式、与民间其他信仰灵活结合的形式亦极易被辽东民众接受。
三、明代辽东地区社会教化的特点
明代,“辽东为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甲兵之所聚也,夷夏之所交也”。修《辽东志》的要旨为:记述“疆域形胜之分,险要扼塞之处,民情风土之宜,学校人才之辨,政赋物产之差,兵革士马之用”;而后“究其始终,察其盛衰,验其淳漓,审其登耗,观其强弱,以知其成败、得失之故”。通过对《辽东志》与《全辽志》中学校、祠庙、典礼、官师、风俗、人物部分的梳理,总结明代辽东地区社会教化有如下特点:
(一)化夷为民,倡导汉俗
辽东地区古为大荒之境,“汉世以降,沦入东夷”,又历辽、金、元三代,“浸成胡俗”。明代,辽东地区虽为明廷直接统治地区,但仍邻胡虏。“守边地”“化胡俗”成为辽东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守边”是明廷设置辽东都司的首要职能。《重修辽东志书序》中记载,辽东虽“北邻朔漠,而辽海、三万、沈阳、铁岭四卫之统于开原者足遏其冲”;虽“南枕沧溟,而金、复、海、盖、旅顺诸军联属海滨者,足严守望”;“东西倚鸭绿、长城为固,而广宁、辽阳各屯重兵以镇压之,复以锦、义、宁远、前屯五卫(广宁左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前屯卫)西翼广宁,增辽阳、东山诸堡以扼东建”。所以,在辽东祭典对象中,多以武将居所,乡贤仅有现代管宁、王烈等前代寓居辽东的名儒。明代辽东树立如花云(花将军祠)、张良佐(广威将军祠)、杨维藩等边疆名帅为膜拜对象,旨在宣扬他们英勇守边、四虏不敢窥探的事迹,倡导边地军民维护明廷统治、保家卫国之心。
同时,明廷利用学校、乡约、民俗使辽东境内居民摆脱胡俗,进而安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辽东地区社会教化并未直接以“程朱理学”为内容,倡导人们安邦定国、治学入仕,而是通过学校、乡约组织宣扬忠君、美俗(汉族习俗)等中原文化的基本内容。正统中期以前辽东地区以建立防御体系为主,辽东总兵为最高军政长官,罕有社会教化措施。如辽东乡饮酒礼推行其,正德十四年(1519),地方官员因“恶其缺典”,始举行乡约礼。正德九年(1514),巡按刘成德“恶其缺典”,“尊王制便士习”乡射仪礼[8]。“恶”字明确反映出,至明代中期中原基本礼教不为辽东官民所重视。明代中期以后,辽东社会趋于稳定,地方官员深感进行社会教化的紧迫性,方始行祭典。明代边患危机出现之前,辽东地区居民安于生计,土地得到开发,社会教化由上至下渐次推广。辽东“畜牧供忆,各有司存。罚当罪,而赏当功,皆前古所未悉者……西北诸胡不敢纵牧东方,琛贽联络道涂。民得安稼穑、饮食,以乐生送死。其大者,风俗以教化移易,人材资学校作成”。简言之,至明代中期,辽东“承平日久,礼乐文物,彬彬然矣”[8]。朝鲜使臣途径辽东期间,在驿馆、民家留宿时,辽东官员、役夫、百姓均以汉俗礼仪标准接待朝鲜使臣[7]。辽东地区丧葬习俗、岁时节庆、接人待物多类似于燕赵之间(河北与山西、河南北部一带),即与关内大体相同[13]。但于近边地区仍有父丧食酒肉,争抢礼物不顾礼仪谦让,男女聚会不分座等胡地之风,这种不符合中原文化的现象多为“北俗习染夷虏”所致[7]。所以,在“四民来实”的辽东地区,养成中原文化习俗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
(二)以礼代教,孝悌为本
辽东地区的社会教化基本参照明廷颁布的仪礼标准。如前文提到的祭典仪式,均有“如仪”字样,即仿照国家仪典,具体参考朱熹编制的《礼仪集注》。因地缘、经济条件所限,辽东从上至下没有深究礼教思想渊源的物质基础。所以,辽东地区不可能发展出独具特色或者更为丰富的社会教化内容与形式,直接颁行中原教化的现有仪式更为简单有效。地方志中呈现出的辽东社会教化措施,多仿效、简化中原地区的教化内容。具体表现在:明代辽东地区几乎没有国家御令、礼典等地方实施细则,社会基层中的祖规家训十分罕见;教化礼仪执行过程中具体环节可因地变通。例如,乡约、乡射等祭典中原地区多在府州县儒学、书院内进行,而辽东地区各卫则可在庙宇空地举行。祭祀祠坛,经常有“旧时举行,今废”等字样,可见礼仪教化传承并未形成。
明代辽东地区树立的教化典型与内地相似。如《辽东志·官师志》载:“出政令,树声教,其必由人乎。爵命以驭其贵,使命以驭其专,职官以驭其分,名宦也者,纪德政,扬名实也”;《辽东志·人物志》载:“德政行,人士淑矣。以儒术显,以将材录,以方译用。至如济美象贤、立功立言、殉名殉节,又各以其汇表之。旁及寓贤,细及方技仙释,无遗人矣”。虽然辽东士大夫家以礼仪廉节持家训子,城郭附近之民与此一致,“孝悌贞信不绝于书”,但实际上,明代辽东地区的社会教化推广有限。辽东腹地村落多数居民仍为衣食而忧,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没有条件践行中原礼俗,所以在辽东方志中记述的道德行为十分简单,“孝悌”成为辽东民众教化的根本。《辽东志》与《全辽志》中“人物志”多记述名宦、守将事迹,普通民众仅以“孝行”入志。如广宁右卫人吴裕,“少孤,母王氏教育备至”,“母疾衣不解带,汤药必尝”,母丧“三年不入仕”。义州人史璠,母有疾,“朝夕不离膝前”;母丧,“绝酒肉,远帷簿,三年不出”。贺钦为其作《倚庐记》。广宁人冯玺,母死,同弟与墓侧居三年,为父守墓以三年。
明代辽东地区社会教化较前代有很大进步,但与清代辖区基本涵盖辽东都司的盛京地区相比,明代辽东社会教化边地特色显著。清政府高度重视盛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在因袭明制的基础上,社会教化重点倡导儒家纲常人伦,方志中宣扬道德典范的事例明显增多。相对于明代《辽东志》《全辽志》中建置、兵备、财富为记述大宗,清代《盛京通志》中职官、学校、选举、风俗、祠祀、帝王、名宦、孝义、烈女、隐逸、流寓等均独立成卷,且内容超过了山川、建置、公署等内容。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2] 张锡勤.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J].齐鲁学刊,1998(2):72-78.
[3] 金毓黼等.奉天通志·教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4] 元史·选举志一:卷81[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
[5] 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大元国广宁府路尖山单家寨创建大玄真宫祖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7] 林基中.燕行录全集[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8] 金毓黼等.辽海丛书 ·辽东志[M].沈阳:辽沈书社,1984.
[9] 齐洪森.东北地方教育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10] 明太祖实录[Z].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九年重抄本.
[11] 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制[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明英宗实录[Z].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九年重抄本.
[13] 申时行等.明会典·乡饮酒礼[M].北京:中华书局,1988.
(责任编辑:刘士义)
The social enlightenment among Liaodong chronicles in Ming dynasty
ZHANG Xiaoming
(AnshanNormalUniversity,AnshanLiaoning114007,China)
Ming dynasty is the prosperity era on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A large number of annals,province,state and county chronicles were published.LiaodongChroniclesandQuanliaoChronicles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annals of Liaodong areas.In Ming dynasty,most areas of Liaodong had becom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 central culture spread further to the edge,whose core is Han culture.Civilizing and protecting were the main contents of social education in Liaodong.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n social education practicing in border areas,and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of Liaodong culture and central culture,through combing the contents on officers,elections,figures,customs and persons sent into Liaodong mongLiaodongChroniclesandQuanliaoChronicles.
Ming dynasty;areas of Liaodong;local chronicles;social enlightenment
2016-04-15
张晓明(1981-),女,辽宁鞍山人,鞍山师范学院讲师,博士生。
K29
A文章篇号1008-2441(2016)03-0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