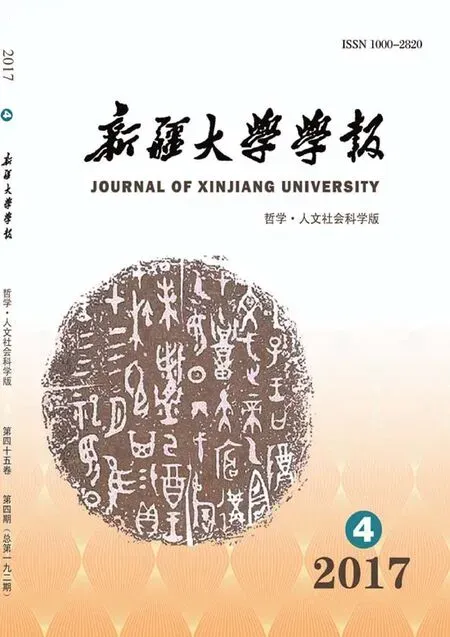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
2016-09-29孙文杰
孙文杰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西域,自古以来即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以及东西文化的汇融之地,中国有关西域记载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最早《穆天子传》与《山海经》即已有西域的相关描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著《出关记》,惜已无传。彼时,内地对西域的认知与理解极其有限。但自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之后,内地对西域开始有了更为确切翔实的了解与认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便开始了对西域的专门记载,由此开启了历代正史设置《西域传》的先河,为后人研究西域提供了最可为倚重的参考文献。
除此之外,历代还因僧游、出使、朝觐、战争等诸多原因,留下众多亲历西域者的著作文献,此类文献因具有实地考历,可信度较高,亦为后人研究西域留下宝贵的资料,如玄奘《大唐西域记》、王延德《使高昌记》、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等。
虽然历代正史、私人著述对西域的记载不绝如缕,为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诚如唐景升所言:“大都因袭旧史,捃摭遗闻,重复疏乖,可据之史料,至为有限。”[1]一直到了清代,有关西域之著述才真正兴起。之后,伴随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西北地区的持续用兵,并在乾隆年间最终统一新疆而真正兴盛起来,至此有关西域的著述才蔚为大观,出现了大量涉及新疆的官方、私人著述,如《新疆回部志》《西域闻见录》《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西陲总统事略》《西域水道记》《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荷戈纪程》《新疆图志》等。而在这些著述中,和瑛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和瑛(1741—1821),字润平,号太葊,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后历任知府、道员、布政使、按察使、驻藏办事大臣等职。1802年(嘉庆七年),因“金乡冒考案”被贬往新疆效力赎罪。同年十二月,当和瑛行至哈密时,诏命其以蓝翎侍卫任叶尔羌办事大臣。1803年(嘉庆八年),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1806年(嘉庆十一年),因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任上处理“喀喇沙尔亏空案”之政绩,召任吏部右侍郎,旋又因前乌鲁木齐都统那灵阿贪腐案发,于归京途中被任命为乌鲁木齐都统。两年后,由于其政绩卓著,召任陕甘总督。
和瑛一生沉浮宦海五十余年,其足迹虽遍及大江南北,但在新疆任职的七年却是其整个仕宦生涯最重要的时期。
任职新疆期间,在积极参与政事之外,和瑛在新疆文化建设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分别成书于1804年、1807年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均是其为宦西域时所撰。其时,正处于清代西北舆地学由兴起期向兴盛期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两部方志内容考证详实,体例严谨完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新疆及乌鲁木齐地区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史实,立体反映了清代中期这些地区的全面特点,堪称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即便是反映清代新疆历史、风俗、风情等方面内容的诗集《易简斋诗钞》,也足可补舆图之缺。由此可见,和瑛所作有关西域的著述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的双重价值。
同时,作为乾嘉时期清代西北史地由兴起期向兴盛期过程中的典型代表著作,它们又为后世西北史地的繁荣作出了表率。因此,和瑛西域著述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其价值与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门类创新
和瑛西域著述在充分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兼具学术与系统性①有关和瑛西域著述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以及其学术与系统性的研究,详见拙著《和瑛诗歌与新疆》(《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7—122页)、《〈回疆通志〉史学价值论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66—70页)、《〈三州辑略〉史学价值论析》(《昌吉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0—18页)、《〈三州辑略〉史料来源探究》(《昌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8—44页)、《〈回疆通志〉史料来源探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1—106页)。,不仅其诗集《易简斋诗抄》扩大了清代西域诗的题材范围与表现手法,对清代中期以后的西域诗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学术与系统方面,有着更为明显体现的是其《回疆通志》与《三州辑略》两书,它们在体例上的一个重大价值,就是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编纂。同时,和瑛西域著述在我国传统的史地记载该地历史、沿革、疆域、山川等记载内容之外,在门类创新方面也着有诸多的创新和突破。现将《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与《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等其前后的清代新疆方志代表性著作,在门类设置上进行比较,详见表1。

表1《回疆通志》《三州辑略》与主要清代新疆方志门类比较表
②《大清一统志》曾经先后三次编纂,首次为康熙二十五年开始编纂,至乾隆八年最终刊行。第二次为乾隆二十九年,因清政府已统一新疆,原来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乾隆帝下令续修,第一次将“西域新疆统部”收入《大清一统志》,与西域有关部分被称为《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第三次是嘉庆年间在第二次修订的基础上三修。此处专指《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

(续表1)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和瑛《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的门类分布充分继承了《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西域闻见录》等之前的清代西域方志相关门类。同时,和瑛西域著述在门类分布上也有很多创新与突破,如官铺租税、杂支、事宜、伯克、硝局、流寓、艺文、库藏、仓储、户口、马政、旌典等门类,均对前人西域著述门类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尤其是“伯克”“回务”“流寓”“艺文”四门,更是属于首创,独具特点。
与此同时,通过上表我们还也可以看出,和瑛西域著述门类创新对后世西域方志的编纂也有较大的影响。如《三州辑略·艺文》对《西陲总统事略·西陲竹枝词》《新疆图志·艺文》之影响,《回疆通志·硝局》对《新疆图志·实业》之影响,《三州辑略·流寓》对《新疆图志·名宦》之影响。
二、泽被后世
实际上,和瑛西域著述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其体例门类创新方面。如前所揭,和瑛西域相关著述内容丰富翔实,真实准确,虽非新疆之通志,但亦可补通志之缺。《回疆通志》《三州辑略》自刊行以来,内容即对后世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有着重要的影响。后世的西域著述,无论是《西陲总统事略》《钦定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西陲要略》《新疆图志》等方志,还是《辛卯侍行记》《莎车行纪》《新疆纪游》《蒙古游牧记》等游记,均大量征引、参考和瑛西域著述相关内容,如《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徐松撰。徐松生长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精通考据辑佚之学,他不仅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又深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
1812年(嘉庆十七年),徐松因事谪戍伊犁,从此走上西北史地的学术之路,成为清代西北史地具有标志性成就的学者之一,《西域水道记》是其西北史地代表性著作,首次创造性的以新疆湖泊受水体来划分西域水道,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在西北史地领域地位颇重。但是,《西域水道记》也同样多处参考征引和瑛西域著述的相关内容,如表2所示。
和瑛西域著述不仅继承传统史地学的优良传统,旁征博引,而且将之与实地考证融汇互用,纠误补缺,从而保留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西域相关史料,进而成为后世西域方志编纂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伊犁总统事略》《钦定新疆识略》《新疆图志》莫不如此。尤其是《新疆图志》,不仅多处参考征引和瑛西域著述相关史料,更是明确的将和瑛《三州辑略》列入其“引用书目”中[2]。当然,《西域水道记》也不例外,亦从中多处汲取营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后世文人有关新疆的诗集,如洪亮吉《更生斋诗文集》、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等,也曾多次征引或参考和瑛西域著述。

表2《回疆通志》《西域水道记》中关于喀什噶尔河流内容比较表
三、学术与系统兼具
自清代初期,学界涌现出一批以清代西域为主题的著述,但是,关于清代西域的私人著述不仅数量尚未形成规模,颇为零散,甚至可以称之为简陋,主要有两类组成:
一是边疆大臣为治边需要而编纂的方志类,如永贵等人的《新疆回部志》、沈宗衍的《蒙古沿革志》。
二是出使官员、边疆大吏、从军西征的官员以及因事贬往西域的内地官员文人所作的笔记、杂录、日记等,主要有马哈思的《塞北纪闻》、殷化行的《西征纪略》、夏之璜的《出塞日记》、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等[3]。
这些相关西域著述虽然保存了极为重要的西域史料,但由于彼时正处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创始期,难免瑕瑜互见。这些著述不仅篇幅简短,内容简略。更为严重的是,此时的新疆方志不仅材料零散,而且缺乏系统与学术性。
而以和瑛为代表的嘉庆年间相关私人西域著述,一改往昔记载残缺以及范围狭窄的缺陷,对各种史料博采兼收,掇拾遗残,采摭缀辑,爬梳整理,汇为一编,进而使其西域著述具有较强的系统性[4]。
和瑛之西域相关著述不仅体例严谨,内容系统完备,而且材料丰富详实、确凿可靠,如《回疆通志》卷一录御制诗及碑文,以记载平定伊犁诸役之战功;卷二至卷六,分叙哈密、吐鲁番回部总传及其子孙分派而有世爵者诸列传;卷七至卷十一,则依次分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八大城,及吐鲁番、哈密之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官制、粮饷、贡赋、租税、卡伦、军台等;以卷十二分纪略、风俗、物产等目列叙殿于后。可见全书自成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与此同时,正如和瑛在《三州辑略·叙》中所说那样,其受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影响,在西域著述中对各地的历史沿革、山川、疆域、建置、古迹等内容,在考据古籍的基础上加以实地考查,并进行精审地考辨,对西域相关历史与现实进行纠误补缺,诚如沈瑞麟所评“遂踵《西域图志》之规,爰有《回疆通志》之作。观其裁融方册,校核前闻,证必穷源,辞无甚泰,事为后法。则昔略而今详,义在办方;必州居而部别,识道里、山川之数,度幕不迷;籍军屯什伍之资,防秋有据;土均地会,审物产之异宜;件系条分,谱明王之氏族。信可谓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者也……视《一统志》而事详,本《闻见录》而时近。”[5]2
因此,和瑛西域相关著述不仅具有严格的系统性,而且也以其严谨的考辨具有了较强的学术性。学术性与系统性兼具,代表着清代西北史地学已经初步走出缺乏学术与系统性的见闻杂录式的私人著述,为后世西域方志的编纂树立了典范。
四、加强西域认知
自元代以后,中原王朝政府对西域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开始逐步减弱,到了明朝,政府控制西域的范围最远不过哈密。而清初,我国的西北疆域恰如梁玢所言:“今之疆域,率由明旧,可考而知也……(其地)又西而凉州、甘州、肃州,东而靖虏、宁夏,极于榆林,皆边卫也。”[6]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时人对西域的认知和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史籍,并深受其影响,如班超“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观念。其他历代有关边塞的记载所反映出的孤苦和思乡之感、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地理特征和荒寒之感、文化疏离感等,使边塞几乎成了隔膜的代名词[7]。可见,时人对西域的认知仍受到传统的、强大的自书本而来的古人观念的浸染和影响[8]35,不肯接受国家疆域的扩充,仍将嘉峪关视为内地与西域地理和文化的分界。这一情况,随着以和瑛为代表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官员的履新,以及他们极具实地感受的西域著述的陆续面世而有所改观,逐渐开始影响并改变了外界对西域的认知。
在和瑛笔下,西域并不像内地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贫瘠、荒凉,在清朝统一之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域已成富庶之地,社会、经济均有巨大的发展:“尝询嘉峪关吏,内地民人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不宁惟是南路回部十三城,暨土尔扈特、和硕特、布鲁特等游牧,其户口至不可思议。安居乐业,共沐皇仁。”[9]而战后西域户口之所以如此激增,和瑛在其奏折中也给出了答案:“乌鲁木齐水土旺厚,民户殷繁,每岁丰收,并无荒歉。虽巴里坤、古城等处稍觉枯寒,然不过节候较迟,其麦豆收成亦一律丰稔,是以各乡户民按亩输粮,别无徭役,民力原无拮据,洵乐土也。”①和瑛,奏为体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方浮收勒派积弊实在情形酌拟更正各款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23-0176-019。天山南路地区,亦是“其地三山环抱,二水交流,土田肥腴,城堡麟次。”[5]186“桑麻、禾黍宛然中土”[5]265、“内地商民、外番贸易者来往聚集于此”[5]291。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繁荣,中原文化也慢慢影响到了西域,人们已感觉不到异域孤冷。在这里,有“桃花随水去,自待春风还”的江南韵味[10]516页上,有“马腾银汉上,人驾玉虹来”的壮阔景色[10]512页下有“呼鹰尽出桑麻里,戏马闲看果蓏村。镇抚羌儿高枕卧,双歧铜角听黄昏”的安宁祥和[10]513页上。这些记载表明,像和瑛这样的亲历西域者,对西域的认知已经大有改变,其西域著述中的内容对新疆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诚然,和瑛及其西域相关著述,并没有彻底地、完全地改变人们对西域的认知。但经过以和瑛为代表的乾嘉时期西北史地学者(如祁韵士等人)不断对西域的推广与介绍,人们对西域的了解开始逐步摆脱对汉唐文献的绝对依赖,对西域的认知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大的转变,对西域的关注度也愈来愈高。人们关注已转变为如何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经营和管理,并通过对西域的有效经营来缓解内地的社会危机。也就是说,经过和瑛等人西域著述的不断推广与介绍,人们已经将这里视为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在清人心目中的地位亦不断地得到改变,并有大幅度地提升[8]39。
五、依据《西域同文志》规范舆地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此后,为了更有效地经营和管理西域,便开始大批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编纂西北舆图;同时,设置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职于各个行政区域,在西域开始全面设吏管理。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如新疆地区的人名、地名大多均是少数民族语言命名,仅译其音,但不知其意,“非纂辑文臣所晓”。且因不同人员或书籍翻译的不同,往往将一地或一人之名误作多地、多人之名,常常“粤问而燕答”。
因此,清政府在组织编纂《西域同文志》时提出:“志同文云者,仍阐韵统之义,而特加以各部方言,用明西域记载之实,期家喻户晓之实,而无鱼鲁毫厘之失焉。”[11]由于乾隆帝精通满文、蒙文、藏文等语言,深知此意义重大,特亲加指导,敕命编纂该志。是书涉及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蒙古等文字,收录专有名字3 111个[12],是西域地区的地理沿革、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但也正如前所揭,清人对西域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西域同文志》流传范围很小,所以它自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面世以来,所起作用有限。
和瑛虽因事以戴罪之身谪往新疆效力,但由于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敏感的前瞻性,并且有志于加强清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经营和管理,而其西域著述的编纂目的之一,即是为维护和巩固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而提供材料支持的:“惟愿职斯土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5]3因此,和瑛及其西域著述尤为重视新疆地区地名、人名的规范处理,这无论是在他的《回疆通志》《三州辑略》,还是《易简斋诗钞》里,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和瑛更是在《回疆通志·例言》中明确提出:
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尊《同文韵统》更正。如叶尔奇木之为叶尔羌,哈什哈尔之为喀什噶尔,英阿杂尔之为英吉沙尔,哈拉沙尔之为喀喇沙尔,穆逊打阪之为穆苏尔达巴,罕准土斯之为珠勒土斯,贺布诺儿之为罗布淖尔,色提巴尔第之为色提卜阿勒氐之类是也[5]10。
《同文韵统》,章嘉胡土克图等人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奉敕撰,以西番字母参考天竺字母,贯合其异同,而各以汉字译其音,内容凡佛经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号地名多用西番之语。根据和瑛编纂《回疆通志》例言上下内容判断,此“《同文韵统》”应该是《西域同文志》之误。和瑛敏感的注意到,西域地区的人名、地名多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来命名,由于各著译法的不同,相沿积久,以致后世颇多惑误。
因此,他提出按照“《同文韵统》”规范西域之地名、人名、山川名。而这一做法,在清代中期官修西北方志之外的私人著述中非常罕见,无论是比和瑛西域著述稍早的《西域闻见录》等书,还是稍晚的《伊犁总统事略》等书,均未能依据《西域同文志》作出及时的响应。遵循《西域同文志》规范西域人名、地名的做法,直至道光中期才成为清代私人著述西北史志的通行做法。和瑛及其西域著述的这一行为,为后世私人西域著述的编纂作出了表率,树立了典范,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与价值意义,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和瑛及其西域著述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继承传统史籍的基础上,重视实地考证与文献考据的有效结合,并多有创新,以其鲜明的特征与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成为乾嘉时期西北史地中的佼佼者,作为乾嘉年间西北舆地学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推动了清代私人西北史地著述的进展,为乾嘉之后西北史地的兴盛作出了诸多成功的表率,更为清代西北舆地之学的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