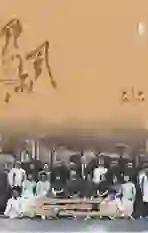钱穆在苏州中学
2016-09-28郦千明
郦千明

钱穆家境贫寒,幼承家教,自学成材,中学毕业即参加工作,先后在家乡无锡一带教书为生,从小学到中学,前后达二十余年。上课之余,他怀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沿着前辈学人的足迹,一心钻研国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苏州中学3年是他中学教师生涯的最后一段时光,也是他于国学研究方面渐趋成熟的时期。正是从那里开始,他的学术成果迭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最后终于登上大学的讲坛,成为一代儒学宗师。
学生喜爱的国文教师
1927年秋天,因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书时的同事胡达人的推荐,33岁的钱穆应聘到苏州中学,任国文课主任教席兼高年级班班主任。初来乍到,他便对苏州这座风景秀丽的古城及百年学府苏州中学留下了良好印象,暗暗打算在此作长期逗留,做一名辛勤的园丁,浇灌出满园桃李,一展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抱负。
苏州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名胜古迹众多,尤以园林古刹闻名遐迩。苏州中学坐落于城内三元坊,其前身为清代江苏巡抚张伯行创办的紫阳书院,人文荟萃,名师云集。校内有山有水,环境幽静,是教书育人的极佳之地。钱穆到校不久,便四处溜达,发现校园面积颇大,运动场、图书馆、教学楼、综合楼一应俱全,校内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节假日,他还兴致勃勃地游览学校附近街巷,发现出学校大门,向南右转弯便是孔子庙,雕梁画栋,建筑宏伟。孔子庙前为南园遗址,乃明代宰相王文肃所营建,内有亭台楼阁之胜,也是一处访古探幽的宝地。钱穆游走其间,流连忘返。不过,令钱穆最满意的,莫过于苏州中学丰富的藏书。这是他以前教过的学校都无法比拟的,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有难得见到的古籍善本。课余之暇,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埋首纸堆,乐而忘归。
他还喜欢逛学校周围的书摊、书肆,碰到爱读的书籍,如获至宝,不惜花大价钱购买。久而久之,书肆老板大都认识他,知道他是苏州中学的老师,嗜书如命,是一个极好的主顾。有的店家收进旧籍,往往预留着等他选购。有的与他事先约定,届时送书上门。一位稔熟的书店老板曾对他说:“苏州中学前有王国维,今有你钱先生。你俩都极爱书,堪称我们书店的衣食父母!”钱穆听罢,赶忙摇摇头说:“岂敢,岂敢!王国维先生乃国学名家,道德文章,闻名天下,今世鲜有望其项背者。我只不过是一名穷教书匠,喜欢读点书而已。”
在苏州中学,钱穆碰到了一位好校长汪懋祖。早年留美归国的汪校长,熟悉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特别注重因材施教。他倡导设立学分制和选科制,鼓励老师根据自己的特长开设选修课,供学生选择听讲。期末评定等次给分,学生修满规定学分,即可顺利毕业。在他的推动下,苏州中学的国学教学迅速得到发展。
钱穆经常穿一件青布大褂,戴金丝眼镜,头发偏分,匆匆行走在校内绿荫小道上。遇到师生走过,笑容可掬,热情地打招呼。他口才极好,讲课颇具特色,大受学生欢迎。讲解古文,巧譬善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说话虽然带有无锡口音,但吐字清晰,娓娓动听。讲到得意处,他常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他教国学文和学术文两门课程,让许多学生记忆深刻。学术文是选读从古至今代表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文章,他对古代名家名作都有深入研究,从作者、时代背景到所涉及的材料和思想传承,演讲时往往信手拈来,让人眼界大开。他分析问题,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有名叫胡嘉的学生最爱听他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课堂笔记十分详细,且参考各书引证,受到他的赞扬。后来,胡嘉学有所成,回忆往事时,表示非常感谢当年钱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
钱穆发现苏州中学与无锡三师校风各有所长。三师风气纯良,师生如家人;而苏中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师生关心时局,遇事敢于同当局抗争。执教第一学期,他担任学校高年级班班主任。有一次,班里几名学生跑到他寝室里问他,以前遇到学校欠薪时,几位学生敬重的老师必定请假,不赴校上课。如果这些老师依然去上课,必为同学所轻视。先生授课极受学生欢迎,而近日学校又欠发工资,只有先生还依旧来上课,大家都表示诧异,不知什么原因。钱穆闻言,笑着对学生说,学校欠发薪水,应该是暂时的事。课业却事关学生的前途,岂可说停就停。请大家安心上课,勿以这种事自扰。同学听后,默不作声,各自打道回府。
过了几天,那几名学生又来钱穆宿舍,对他说班里已决议罢课,派代表去南京催发教师工资。钱穆仍然和蔼地劝道,这种事应由教师通过学校向政府催发,与学生没有关系。一名高个子学生说,学校向政府催发,政府不会动心。如果学生动员起来,那才会有效果。钱穆摆摆手说,大家年纪尚幼,还未接触社会人事,怎知政府内情呢!万勿听信他人传言,轻举妄动,后悔莫及。领头的学生说:“班里公议已定罢课,今天特来告诉先生。”见劝告无效,钱穆颇感无奈。
后来,学生果然全体罢课,学校只好宣布放假。钱穆认为自己身为班主任,未能有效劝阻本班学生,深为自责。于是,写信给汪校长,请求辞去班主任一职。然后收拾行李,暂时回无锡探亲。
罢课结束,钱穆接到通知,又回校复课。校长汪懋祖亲自登门拜访,请他无论如何不要辞去班主任职务,并说那几个带头的学生从南京回校后,已当面严加训斥,人人都写了保证书。他们都表示以后必诚心听从老师的教诲,不敢重犯类似错误。盛情难却,他只好答应继续留任。第二天,他召集那几名学生开会,好言劝慰,请他们珍惜光阴,以学业为重,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诸生都说很后悔,没有听从老师的教导,恳求他继续担任班主任,并保证以后有事必先来请示。至此,辞职风波才告平息。
罢课事件后,钱穆发现学校风气有了较大转变,师生关系也变得愈来愈融洽。那几位学生尊敬的同事,大多继续留校任教,工作劲头比从前更足了。他原本和汪校长联系不多,为罢课的事,有过几次接触,彼此发现颇有共同语言,自此交往密切起来。后来,钱穆结发妻子病故,汪校长还亲自做媒,将夫人北京女师大的一名同学介绍给他认识。可惜,女方任中学校长,立志独身,献身教育。此事遂无疾而终。
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令钱穆印象深刻。有一天,他因苏州青年会之邀,赴该会作“易经研究”的学术讲授。演讲完毕,在座的苏州耆绅张一麟经青年会负责人介绍,与他见面。一番寒暄后,张一麟盛赞他课讲得好,不愧是苏中名师。又说他国语吐音明白,听众均很满意。其实,他平常说话带有很浓的无锡口音,讲国语自己也不太满意。他还是第一次听别人夸他国语讲得好,心想可能苏州、无锡都属吴语区,发音本来相近,大家容易听懂罢了。也可能张一麟的国语讲得更逊色,所以才会这样说。
结识学者蒙文通和胡适
钱穆结识川籍学者蒙文通,缘于无锡同乡蒋锡昌的牵线搭桥。
在无锡三师任教时,钱穆对先秦诸子发生兴趣。那时学校规定每周举行周会,聘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演讲学术,全校师生可自由参加,而且演讲稿必定在校刊全文登载。有一次,他应邀作“先秦诸子论礼与法”的讲座,讲稿照例登于校刊。时蒋锡昌在四川重庆一所大学里教书,看到无锡三师校刊上钱穆的那篇讲稿,非常欣赏,当即将校刊转给同事蒙文通一阅。
蒙文通是蜀中大儒廖季平的弟子,治史学和经学,成就卓著。他看到钱穆的文章,拍案叫绝,认为此文论述的内容与恩师廖季平先生所主张的相近,两者可互相参照贯通。于是,马上提笔给钱穆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详述自己的看法。钱穆收到信后,也立即回信,请求批评指正,并表达谢意。自此,两人鸿雁传书,广泛深入地探讨学术,交流心得,结下了深厚友谊。
1929年冬,正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竞无讲佛学的蒙文通,抽空到苏州拜访钱穆。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钱穆很高兴,连日陪好友游览姑苏名胜,以尽地主之谊。两人同游灵岩寺,又到太湖之滨的邓尉赏梅。时值隆冬,他们各乘一顶小轿,饱览沿途风光,徜徉湖山之间,谈古论今,痛快之至。
蒙文通得知好友的《先秦诸子系年》刚刚完稿,便迫不及待地拿来先睹为快。连出游的小轿上,他还取出随身带着的书稿浏览片刻。他真诚地对钱穆说:“你的书稿体例宏大,构思精巧,只有三百多年前顾炎武等老前辈可与之相比。清代乾嘉以来,很少有著述可与此书并肩。”回到苏州城后,他仍未读完此书,便请求携带书稿回南京接着看。他有个朋友专治墨子,看过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颇有启发,便亲自抄录书中有关墨家的几个章节,刊载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这是钱穆这部书稿最先发表的一部分。
钱穆和蒙文通后来都应聘到北大任教,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友谊与日俱增。有一次,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要辞退蒙文通,说他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在说什么。钱穆竭力为好友辩护,竟和胡适争执起来。可惜胡适不为所动,下学期依然将蒙文通“踢出”北大。
如果说,钱穆与蒙文通属于意气相投,一见如故;那么,钱穆和胡适的初次见面,算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钱穆对胡适早年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钱穆身体力行,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时一口气完成10余首新诗。钱穆治诸子学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主张将诸子的思想放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进行立论和考察。那次在苏州青年会演讲“易经研究”,钱穆就公开声称,他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一般来说,两人有这样的背景,关系应该很好的,可是他们并不投缘。
1928年秋,37岁的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讲学。抵达苏州的第二天,他受徽州同乡、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的邀请到该校演讲。不久前,友人曾告诉胡适,去苏州“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于是,他抵校后,即向汪校长询问钱穆的情况。汪懋祖特地安排钱穆和胡适同坐于主席台,两人礼节性地握一握手,并互致问候。刚坐定,钱穆便问道:“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不得,您知道何处可以找到吗?”
或许资料过于偏僻,让胡适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未能回答。他以为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这使他很不是滋味,两人相对枯坐,再无一言。原本大家都很期待的一场聚会,就因为钱穆劈头一句话,弄得彼此都感到无趣。
演讲完毕,汪懋祖设午宴招待贵客,钱穆奉命陪席。饭后,主人挽留胡适在苏州逗留一晚,遭婉言谢绝。胡适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带剃须刀,这一晚会让我十分难受。”大家在拙政园闲游和漫谈一个多小时,胡适坚持要走。临别时,他取出日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上自己在上海的住址,递给钱穆说:“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钱穆说“谢谢”,双手接过纸片,叠好放入内衣口袋中。初次相见,胡适给钱穆的印象是一位流于世俗之名的学者。
因为一把剃须刀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大家都认为小题大做,只有钱穆心里明白,对方是以此为借口而不想和他交谈。他觉得自己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些资料遍寻不得,恰好碰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不禁当面询问起来,实非有意刁难。
几十年后,他回忆往事时反思道:“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穆未与对方联系,更没有去上海胡宅登门拜访。
学术研究成果迭出
在苏州,钱穆的国学研究风生水起,成果迭出。他心中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从集部入手,逐步扩展到经部和子部,然后转归史部。治学则以专驭通,由子学和经学入史学,把子学、经学和史学紧密结合,用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子学和经学,以考据治史,同时又超脱于考据之上,显露出以史学研究为中心的学术风格。他的《易经研究》、《墨子》、《老子辨伪》等无疑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而《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轰动学林,成为他打开通往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钥匙。
早在无锡三师时,他就开始关注和收集先秦诸子的资料。到苏州中学后,课余时间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先秦诸子系年》的研究和写作上,重在理清先秦诸子师友关系、学术渊源及发展脉络。当时,国内正兴起“先秦诸子热”,北平和上海各大报刊竞相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能安心写作,独立思考,他从不撰文投稿,参与这样的讨论,而是将写成的稿件反复修改,希望有所发现和创新。
这项工作历时9年之久,直到1930年春,新婚不久的他赶写出《自序》,这部书稿才算大体完成。回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默默耕耘的情景,一幕幕仿佛如在眼前。其中甘苦,唯有作者自知。在《自序》中,他说:“所至学校,藏书无多,又不能恣意讨究。课务杂碎,败其深思。每一扰搁,如泥牛之入海,追探便无踪迹。偶得一日或数刻之清暇,灯前人静,精力未灰,展纸疾书,获成一篇。累积既多,稍得系统。乃逐逐翻书参考,遇及异同,过写眉端,积久之后,更复改为。然初翻甲籍,续阅乙册,目光所及,时有转移。精思贯注,未能尽赅。而乙书在手,甲书已去。乙书既去,丙书方来。记诵难周,摘录不尽。又隔之以时日,杂之以冗扰,乘之以疲怠,遇之以疏阔,虽用力之多,而所得实寡,职以此也。”
前人讲诸子学,都出自于汉代刘歆的《七略》。后来班固以此为基础作的《诸子略》,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于是有九流十家之说,后人在研究诸子学术时,便把这一划分绝对化,造成各家之间彼此不通,门户之争便起于此。
钱穆反对门户之见,力求贯通诸家来考察。他认为前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通病:第一,往往只研究一家,不能相互贯通,造成诸子间相互分离和矛盾。第二,对于史料丰富的大加申论,而对史料不详的望而却步,不懂得疏者不实,实者皆虚的道理。第三,前人讨论诸子生卒及行事的年代,多依据《史记·六国年表》,然后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但《史记》也多有错误,不可全信,否则将以讹传讹,贻笑大方。针对上述三种错误做法,他提出自己治诸子学的用心和宗旨。其一,上溯到孔子生年,下到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其二,凡先秦诸子皆一一详考,力求弄清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的轨迹。其三,对于先秦列国世系,也多有考察,另列为通表,以明其先后。前史所出的错误给予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也如网在纲,条贯有序。
他考察诸子的一大特点是史书与诸子书互参,通过考证得出诸子百家相通的基本看法。尤其是用《竹书纪年》订正《史记》之误,颇具独创精神。也就是说,他在考订诸子时,把史书与诸子书、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结合起来,拓展了国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先秦诸子系年》虽在1930年春已完稿,却迟至1935年12月才出版。按作者自己所说,原因是“自知其疏陋,恐多谬误,未敢轻以问世”,所以仍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此书被视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先秦诸子和战国史研究经典之作的必要条件。陈寅恪曾说:“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而顾颉刚更是赞不绝口:“宾四之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钱穆在苏州中学的最后一学期,即1930年春季,他的另一部要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也正式面世。此文旨在打破晚清以来今古文之争的谬见,排击当时主宰经学界的今文经学殿军康有为的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
钱穆既不从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入手,也不从经书考辨入手,而是根据《汉书》的大量史实,厘清自西汉宣帝石渠阁奏议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的120年间,经学各家各派的师承家法和经师论学的歧异和焦点所在,分析康有为的刘歆为助王莽篡汉伪造古文经之说有28处不通,从而论证了刘歆编造伪经说纯系康氏为托古改制而杜撰的。钱文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共鸣。缪凤林盛赞其为“近人的一篇杰作”。胡适也给予充分肯定,在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
以前,北平各大学开设的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讲的都是康有为的观点。钱文发表后,各校经学课秋后基本停开。钱穆的高足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的学术贡献,说:“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
《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都是考据学力作,但钱穆反对将考据学等同于史学。他从事历史考据有更高的目标,即排除学术研究的门户观念和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这是他对国学研究作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获得顾颉刚的赏识和提携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钱穆这匹学术“千里马”没有获得学界红人胡适的青睐,却被胡适的私淑弟子、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偶然发现。正是由于顾颉刚的热心推荐,才使仅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钱穆最终登上国内顶尖大学的讲堂,跻身一流学者的行列。
1928年七八月间,顾颉刚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离开广州中山大学,途经苏州老家小住。有一次,他与东吴大学陈天一闲聊,陈谈到苏州中学国文教师钱穆研究史学成果迭出,颇有成就,并表示如果愿意见面,可出面介绍。就这样,两人相约去钱宅拜访。那天,宾主聊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顾颉刚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先秦诸子系年》稿,一下来了兴趣,便指指稿件,问能否带回家仔细拜读。钱穆爽快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陈天一又来访,对钱穆说:“顾先生北上行期将至,我俩能否一起去回访他。”钱穆欣然同意。于是,两人来到悬桥巷顾家花园4号,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顾颉刚对客人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又说,他离开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曾委托他物色新教师,因此想请钱穆前去任教。钱穆觉得顾颉刚虽是著名教授,但为人谦和,坦率真诚。顾颉刚接着说,他在中山大学上课,以讲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这次去燕京大学,仍当沿袭中山的课,继续讲今文经学。最后,他还热情邀请钱穆向其即将赴任编辑的《燕京学报》供稿。
不久,广州中山大学拍来电报,聘钱穆前去任教。钱穆拿着这份电稿,跑去找校长商量。汪校长挽留道:“你去大学任教,是早晚的事。我明年将离开苏中,你能否再留一年,我们一起进退。”钱穆是极重感情的人,见校长如是说,便当即答应留下来。于是写信给中山大学,婉辞聘约。
顾颉刚闻讯,致函钱穆,再次提出请其为《燕京学报》写稿。于是,钱穆将刚刚写成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寄去。尽管钱穆否定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啻与顾颉刚的观点唱对台戏,但顾颉刚相信“知出乎争”,丝毫没有介意,依然将钱文编入学报第七期公开发表,并在自己《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接着,又屡次邀钱穆批评自己的文章,目的是想听到不同的见解,以便修改和完善。钱穆也不客气,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顾先生“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识其为一流”,“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顾颉刚在发表这篇评论时,特地加跋道:“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原稿标题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编发稿件时,顾颉刚将其改为日后广为人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许多年后,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检出这篇力作的手稿,发现上面有乃父编辑时留下的笔迹,才发现这个秘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钱穆夫人胡美琦到北京查阅顾颉刚日记,看到顾潮送来的丈夫旧稿,回忆说:“以前听钱先生说过,这篇文章的题目原来不是发表时的那个题目,不知是否为顾先生所改,现在可以明白了。”
除了帮助钱穆发表研究论文,顾颉刚还向燕京大学竭力推荐,聘请钱穆到该校任讲师。这种博大的学术胸怀和知遇之恩,使钱穆终生难忘,他感慨地说:“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1930年9月,钱穆收拾行囊,告别苏州中学,前往北平燕京大学报到。从此,他的学术人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