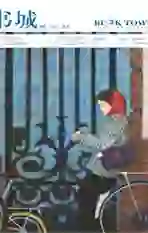眼前的春秋(下)
2016-09-22黄德海
黄德海
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
《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前句有《诗大序》背书,“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历代尊为圭臬。至现代,则有专文专书讨论,与“文载道”并举,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至于后句,大序把它作为前句的解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其后也关注者希,几乎只在引用的时候作为对句出现。作诗言志,教诗明志,赋诗观志,献诗陈志,志与诗连绵不绝地发生关系。《眼前》讲到的那场国际性宴会,作为天下盟主的执政,客于郑国的赵武对其七位部长级人物开口,也果然是:“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为什么偏偏是“志”?
“诗三百风雅颂,大致是个同心圆模样,也像是时间里生成的诗歌涟漪……这一诗的涟漪,很清晰也是权力的涟漪,《颂》中心一点的几乎只存在周天子一人(孤独地虔敬地面向着上天),《大雅》挤着共治的庙堂之士,《小雅》则是源远流长的、从早早周还是个部族时就有的所谓子民,《国风》才是放眼天下的万民兆民;这大致上也是个从天上到人间的涟漪,从祭祀崇拜到王国统治再到生命现场的耕织劳作、情爱婚姻乃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因此,这也就是悠悠岁月的一个时间涟漪……《诗经》的搜集者、编辑者,从一首一首诗的具体呈现隐隐觉察出这一大时间图像、时间秩序。”把这个时间图像二维展开,也同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空间图像了,那层涟漪从中央及于地方,又由地方回荡至中央,而自天子以至于士大夫的“志”(“志”为士心,起码在古代还算不到庶民头上),就在这时空的涟漪里流动不已。
一个人胸怀的志向,他变化万端的情感,无论是怎样的形态,只要是真的,都可以藏放在一首首“诗”里,所谓“思无邪”。赋诗呢,亦无邪,即使一个人把自己巧妙地包装起来,在高明的人看来,也仍然是一种无邪,因为遮掩本身即是他的心性流露。一个人的赋诗,也会明明白白地流露出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具体情境,他在风雅颂这时空涟漪的哪个涡流里。赋诗人自己的生命信息散发出来,会被有心的观诗人提取,于是,《诗经》“与其说是文学诗集,不如看成是一部生命定理大全、定理的百科全书,记得愈多,就愈知道怎么计算世界”。有心的读诗和观诗者,无数次出入于不同时位、不同性情者的复杂情感变化之中,熟读而精思入神,告诸往而知来者,由知言而知人,授政以达,四方专对,处事经权合宜,“深则厉,浅则揭”,始终随时随地而动。
那随时随地流动的“诗”,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板板滞滞地读起来,是不是有些不够劲不过瘾,仿佛缺了一点魅惑力一点烟视媚行的美?对,嘉会需佐以歌,单单把诗拎出来,缺了歌的流宕徘徊,就少了美目的一盼,临别秋波的一转,老让人觉得不够尽兴。你当然猜到了,除了诗言志,还需要歌永言—更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情怀,有时连歌词也省了,随着自己的情感起伏而有了节奏,拖长声音,直接咿咿呀呀地唱出来。于是,我们从诗来到了乐,“再没有任何东西如音乐,和人的感知全无隔离无需中介,直接就是生命的呼吸起伏流动云云,如昆德拉引述黑格尔说的,音乐‘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这些起伏是文字到达不了的”。
我们(尤其在现场)听到音乐或者肉声的歌,会不自觉地跟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流动的声音,仿佛《诗》的“兴”,破空而来,有些接近无有意味,“就只是始生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也还早于人心的哀与乐生成”。音乐“有自身独特的生长演进之路,并不描摹不跟随这个世界,也很快就脱离开这个世界;音乐先于世界的形成,源于更早也更浑然的自然,并自成世界,你得放它自由,像人心一样自在地、若即若离地流动”。在这里,文字和词句失去了效力,“音乐(或说音乐围拥起来的这一个暂时世界)很轻易地就淹漫过它们,溶化并驯服了它们”。我们听着这一切,仿佛“孤独地束手站在天地之前,再不能多前进一步了,只有我们身体里的某一部分、某物,如轻烟如气息如袅袅不可闻见的声音,可轻微地、难以言喻地上达”。我们如重负初释,卸去了日常的包袱,在沉浸里获得净化,内心柔软如初生的嫩芽。
多么期望这个关于音乐的讨论就停留在这里,世界或许将朝某种理想中的大同境界行进,人也将专气致柔如婴儿不是吗?很可惜,这沉浸的惯性并没有及时刹车,在这沉浸的感觉里,我们来到了“某个迷醉之地、某个共同荣光或日已西夕荣光逝矣的非比寻常时刻”,或者,某个整全的、唯一的、至上的东西在那里,“人进入到某种集体的、相似的心思状态情感状态”。“音乐的强大夷平力量,创造出某种全然感性、全然抒情的封闭世界”,趋同本性让人“沉缅、泛滥以及进入一种集体迷醉状态”,“显露出附魔也似的表情和难以控制的身体”。紧跟着来的,就是暴力了,某种“需要叫喊、动乱和野蛮行为”的集体暴力:“大革命,通常就是一首歌对抗另一首歌,这一音乐效应压过另一音乐效应,一直到我们今天刚刚都还是这样……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大抒情诗,而且每回革命还都真的写成、唱出、留下一首一首歌来不是吗?”
“乐胜则流,过作则暴”,这以沉浸开始、以沉湎启动、以嗜血结束的历史实例,两千多年来层出不穷,“荣格精准地指出,这样迷醉的感性和抒情,正是暴力的上层结构”。所以,人得想方设法把这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或者把它“封闭在宗教崇拜里,秘而不宣地控制在祭司巫师云云这些人手中,成为某种独占的知识、配备和操作秘技”;或者“小心翼翼地,最好从源头处就控制好它才行”。也就是说,本该秘而不宣的音乐力量,“古代中国比较特殊的是早早把它光天化日地摊开来,通过理论化,释放到一般性的世界里,得到更广阔的理解、结合和应用,比方成为某种统治知识和手段,但也无可避免地早早启动了除魅”。六经之一的《乐经》消失,是否就是为了控制音乐的不可预期效应,就是古人对音乐除魅的方式之一?
“《乐经》成为一本书却又不幸流失之前,它一直生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在人们的记忆里、话语里,是人们思维乃至于现实工作确确实实的一部分”。因而,《乐经》的消失,只不过是一本书的湮灭,而不是古人关于乐的思维方式的消失。“一本书从不单独存在,它同时生于、存在于并完成于其他更多的书中”,《乐经》的思维方式,就存在于古人关于音乐的“秘索思”里,存在于《左传》人们对乐的理解里,存在于后出的《礼记·乐记》里……对此,唐诺自信地确认:“如果说今天《乐经》忽然在沉睡两千多年后冒出来,比方挖到一大叠竹简或又找到孔子另一处住宅云云……结论文风不动,当时中国人的音乐想法、音乐图像不会改变,甚至也不会增添什么,没事的。”
是的,不会增添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中国古人对音乐的理解,“相当程度阻拦了音乐,也相当程度减去了暴力,两千年里,少掉了不少死亡,尤其少掉了很多人附魔般的迷醉、残酷、嗜血、狰狞表情。一样的,你怎么可能去除掉这一边不跟着也去除掉另一边呢?难以想象中国会出现瓦格纳那样的音乐,包括音乐本身的繁复,也包括那一种炙热激情”。那消失在平静后的热情,让唐诺有点遗憾地说起春秋时期最有名的乐师师旷:“他始终冷静、理性、耐心,心思澄澈而且话说得好,以卡尔维诺的分类来说,他是水晶也似晶莹的人,而不是一团火也似激情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明智的忠告者,以及一个总是意态安详目光杳远的哲人,他的生命成就最高的那一点仍是音乐吧?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他更多,尤其是有关这样一个人‘他一生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
或许用不着遗憾,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唐诺几乎已经说了出来:“礼与乐,在人的思维探究里逐渐合流,更在道德体系、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里必然地合流,成为如光与暗也似必须一起想才完整可解的一体东西。”进而言之,《诗》《书》《礼》《乐》《易》《春秋》构成的六经系统,本来就是完整的结构,它们各有其所司的范围,却又在思维上勾连为一个整体。在这个结构里,《乐经》不用非得是一本具体的、写出又消失的书,它只要在那个合适的位置上,让人们在想事情的时候想到它,就已经是存在了。或者不妨这样说,六经的完整表达,未必非得是实然的存在,也不妨是变动而不易的“言辞的城邦”,它一直闪耀着卓越的光芒,让人在嘈杂的尘世里可以时时瞥见,比照自己当下置身的一切,增添思维的向度。
话说到这里,也就不妨来设想一下师旷—脑子里有完整六经图景的他,早就意识到了乐残暴嗜血的那部分力量,因而也就时时警惕着“他一生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的力量,把它的躁狂之气一点点收拾干净,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心思澄澈的乐者,一个并不存在的《乐经》陶养出来的理想人物。《弹琴总诀》谓:“弹琴之法,必须简静,非谓人静,乃其指静。”那个坐在古琴旁边,指头都能即刻静下来的人,不就该是能免除乐的不幸效应而收归己身,不就该是冷静、理性、耐心而心思澄澈的吗?那不息的生命活力,深深地藏在师旷最心底,看起来古井不波,却跃动如灵蛇,对,就是那样,“深深拨,有些子”。
一直移动着的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毕生致力于写苏格拉底谈话的柏拉图,跟传《春秋》的《左传》作者,是不是有着相似的心境。老师早已经离开了,而老师的言谈话语,还深深地留在心里,他们要试着用自己的笔,记下那伟大灵魂的样子,却又时时感到书写的困难—“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虑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恰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文字写成后的流播,更加不可预知,因为它会“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没有办法知悉,柏拉图是不是另有其“未成文学说”,孔子是不是有秘而不宣的口传心授,我们能读到的,只能是真真假假的柏拉图公开作品,以及《春秋》和包括《左传》在内的“三传”,因而也不得不从这不可信赖的文字开始。
鲁宣公二年,《春秋》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就是日后我们熟知的“在晋董狐笔”,晋国的董狐严厉地记下,赵盾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晋灵公,《春秋》照搬不误。事实呢,“杀人未遂的反而是死者晋灵公,还三番两次;凶手赵盾只是个被害者,连自卫杀人都没有,他逃掉了,而且事发当时人已流亡”。乙丑这天,赵穿发兵攻杀灵公,流亡的赵盾赶回来收拾残局,“事后董狐记史,大笔写的却是‘赵盾弑其君,还当场公布出来,赵盾当然自辩,但董狐讲,你是国家正卿,事发当时你人尚未出境,回来又不追究弑君贼人,不算你杀的算谁?”赵盾呢,只好认账,但心有不甘,悲伤地引述了“我之怀矣,自诒伊戚”—“我对晋国故土的眷恋不舍,拖慢了脚步,才得承受这一罪名,真的像这诗说的,情感往往给人招来不幸招来烦忧没错。”
不止赵盾自己,我们不是也替赵盾觉得不甘吗?熟知历史的孔子,跟我们的心情没什么两样,《左传》记了下来,“惜也,越境乃免”。孔子“深知(赵盾)在这场乱局中的一次次必要作为及其价值,如此的历史定谳罪名毋宁只是不幸,人被抓住了,落入一个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以上)困境里”。那些担负着责任的人,往往会落进类似这样的困境—那个飞快地追赶对方前锋,要先一头顶到皮球的后卫,非常可能被人抢了先,也偶尔会非常不幸地进了乌龙,球队输球的责任,当然要这个最负责任的人来承担。“《春秋》责备贤者”,你没法责备一个本来就不想负责的人,他们躲在永不长大的壳里,用无辜和束手来对待世界,怪他们不得。《春秋》求全责备的对象,始终是愿意、应该也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只是这次轮到了赵盾而已。
文字真是不可信对吧?孔子明明知道赵盾的委屈,却为什么不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春秋》中改动一点什么,让赵盾明亮地留在历史上呢?是不是很可能像唐诺说的:“《春秋》的修改纠正作业,不针对特定的人,甚至已不限于单一国家,而是彼时的一整个世界、人极目所及而且伸得到手的世界,起码孔子自己倾向如此。《春秋》呈现的最终图像……是一个(孔子以为)这样‘才都正确的世界,人都回到对的位置、做对的事,并且对于所有人无可抗拒的灾变和命运袭击,都作出对的回应和选择;把一个正确的世界版本,叠放在歪七扭八的现实世界之上留给后人。”
精通世故的孔子当然不会幼稚到认为,人人都愿意尽力去完成这个正确的世界版本,他当然知道人心的万有不齐,知道小人天性上就有逃避责任的倾向,知道无论跟他们说多么富有洞见的话,“纵闻一音,纷成歧见”,最终也不过是变成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不会迂阔到要寄希望于他们。如此一来,期望世界可以是正确版本的《春秋》,寄希望于贤者的,就不只是要承担起他自己该负的责任,还得把其他人因无知和怯懦推脱掉的那份,也一同担负起来。如果放弃承负,就请你把自己放回到小人的位置(或者你并不自觉,那么好,就让《春秋》用忽略来把你放回)。赵盾,不正是承担了本该是晋灵王以及晋国变乱者的责任?并且,他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几乎只能是小声咕哝两句诗,委屈再深一点,声音再大一点,引的诗怨意再深一点,《春秋》可以让他免责,当然,他也就永远得不到孔子对他的回护—有一个孔子这样级别的人来回护自己一下,内心的委屈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安顿,或者竟可以是荣耀?
在格林《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柯林医生谈起:“你还记得修女们在丛林中办的那所麻风病院吧?当发现D.D.S是有效药物时,那儿的病人一下子便减至六个。你可知其中一位修女怎么对我说吗?‘真可怕,大夫,再不久我们就要没有半个麻风病人了。她真是个麻风病爱好者。”—“人的确会不知不觉成为麻风爱好者,如果你夸大单一一个信念,并把它牢牢绑于单一一人一事一物。”比如,单纯认为《春秋》对赵盾的褒贬是正确的,执此批评《左传》曲意回护;比如认为《左传》对赵盾的体贴是对的,执此攻击《春秋》蓄意篡改;比如认为谏言而死是正义的,引颈就戮是凛然的,某些心软的片刻是自己的慈悲,带着特殊姿态特殊语调的“对抗性书写”是唯一的可能,如此等等,都难免会不经意地成为某种类型的麻风爱好者。
得好好感谢《左传》,它没有成为麻风爱好者,“我们完全看不出(写作者)有任何畏怯迟疑,可也不见用力”。如此灵活的书写方式,让我们在《论语》之外,看到了一个处置事务经权合宜的孔子。在《春秋》这里,孔子“本来只是受着较多约束的书写者而已,但因为后来有了《左传》,孔子……成了书中人物,有机会回复成一整个人的完整存在,让多于《春秋》书写者的另一个孔子显露出来—一样写下了‘赵盾弑其君这历史定谳判决,却又对这个判决表示惋惜以及可以继续讨论”。这个合拢起来的、不停变化着的人,才是孔子,说话永远有弦外之音,做事永远针对具体,他“常对相同的问题给予不同的回答,今天明天不同,子路问冉有问不同;还有,‘未知也这一保留之词算是孔子常用,用于人也用于事,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探询;还有,孔子不惜破坏甚至推翻自己说过的话,也许是在他察觉学生太相信时”。孔子对来问者的回答,总是跟着时间变化,还得针对来人刹那的调整,答案便不免神形百变。想把孔子抓牢,让他给出某一问题的永恒不变答案,怕只是懒人的奇想罢了。
“最可惧最不确定的是时间,一直移动着的时间”,人不得不在这移动的时间里不停地调整,不停地决断,“生命的确处处是抉择,绵密到几乎无时无地,绵密到甚至已不感觉自己在作抉择”。幸运的是,这样的抉择并不是每次都如麻风爱好者那样面临生或死,to be or not to be,先进或堕落。那些激烈的二选一图像,“孔子不会认为是人生命的经常性处境,漫漫人生遇见个一次两次已够沉重够倒霉了”。更可能的人生之路,或许该是某种缓慢却并不停息的成长。当然,人也难免不幸到会遇上这样极端的人生抉择,“也许在某种极特殊的不幸时刻会如此像是日月星辰和人正好在某个交会点上,碰上了”,孔子也并不逃避,“那就归诸命运归诸天地神明迎上前去吧”。不自处险境,但危险真的来了,也得应对是吧,这应对“需要的不只是瞬间的勇气,还需要知识,需要不停歇的思索、决定和怀疑”。运气好一点的话,“履虎尾,不咥人”,境况虽然危殆,仍然可以曲曲折折走出一条生路对吧?
《眼前》临结尾,唐诺有些感伤起来,他谈到了善恶问题。每个民族里,对恶的描述都生动而精彩,善却往往乏善可陈。究其实,“恶是斑斓的、淋漓的,但通常并没有什么深度,一般人也容易看懂,它的核心基本上只是人皆有之的生物性本能及欲望……它令人误解的深度只是技术性的必要隐藏……真正深奥的是善,直至深不可测,因为这是人单独的发现和发明,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物性生命构成的联系极其幽微、间接、不定,倒是屡屡背反;也因此,善不容易说明不容易说服,它对人有相对严苛的要求,每朝前走一步,便得抛下一堆人,听不懂以及不愿听懂的人,最终,它总是远离人群,消失于人的视线之外”。善的书写和领受困难,最终几乎让它在书里消失了,那些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都写不进书里面。
或许,我们也用不着如此感伤吧。如开头所引,那些惯于沉思的书写者,大概早就意识到了书写时如善恶不均这样无可避免的难题,甚至还更远一步地意识到了书写本身及其流播的困窘。我很愿意相信,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解决之道已经蕴藏在其中—那本安放不下孔子太多善意的书,不是通过《左传》,通过历代的有心人,也通过唐诺,一点点复原了出来,也一点一点好好地传递下来了吗?通过不断地书写,交谈,与这世界和我们自身的问题共同生活,善不是“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自足地延续下去”了吗?某些纯洁的希望,银白丝线一样从天上垂下,虽未触及地面就返回了天上,但那星星点点的亮光,并没有就此消失。那自古人绵延至今的善意、善念和无比艰难的善,虽不绝如缕,却依然流淌在不息的时间长河之中,婉转地传递到了有耳能听的人心中,并最终呈现我们的眼前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