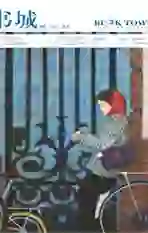汽笛七八样 击柝有派别
2016-09-22王培元
王培元
一
“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这是鲁迅小说《弟兄》里,张沛君在患猩红热的弟弟的床边,焦急地等待驾驶汽车来诊病的普大夫时的情形。
《伤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此为主人公涓生的自述,未尝不可以看作也是作者自己曾有的感受。
鲁迅的听觉似乎格外灵敏,他对声音极为敏感,这在中国现代作家里恐怕并不多见。《厦门通信(三)》是他致李小峰的信,夜深写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五更,就听到了更夫的击柝声,于是又加了几句:“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在游戏笔墨中,可看出鲁迅对“声调”及节奏的超常感知力和浓厚兴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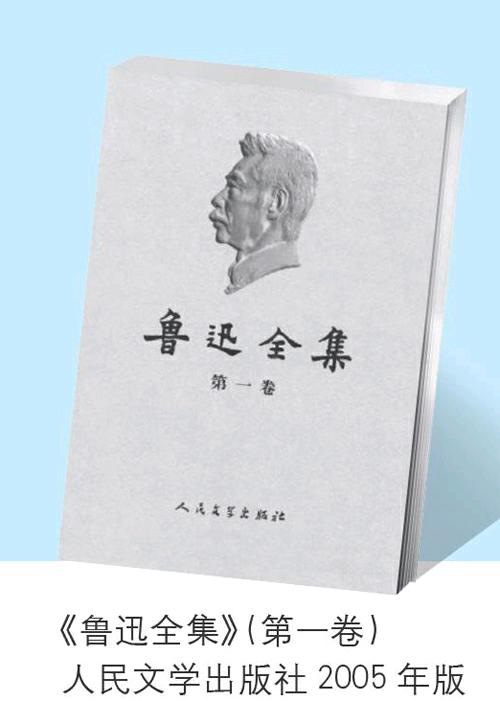
耳朵是人类特别神奇而又十分苛求的器官,它可以在最佳状态下听出每秒振动少于三十次,以及每秒振动超过一万五千次的声音。著名音乐家梅纽因说,人耳难以想象的灵敏,对于人类的听觉与情感之间的复杂互动,起着巨大的作用,“听觉是个伟大的导师,它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与我们的所有心境和情绪相关联,接通人类的喜怒哀乐”(《人类的音乐》中译本)。著名的“基尔连摄影术”显示,当一个陌生人走进一个房间时,他的电场与房间里的人的电场,就会发生某种改变,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在人类体内深处,有一种产生于自身的从不会静止的振动声,那“是我们所有人音乐的核心”(同上书)。
鲁迅大概就是梅纽因说的“拥有富于想象力的听觉天赋的人”。“音乐肯定是起源于撞击我们双耳的自然之声,起源于我们静思时用我们的心灵之耳所听到的那些声音。”(同上书)“心灵之耳”不仅意味着发达的听觉能力,更关乎“心灵—精神感应力”。具有这种“异禀”的鲁迅,其作品总是蕴含着“浓烈而千旋万转”(钱理群语)的情感,其语言总是能传达出特有的丰神格调,其文学具有镌刻着鲜明个人印记的音乐性。首先,人们从其作品中可听到千姿百态而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声景”(soundscapes):狂人发出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撕心裂肺的近乎绝望的呐喊(《狂人日记》);乌鸦于死一般静中“哑—”的一声大叫,然后张开两翅箭也似的飞向天空(《药》);小尼姑的哭声中混合着阿Q十分得意的笑,以及酒店里人们的九分得意的笑(《阿Q正传》);毕毕剥剥连绵不断的鞭炮中,夹杂着送灶爆竹的钝响(《祝福》);一匹受伤的狼深夜里在旷野中长嗥,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孤独者》);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宛转悠扬的横笛(《社戏》);鸣蝉在树叶里长吟,油蛉、蟋蟀在泥墙根低唱和弹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长妈妈高兴地告诉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买来了(《阿长与〈山海经〉》);浩浩荡荡洪水包围中文化山上传来学者们的话语:“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 K”(《理水》);在悲哀的喇叭中出场的女吊慢慢唱道:“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女吊》)……
自然还有那些歌谣俚曲,《长明灯》结尾孩子们唱着“我放火歌”,《偶成》所引乡民给戏班“群玉班”编的歌;而最妙不可言的,则是堪称神来之笔的《铸剑》里那三首半楚辞体“哈哈爱兮歌”: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
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
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
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
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乎,
阿乎呜呼兮呜呼呜呼!
在复仇的凛然正气、对专制暴君的嘲弄戏谑以及与仇敌同归于尽的决绝气概中,散发出一种阴森狞厉的地狱气息。在一篇颇有趣的短文《“音乐”?》里,鲁迅以“戏仿”的方式,对徐志摩某些故弄玄虚的神秘诗歌理论及译诗作了讥讽:“……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唵,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介萝卜玎琤淜洋的彤海里起来。”文末大声召唤“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枭的真的恶声”。可以说,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哈哈爱兮歌”,就是鲁迅之所谓“真的恶声”。
恐怕也只有这种语体风格的吟唱,才最契合“声音好像鸱鸮”的宴之敖者的个性气质,也才能烘托出悲壮崇高而又血腥荒诞的复仇故事的气氛吧。当“胡诌的歌”尖利地唱起来的时候,一种闻所未闻、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复仇绝叫”,顿时轰响回荡于天地之间。
二
鲁迅作品中如下一类文句甚多:“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他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准风月谈·后记》);“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汉文学史纲要》里说的“大抵协其音,偶其辞,使读者易于上口”,也正是他自己对于语言音乐性的追求。
节奏和旋律是音乐的最基本元素,鲁迅作品的音乐性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到了多样化的呈现。上文所举例证可谓不胜枚举。鲁迅“语感”极好,他非常清楚汉语一字一音、形式整饬、单音节词多、有声调变化的特性,并以炉火纯青的语言造诣和文字技巧,进行戛戛独造的艺术创作。他极为擅长以音韵和节奏的丰富变化来编织文字、表意抒情,不愧是中国作家中罕有其匹的语言巨匠。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伤逝》中这些具有浓烈激越、深沉婉曲的抒情意味的句段,无疑是诗的,也是音乐的。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开篇这一引起歧义的语段,叠句而兼尾韵,最后一句字数稍多,使语言节奏沿着舒缓方向进一步向前伸展,进入一种具有沉思默想的语调。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鲁迅语)的书写策略中,恐怕不但有意义表达的精确、别异的需要,也有由节奏韵律的变化而生成特殊音乐感觉的考量。
《故乡》中母亲对“我”提到闰土就要来时,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连续采用了长句,行文一下子变得很缓慢,节奏纡徐舒展,“我”也随即沉入到对往事的追忆中,重返早已逝去的故乡的美好梦境里,语言形式十分契合回想旧事故友的情感表达需求。作品结尾的几个段落写“我”乘船离开故乡,仍然基本采用了比较长的语句,恰如其分地营造出一种冥想深思的氛围,以抒发对未来故乡民众应过上未曾有过的新生活的祈愿;徐舒的节奏又与船底潺潺流过的水声产生了一种和谐对应的效果。
但有时在鲁迅笔下,较长的文句又可能发生另一种艺术效应。《记念刘和珍君》第五节在具体详尽地描述了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三位女性中弹牺牲的情形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如下两句:“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前一句共二十七个字,是个相当长的单句,在这里时间不仅减慢了、拉长了,而且几乎是凝滞了、停顿了,宛若一个很长的慢镜头,一段沉重的、极缓慢的“壮板”(Grave),这就把刘和珍等三位女性遇难的细节、场景、过程,逼真生动地呈现出来:她们先后中弹,趔趄了一下,身体摇晃着,竭力挺住站稳,想互相救助搀扶,但还是慢慢地倒了下去,重重地落在地上,又继续挣扎着,最终停止了呼吸。请愿学生在执政府前遭到虐杀、喋血的真实场面,鲜活真切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作者大哀痛、大愤慨的感情自然也都隐含在这个长句之中了。
《怎么写(夜记之一)》中的一段文字,则以缓慢而宁静的速律(Agiato),抒写自己一个人深夜里在厦大图书馆楼上的生命感受和内心体验,具有含蓄蕴藉、沉郁深幽的浓厚抒情意味:“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往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比喻、对偶、排比、复沓等多种修辞杂用,词句长短交替,节奏感极强,高低错落,跌宕起伏,抑扬顿挫,韵味悠长,千回而百转,宛如一首柔美深挚、婉转低回的“夜曲”。以酒比静,已是极为精绝的一笔;对悲苦、有无、实虚等各种复杂情绪、幽微心曲,又体察深细入微;情感的抒发、意象的营构,达到了兴会淋漓、出神入化的境界。简洁、凝练而又华丽的语言,就像独奏小提琴的华彩乐段,令人不禁想起混合着激动不安的旋律、优美迷人的气息以及热烈憧憬的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柔板)。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这也是生活”……》)这也是鲁迅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段文字,堪称音乐感极强的沉郁华美的“生命咏叹调”。这个意义丰厚深邃的语言“意群”,运用对偶、排比、复沓、押韵等诸多语言元素,编织出一个形式精致和谐的旋律“乐段”,造成一种波澜起伏、低回婉转、错综变化的阅读感受,把鲁迅病中复杂的生命体验、微妙的情绪波动,以及浩阔深远的人生感悟与哲理思索,表达得深挚激越、酣畅淋漓、格外动人。在十七个语句中,“我”字或居句首或嵌句中,竟反复出现了八次,但读来毫无单调重复之感。这一独特的语言节奏/旋律结构,是鲁迅生命意志的强烈体现、主体意识的鲜明表达与生命力的自由显示,宛若一个异常明亮、突出的音符,出现在静谧气氛中的“充分、宽广、缓慢”(Largamente)的乐段里,用法国低音号幽幽奏响,又不断重复再现(变奏),作者情感的起伏律动与思想的不断深化,于是以这种富于变化的声音节奏及旋律的方式,出色地加以艺术模仿和完美呈现。
三
美国学者威廉·莱尔以《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为题,分析过鲁迅小说结构的若干特点:重复,民谣式地反复使用同一词语、道具以至人物,建立起故事的基本框架;运用“封套”,把重复因素置于故事或情节的首尾,使其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声响与寂静相对比,声响在寂静中爆发,最后再回到寂静,表示故事的开端和结束;静止与行动相对比,故事开始时种种人事纷至沓来、进入行动,结束时又回到原来的静止状态。(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其实,这几点亦皆可视为鲁迅小说音乐化的具体表现方式。
如其所述,《药》的整个故事在寂静中开场,平稳地推进,到第三节发展成渐强音(茶馆一天最忙碌的时刻),然后缓慢下来,最终在渐弱音中结束故事。《肥皂》主要的重复因素是两件道具(肥皂和字典)、一句话(“咯吱咯吱”),作品始于四铭回家交给四太太一块带香味的肥皂,终于四太太用这块香肥皂洗脸,两块肥皂即形成了典型的“封套”。而《示众》的“封套”则是卖包子的胖孩子,小说开始于宁静并有睡意的街景,胖孩子的出现打破了宁静,最后又以返回宁静的方式告终。
实际上,鲁迅许多小说采用的大都是他所钟爱的这种“音乐结构”模式:《风波》开头和结尾,都是临河吃饭的土场上,加上诸多不断重复、贯穿始终的音乐性元素,如九斤老太不离口的“一代不如一代”,七斤不离手的烟管,六斤的饭碗,赵七爷的竹布长衫,以及辫子的有无、皇帝坐了与不坐龙庭等等,整个故事因而形成了一个结构精妙完整的 “音乐建筑”。其他如《祝福》开始并结束于鞭炮声中雪花飞舞的除夕之夜;《孤独者》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离婚》则是以庄木三及其女儿爱姑与他人的对话相始终。
鲁迅曾自称是“散文式的人”,然而他的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具有高度的“诗化”特征,“文思”不仅与“诗思”亦与“乐思”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有学者认为《伤逝》就是一部由四个乐章组成的意蕴丰富的“交响诗”(张箭飞《〈伤逝〉的诗性节奏》)。此外,《社戏》犹如“牧歌”,《夏三虫》似为“谐谑曲”,《夜颂》堪称别具一格的“夜曲”。《奔月》《铸剑》分明都是高亢深沉的“奏鸣曲”。而《野草》则是鲁迅直逼魂灵深处、探究自我生命哲学的“组曲”,像极了肖邦的《二十四首前奏曲》(作品23)及其最著名的几首夜曲,其中《雪》显然是“音诗”,《好的故事》无疑是抒情“浪漫曲”,《秋夜》也是“夜曲”,《过客》和《这样的战士》皆为“叙事曲”,《影的告别》的风格则是“变奏曲式”的。
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早就注意到,鲁迅小说仿佛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椭圆的焦点,又像平行线,是那种有既相约又相斥的作用力的东西(《鲁迅》中译本)。这也就是苏联学者巴赫金所谓的“对话性”和“复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译本)。鲁迅笔下常见的两种乃至两种以上“声音”“对话”的这类现象,实际上就是音乐里的“和声”和“复调”。这是鲁迅作品音乐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
中国古代文论讲言意之别,有“诗无达诂”之说。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语言文字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其色彩、声调、韵味、节奏、旋律,即音乐性来感受和体悟的。鲁迅认为学术以启人思,文学以增人感。“音乐比大多数言词能更深切地触动我们的情怀,并使我们用全身心来作出回应。”(《人类的音乐》中译本)鲁迅对汉语的高超的感悟力和把握驾驭力,创造了一种具有起伏跌宕、千姿百态、循环往复、百转千回的旋律和美感的语言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作品的思想艺术表现力,强化了他的文学的情绪感染力和精神召唤力。
鲁迅在作品音乐化方面的独创性追求、卓越建树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坛上恐怕依然是无与伦比和难以企及的。
二○一六年五月三日于山海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