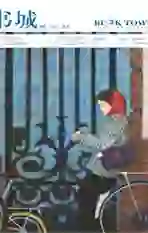“吾面却与何人同”
2016-09-22张宪光
张宪光
一、“镜”中人
芥川龙之介《澄江堂杂记》引用过法朗士的一句话:“我知晓人生,并非与人接触的结果,而是与书接触的结果。”芥川无疑是法朗士的同道。可是想要通过书本认识生活,非博览善思不可,芥川自称有好书癖,《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记载了诸多书事,也是很自然的事。小学时代,他最常流连的是一家租书店:“我认识岩见重太郎是在本所竹仓的租书店。不,不仅如此。认识羽贺井一斋、奸妇妲己、国定忠次、佑天上人、万事通阿七、发结新三、原田甲斐乃至佐野次郎左卫门,总之认识那些闾巷无名天才传说中的人物,全都是在这家租书店。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家夏天西晒的窄小店铺。檐端挂着一个玻璃风铃,下面提溜着诗签。另外,靠墙堆放着几百本讲谈速记书。最后在陈旧的苇编门后,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在做花簪。啊,我对那家租书店该有多么怀念。教会我文学的,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图书馆,而恰恰是那家萧条的租书店。我从码放在那儿的书籍里,得到了一生也受用不尽的教导。而学到超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尊严,也是其中之一例。诚然,超人一词可能是读了尼采之后才有的词汇。但是超人这个东西—伟大的岩见重太郎啊,你腰别传家宝刀,横眉面对天下的英姿,早就把毅然决然下山而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伟业,灌输到我未来的心灵里。那家租书店怕是早就没了踪影,可岩见重太郎直到如今,还在我的心中保持着勃勃的生命。他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悠然地扇扇子,一边……”(《偏颇之见》)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读泷泽马琴的《八犬传》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他最喜欢的是《西游记》,“这样的杰作在西洋一篇都找不到,就连班扬著名的《天路历程》,也无法同《西游记》相提并论”。读罢《水浒传》,曾将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全部背诵下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在镇上唯一一家兼售五金的书店—那所平房如今早已衰败不堪,几近坍圮—流连忘返的情景,当时是多么痴迷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小人书。原来高冷的芥川,也如我等庸碌之辈一样,是从英雄传奇开始他的读书生涯的。一九二一年夏天,芥川来到中国,寻找他记忆中的鲁智深、武松们,带给他的只有深深的失望。后来芥川写作《戏作三昧》,希望通过写作“荡涤人生的残渣”,其中的想象一定还存留着少年时读马琴的记忆吧;—我想在这篇小说中,他并非站在生活的外侧“静观漩流”,而是置身于“漩流”之中。
倘若芥川的阅读止于英雄传奇,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初中以前,他已开始阅读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樗牛的《平家杂感》和小岛乌水的《日本山水论》,以及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泉镜花的《风流线》和绿雨的《霰酒》,并且用蹩脚的英语啃外文原著了。初中毕业后,读了大量书籍,喜欢“王尔德和哥且那种华彩绚烂的小说”。十八岁进入东京第一高等文科学校,主修英文,开始大量接触屠格涅夫、易卜生、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其一九○九年三月六日致广獭雄信中述当时苦读情形云:“恼人的是,纵使西洋名著,在东海竖子手中也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或翻辞典或查资料,仍全然不知所云,只好逐一标明语义,让事件好歹显露端倪。继而复读三遍,以期窥见整个事件首尾。更有甚者,序幕部分俱是暗示之语,令人苦不堪言。”当时读的是易卜生象征主义剧作《罗斯莫庄园》。至于他在此间阅读的详情,有兴趣的可以参读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二日致浅野三千三的书简,他对王尔德、梅特林克、斯特林堡、托尔斯泰等作家的熟稔估计要让许多人自叹弗如。进入大学后,他一方面如痴如醉地读了《珠村谈怪》《新齐谐》《西厢记》《琵琶行》以及日本的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等本土作家的作品,一方面依然醉心于斯特林堡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并在朋友的煽动下写作了《丑八怪》和《罗生门》。与其他作家相比,芥川显然不是日本“物哀”传统的继承者,虽十分熟悉日本的古典,也具有一位作家应有的卓越“感觉”能力,可是他所关注的问题、思考的方法、写作的技巧毋宁说更具西方色彩,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联系最密切、思考最深邃的作家之一。一直到他写作《侏儒警语》时,这些西方小说家还像幽灵一样闪现在他的脑海里,甚至在小说《手绢》中斯特林堡的著作直接登场,成为解构日本武士道的利器。
芥川并不是一个藏书家,没有为书而一掷千金,他的藏书只是“像落叶聚集到风窝里一样”,自然地落到他的书架上,而且“摆得乱七八糟”。据《关于书的事情》介绍,他藏有一八八四年版《各国演剧史》、一八六九年《天路历程》汉译本、约翰·穆莱出版的拜伦诗集(1821年版),以及明治初年出版的小说五十部左右,虽无什么稀罕物,芥川谈起这些书来依然津津有味。从他的随笔来看,他还向旧书店卖过书。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德语成绩出众,当时的德国驻日大使赠给他四册阿尔恩特诗集,后来被他卖给了郁文堂旧书店,得价六元。
芥川曾说过:“书架上的书好似镜子,能照出书籍主人的内心世界。” 考虑到尚无一本完备的芥川中文传记,芥川所读、所藏的这些书,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内心世界,而且为大正初期登上文坛的一帮日本作家提供了一个阅读史方面的样本。
二、诗评家·诗人
世人皆知芥川为小说家,不知其为诗评家、诗人。日人小室善弘曾在《芥川龙之介的诗》一文中作过统计,芥川共创作俳句、短歌、新体诗、汉诗近千首,并且著有多篇诗论。他对短歌的鉴赏,受斋藤茂吉影响颇深,甚至左右了他的“精神自序传”。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芥川偶然读到了斋藤茂吉的初版诗集《赤光》(1913),为他打开了诗歌鉴赏之眼,并在《偏颇之见》中记下了这段经历。芥川认为“近代日本的文艺一方面横向模仿西方,另一方面纵向地致力于在日本土地上扎根的独自性的表现”,而茂吉则是这两方面最完备的个人,是具有象征性的一个人物。芥川从中学到了认识所有文艺之形式美的眼睛和耳朵,否则也许连“懒起恋床笫,搅梦是春雨”这样的美妙诗句也会不痛不痒地放过。茂吉诗云:“荒原亮闪闪,一条道路现,或许性命丢,于此无怨言。”又云:“一条大路亮堂堂,此生此路不彷徨。”似均得益于梵高的《播种者》,有一种沉痛奔放之气。在俳句方面,芥川曾拜高滨虚子为师,且得益于饭田蛇笏很多。有一次读到蛇笏的俳句:“得绝症,心境平,美指拨火桶。”不由得被其感染,并开始学习写作,写下了“娼女悲,十指白,恰似白皮葱”这样的俳句。再如:“春雨细无声,放眼望,积雪皑皑甲斐山。”芥川借这首俳句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时住在甲斐国的蛇笏的思念。如前所述,芥川最欣赏的俳句大师是芭蕉,对小林一茶则时有贬词。以芭蕉为代表的元禄人的俳句,“面对自然的人生”,而“小林一茶则面对现世,即今人所谓‘生活”。在芥川看来,俳句只是一茶“悲哀的玩具”,不如芭蕉的作品在描写自然的字里行间本身即与生活有着神妙的勾连,而一茶则似乎一直未能领悟“此中醍醐”。或许可以说,一茶的诗太粘滞于生活,而芭蕉则将自然、人生融通了。此外,芥川还认为芭蕉的俳句可以将“诉诸眼睛的美与诉诸耳朵的美微妙地结合为一体”。相比之下,他似乎更重视俳句的“诗调”,即语言的音乐性,强调“打开耳孔”。

芥川小说写的是东方故事,技法追步西人,而诗歌则全然是东方的、日本的。虽然有时候他也把一些俗物写入俳句,但大体还是追步松尾芭蕉、正冈子规的路子,追求风雅之“寂”和言外之趣。自高中时代开始,他就通过信件、明信片将自己所作俳句寄赠友人,这似乎是当时的一种风尚,阅读全集第五卷,几乎页页皆有其短歌俳句。一九一五年三月,曾寄赠藤冈藏六俳句十六首,其中之二云:“人生如此苦,如今识尽苦滋味,迷途入‘泪谷。”颇能反映其人生观念。五月曾寄给恒藤恭以紫藤花为题的俳句二十九首,其三云:“不知在何时,紫藤悄悄开始落,花落药罐上。”末句尤有禅寂味。写作《枯野抄》时,也曾大量制作俳句,如:“自斟自酌菊花酒,白衣犹似王摩诘。”意境也很悠远。他曾说:“我未曾受过吟诗作赋的训练,故无自信成为《紫杉》撰诗人之一,仅于创作俳句方面付出常人之辛苦,自认可与虚子相提并论。不日将在某刊物发表本人俳论,即可据此考察我的俳句。高傲之处相似,也有这么一两首自鸣得意。信中难以尽意,不如早赴长崎,掀起俳论大战。”谈起自己的俳句,他还是颇为自信的。然而,那只是他小说写作间隙的一种调剂,为枯寂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而已,并未能如他自己所期待,带给俳句新的贡献。
芥川对汉诗有精深的理解。早在十八九岁就这样评论晚唐人的诗:“今晨细雨霏霏,独坐翻开许丁卯诗集,但觉愁情如雾,扑面而来。其怀古七律,尤为格调哀伤,较之李义山更为细腻,较之温飞卿更为哀艳。青莲少陵以降,以七律独步斗南,良有以也。”立论颇异于前人。集中汉诗虽不多,时有佳作。一九二○年三月,曾作五绝一首:
帘外松花落,几前茶霭轻。
明窗无一事,幽客午眠成。
自以为写得有“悠悠然的味道”,遍赠友人,自夸不已。又曾作七律一首:
似雨非晴幽意加,轻寒如水入窗纱。
室中永昼香烟冷,檐角阴云帘影斜。
案有新诗三碗酒,床无残梦一瓯茶。
春愁今日寄何处,古瓦楼头数朵花。
此诗为小岛政二郎(号古瓦)所作,属于他的得意之作。他自以为写俳句、短歌要比小说容易,要显得更“风流”些,其实未必。但诗在芥川的生命中是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这一点几乎被人完全忘记了。
三、“尿雨者”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写了不少煞风景的事,既有中国的,也有别国的。在上海豫园,芥川看到的是如下景象:“沿着这条摊床街走到尽头,声名远扬的湖心亭一望在即。说起湖心亭应该很壮观,然而,其实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的颓败至极的茶馆。亭外的湖水中漂浮着墨绿色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湖水的颜色。桥面的两边砌着古怪的石栏。我们来到这里时,正好碰见一个穿着浅葱色棉布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写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用菊池宽的话说,我屡屡在小说中使用厕所一类的下等词语。因为我也写俳句,所以据推测说,这是受到芜村的马粪和芭蕉的马尿潜移默化所致。我当然不会对菊池的说法充耳不闻,但是及至中国纪行,因为场所是下等的,如果不时时地打破礼节的束缚,则无法作出生动的描写。如若不信,无论是谁尽可以自己写来试试看。—言归正传,那个中国人正悠然地往湖内小便。陈树藩意欲谋反,白话诗的流行已日渐衰微,日英续盟即将缔结……凡此种种对那人而言都是不相干的。至少在他的态度和面孔上,有着一副只能让人作如此判断的悠然。一孔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备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芥川的描写,曾让而且至今依然让一部分国人不快,然而看一看街边路旁依然常见的如斯景象,这不快是不是稍微减弱几分呢?另一件煞风景的事,发生在一个秃头美国佬身上。芥川抵达杭州后,一直在谷崎润一郎式的浪漫主义、古典想象与眼前的糟糕现实之间折返,一边是玫瑰、微雨、孤客之心,一边是 “五六个男男女女的美国佬正围坐在台阶的桌子上,一边狂饮一边放声高歌。特别是那个秃头先生,抱着女人的腰,和着音乐的节拍,好几次都险些连人带椅一块倒在地上”。更让芥川难以忍受的是:“那个秃头的美国佬走到我们旁边一停下,就马上背对着大门,旁若无人地撒起尿来。”芥川心中不由燃起了“十倍于水户浪示的攘夷之火”。不仅如此,西湖这个稍怯春寒的中国美人,“已经被岸边随处修建的那些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植下了足以令其垂死的病根”。并且对西湖的俗恶趋势,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再过十年之后,极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林立在湖岸的每一座洋楼里都有美国佬烂醉如泥,每一座洋楼的门前都有一个美国佬在站着小便。”芥川所描写的这两条小便,与美妙的风景构成了强烈的对冲,符合布鲁克斯所说的“悖论的语言”这一诗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整本《中国游记》充斥着的正是这种悖谬的隐喻:古典与现代,浪漫主义想象与丑陋的真实,诗性中国与小说中国……当他来到浔阳江头,便不免要去寻找《琵琶行》中的流风余韵,结果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篷里伸出来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唐代的船夫估计也干过同样的事,而白居易避开了它,芥川所到之处,似乎着意于发现现代中国的堕落。是的,这种堕落也许从唐代的胡风煽炽就已经开始了,昔日的魏晋风度、唐宋华彩,在芥川的眼中只剩下残山剩水。再如《杂信一束》,也是浓缩的一个类似文本,芳草萋萋的鹦鹉洲变成了煞风景的木材堆置场,洞庭湖变成了烂泥田,万里长城上最显眼的是一个乞丐童子。诸如此类,莫不造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滑稽。芥川在开始中国旅行之前,里见弴在其行前致辞中说:“中国人在古代时期很是伟大。然而古代伟大的中国人现在突然不伟大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到中国去后,切莫只看过去中国人的伟大,还要找到如今中国人的伟大之处。”芥川也有这样的打算,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让他深深失望。

其实,芥川也是一位“尿雨者”。他的《人物记》写到将“谨严贯穿到细微的一言一行之中”的好友恒藤恭,从不往楼下“尿雨”,而“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芥川则“并非全不尿雨”。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尿雨?”恒藤说:“假如让别人给尿了,我会为难的。所以我不尿。你为什么尿雨?”我回答:“让人家给尿了,我也不怕,所以我尿雨。”
《岛木赤彦》篇中,芥川和斋藤一起去《紫杉》发行所,两人一起在“空瓶堆积如山的下路左侧撒了一泡尿”,芥川又忙不迭地声明此事的发起人不是他。芥川在小说中有点过度严肃,给人苦兮兮的印象,具有语言洁癖,对人世的蝇营狗苟一脸鄙夷,居然也干过这样有失风度的事,不禁让我辈感到亲切了许多。
不过芥川的“尿雨”和《中国游记》中的尿雨者给我们的印象太不一样了,前者带点名士风度,后者则带着强烈的反讽和象征意义。这自然与《中国游记》的写法分不开。同样是对杭州西湖的书写,芥川明信片中的西湖则经过了另一种筛选。五月二日致松冈让:“西湖小巧玲珑,美不胜收。此地盛产老酒与美人。‘杭州西湖暮春夜,我邀苏小掏耵聍。”五月四日致南部修太郎:“来到杭州,眼下在‘新新旅馆一室豪饮特产老酒。窗外是暗无星月的西湖,可见熠熠灯火。乡愁油然而生。”五月五日致下岛勋:“西湖美景几似明朝古画,夜晚湖面灯火闪动,令人称奇。杭州是著名老酒产地,但像我等滴酒不沾者却无从品味。盘中犹剩东坡肉,春燕呢喃闹堂前。”不知芥川发了昏,还是译者发了昏,连喝酒一事也自相矛盾,此姑不论,明信片中的杭州还是富于诗情的。这自然是由明信片的载体、篇幅所致,但至少与《中国游记》的味道有些异样。芥川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致佐佐木茂索的信里说:“《上海游记》之所以诸体兼备,皆因此法轻松自如之故。写小说如走下坡,写游记如履平地。若按常套写作,笔者最感厌倦。”可见他的《中国游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写实,而是有意无意地掺杂进了小说的写法,读起来不似“如履平地”,而是可以感觉到文字底下涌动着的“不平”。五六年前在《书城》上读到邵毅平先生的《芥川龙之介与洛蒂:分裂的中国与日本形象》,方才领悟到芥川的《中国游记》有意无意地模仿了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擤鼻涕、扔花等诸多细节何其相似乃尔。洛蒂在审视着日本,芥川接过了洛蒂的接力棒,转过来审视起中国,而且更进一步,赋予文本更丰富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四、偶像破坏者
芥川龙之介曾说:“面对菊池宽的作品时,眼前仿佛骤然展开了阴天般的萧条景象。令人悲哀的自我矛盾阴影无处不在,或可说利己主义的寒风扑面而来。”“菊池宽作品,首先具有鲜明的特色,毋庸赘言,即作品中跃动着理智的火花。他不断清拭理智眼睛上的阴翳,不知疲倦地透彻剖析眼前出没往来的人间万象。”(《〈心灵的王国〉跋》)说实话,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时我心里产生的正是这样的感受,弥漫着对人性的失望,只是在文字上相当冷静克制而已。也许芥川从菊池宽作品中洞察到的东西,正是他身上已有的东西。
芥川对“稀世天才”松尾芭蕉的评论,似乎也验证了前述观点。他对芭蕉似乎抱持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面由企羡而滋生出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一面又夹杂着他所特有的怀疑主义的腔调。他敏锐地指出,在芭蕉身上,“诗人性情”要比“隐者性情”更强劲,他“爱的是没有彻底成为隐者的矛盾的芭蕉”,尤“爱他的矛盾之大”。他对芭蕉诗调、俗语、画趣、对汉诗的活用等多方面的分析,表明他对芭蕉的俳谐下过很深的研究功夫,故而可以洞幽烛隐,绝非肤泛之谈。除了技巧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了隐者芭蕉与时代的关系:“芭蕉一点儿也不是孤立于时代之外的诗人。不,毋宁说是一个将自己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时代之中的诗人。”并且“是一位继《万叶集》之后最切实地把握时代、最大胆地描写时代的诗人”。芥川之所以这样说,在于芭蕉的某些俳句“简直写尽了元禄时代的人情”,“不是淡漠枯寂的隐遁者的作品,而更像面对仿佛出自于菱川浮世绘中的女子或小伙子的美貌,震颤着敏锐感受性的多情的元禄人作品”。这样的评论也不免让我疑惑,这到底是在谈论芭蕉,还是芥川夫子自道。
不仅如此,芥川还在《芭蕉杂记》中强调了芭蕉的另一个形象:“芭蕉是一个根本不在意一般习俗的偶像破坏者。不用说,经他的手破坏了许许多多的偶像。发出那‘俳谐乃《万叶集》之心。丝毫不亚于唐、明及一切中华之英杰的豪言壮语者,正是芭蕉。扬言‘世间并无读了无益之书,比起儒佛之书,似应读些日本书以及其他净琉璃之书者,也是芭蕉。一语道破交友原则,称结交其他门派‘无碍,只有盗贼和赌徒才不应结交的,还是芭蕉(不,芭蕉对待盗贼和赌徒,未必像蛇蝎一样加以排斥)。”我想,芥川眼中的芭蕉未必完全符合芭蕉的本相,折射出的很可能是芥川本人关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理解,而且他自己也隐隐以偶像的破坏者自居吧,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联系最密切、思考最深邃的作家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芥川是一位日本古典的重构者,也是一个文化的解构者,总是用一双怀疑的眼睛毁坏着偶像,破坏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幻象。他所解构的对象,包括神话人物桃太郎,包括被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包括日本武士道的标杆性人物大石良雄和武士道的鼓吹者新渡户稻造,当然他也没有放过基督教以及古典中国的幻象。这或许才是芥川龙之介特别卓异之处。
芥川有一次接受《新家庭》杂志约稿,明确表示“不喜欢任何偶像崇拜”,“无论英雄崇拜还是天才崇拜”,同时“也厌恶极易导致偶像崇拜的感伤主义”,这恐怕正是在芥川小说中看不到感伤主义的原因。对于日本的古代英雄,他似乎公开赞美过的仅有少数人物,岩见重太郎是其中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芥川以为“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为了驱使像家畜一样的我们,好像也时常戴着假面具”,而岩见重太郎则不然,他不是一个偶像,他在“打破牢狱的同时蹂躏了人间的法律;接着,又在铲除了狒狒的同时,蹂躏了偶像的法律”。换言之,世人所知不多的岩见重太郎,如素戋明尊、巴枯宁这样的豪杰一样,是“单行独步之人思想生涯的象征”,“蹂躏了人间的虚伪和神明的虚伪,想来将来还会义不容辞地蹂躏一切的虚伪”,他的勇猛过人“本身就有着给我们末世众生的心带来莫大欢喜的特色”。芥川无视社会、文化对生活的设置,试图铲除日本文化中的“狒狒”,是一位查拉图斯特拉、岩见重太郎式的人物。
接下来笔者还想再追问一句:芥川龙之介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解构”呢?答案或许可以从《偏颇之见·大久保湖州》一篇中芥川的解析中找到。他说:“英雄崇拜者的英雄,与其说是英雄,倒不如说是神更妥当些。道德主义者的英雄,即使不是太好,可能就是太坏。但是他们的英雄只要保持了某种统一性,即使没有多少人性味,也显示了玩偶味的可爱。可是一部分传记作者的所谓很有人性味的英雄,就连这种可爱劲也没有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所创造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更是一个最令人不快的怪物。是比那所有引诱了圣安东尼的地狱的喽啰们都更加让人不快的怪物。”而湖州不仅是一位有趣味、有个性的历史学者,更可贵的是在《德川家康篇》中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人”,即凡人的一面与非凡人的一面两者相融合,“于英雄之中,指出了一个默默营生的完整的人”,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同情和理解力。湖州这样写道:“天自不言,而使人言。然,人声未必与天声一致,人的褒贬毁誉时常与天公的公裁龃龉。人世最可怜者,为生前不闻天声而人死者。后人不可不代天而成为死后的知己。”因此芥川认为湖州为英雄“去魅”,将人声、天声二者合一,并且“湖州所以是湖州,在他从德川家康这个英雄身上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之前,就已在所谓属于未来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美术家、史学家、哲学家、企业家等一群人中发现了完整的人”。正是基于“完整的人”这一看法,芥川才成为了一个偶像破坏者,而他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没有得到正视。
五、结语
仅读芥川的小说,会感觉到芥川理智的“冷漠”,会认为他是一个患有忧郁症、苦兮兮难得一笑的人;然而通读《芥川龙之介全集》,你会发现芥川有趣且富于幽默感。他喜欢书画拓本,声称“做文章,恋慕女人,进而欣赏古玩”,“旦暮死去,亦可瞑目”,喜欢读中国淫秽小说,善于戏谑调侃,擅辩,写的论文、杂评皆不乏锋利之处。你要了解全面的芥川,不可不读《肉骨茶》《野人生计事》以及《人物记》等篇。芥川小说呈现的是他的理性深邃的一面,随笔呈现的是他随性日常的一面,后者更真实而可爱。其《〈各种风骨帖〉序》云:“见诸公之画,如见诸公之面。眼横鼻直,样态相似。骨骼血色,情状不一。吾笑杜陵老人,见画中之马而不见人。秋夜灯下翻开此册,一面夭夭,一面垂老。借问灵台方寸镜,吾面却与何人同?”吾读《全集》,颇有同感,因此尝试为此公绘出另外几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