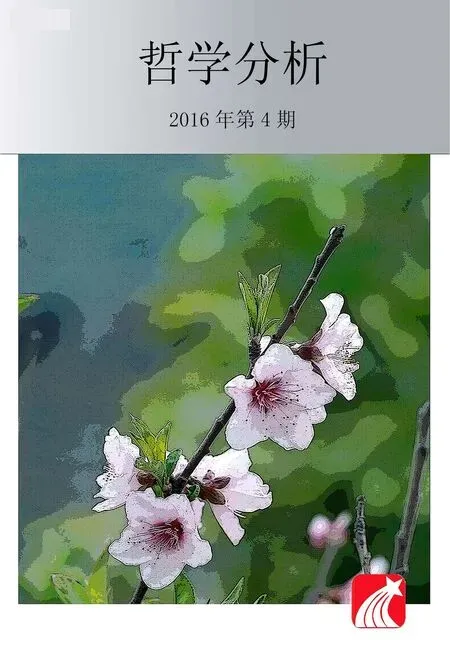在物性与意向之间看技术人工物
2016-09-16李三虎
李三虎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在物性与意向之间看技术人工物
李三虎
当代技术哲学在经历“经验转向”之后,开始把技术人工物作为分析的学术焦点之一。按照荷兰学派的研究纲领,技术人工物包含结构和功能双重独立属性。但当考虑结构—功能关系时,却发现分析上存在诸多困难,此即技术人工物在本体论上的“硬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是硬问题,是因为目前人们启用的构制理论和随生理论,均采取了结构—功能二元论描述方法。其实,就技术人工物来说,技术哲学应采取一元论解释方法,将功能(甚至非功能)意义作为被解释对象,而把与此相关的一切因素,如结构或物性、目的或意向、使用和背景等作为解释要素。这种方法不仅能够避免本体论上的“硬问题”,而且能够诉诸人对技术人工物的经验和使用背景,在物性与意向之间,围绕其功能和非功能意义做广泛解释。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人工物与自然物的不同,便不再是如亚里士多德那样指认的外在目的或功能特征,而是被赋予的包括功能和非功能意义的内在规范性。
技术人工物;物性;意向;功能承担;规范解释
当代技术哲学在经历“经验转向”之后,开始把技术人工物作为分析的学术焦点之一。在实在论意义上,技术人工物不完全是独立的实体或工具,而是一种现实的间性存在或关系实在。技术人工物实在本身,意味着人与物的同时在场。物的在场是指人工物的物质基础、物理构成、结构或物性,人的在场是指人的人工物制造和使用行为,包括人的目的、需求和意向以及人工物的设计、功能和使用等。在哲学上,我们追问人的在场问题,是要回答技术人工物何以具备某些功能或人何以对物性进行操作和创造等问题。但是,技术人工物的有意识的制造、使用和功能并不直接取决于其物性,物性仅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能以功能和非功能意义而存在。也就是说,技术人工物意义不仅源于其物性承载,而且依赖于其使用者及其所处社会结构创造的条件和环境。技术人工物既是物理客体,又是社会或文化客体。鉴于这会导致一种对技术人工物的二元论描述,所以需要围绕技术人工物的物性与意向的价值关联提供一种整体论说明。
一、本体论上的“硬问题”审视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人们在实体理论意义上,已经习惯地把人工物看作是有意识地制造的、服务特定目的的客体或工具。在当代技术哲学中,围绕技术人工物存在着诸如自然事实/使用实践、物质基础/社会建构、物理结构/社会功能、工具手段/目的意向成对的描述概念。从本体论上看,这些概念的存在使人们很容易将技术人工物刻画为一种具有二元属性的实体或客体,也即认为技术人工物由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构成。人工物作为自然事实的存在,虽然依赖人的参与,但要参照其物理结构或物性;人工物作为社会事实,则直接地依赖于人的制造、使用、目的和意向活动。自1998年以来,荷兰学派(主要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埃因霍恩理工大学)的技术哲学研究,以一种技术实体描述的战略姿态,提出了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双重属性研究纲领。如果超越具体的结构—功能双重属性描述,上升到本体论上来,那么结构—功能关系分析将显得非常复杂和困难,此即技术人工物在本体论上的“硬问题”。
在哲学史上,本体论的硬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哲学议题,而是与传统的心—身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存在一定联系。自笛卡尔以来,心—身问题长期困扰人类的智力活动。许多哲学家对此曾指出许多解决方案,争论不休。在当代心智哲学中,查默斯(D.J.Chalmers)提出了“意识的硬问题” (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毋庸置疑,有些有机体是经验主体。但是,这些有机体系统如何成为经验主体仍然令人困惑不已。当我们的认知系统参与视觉和听觉信息处理时,我们便拥有了视觉或听觉经验。为什么会有深蓝的质感、中央C音的感动?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会存在类似享受或情感经历的东西呢?尽管大家都认为经验来自物理基础,但我们对经验为什么和怎样会如此发生却缺乏绝好解释?物理过程为什么会全然导致一种丰富的内心生活?无论是应该如此还是确实如此,这在客观上似乎都不太合理。①David Chalmers,“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Vol.2,No.3,1995,p.201.
这里所谓意识的硬问题,是指解释人的大脑作为一种有机体如何和为什么具有感受或现象经验——感觉怎样取得诸如味道、颜色等特征的问题。从本体论上看,这之所以成为硬问题,就在于它把人的大脑看作心智依赖的有机体。同样,技术人工物就其源于人的信念、意愿和意向而言,也是心智依赖的东西。
与查默斯的“意识的硬问题”类似,当荷兰学派解释技术人工物时,也提出了技术人工物如何和为什么拥有相应的现象经验的硬问题。当然,技术人工物的硬问题并不是心—身问题的当代翻版,因为心—身问题是关于人类心智与身体之间的本体论还原问题,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功能问题则是一个在制造和使用背景下的结构—功能整体解释问题。但是,这毕竟涉及对心智依赖物的哲学解释,所以它即便不是心—身问题的当代翻版,也与意识的硬问题相似,属于心—身问题的衍生问题。
那么,将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归结为结构—功能关系问题,究竟困难在哪里呢?在查默斯看来,意识的硬问题是相对于解释诸如辨别和综合处理信息、表达心理状态、全神贯注等能力的“简单问题” (easy problem)而言的。简单问题之所以容易解决,是因为它直接指明了自身的功能执行机制。硬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超越了功能执行的所有问题,为此必须要注意到,我们对所有与经验相近的认知和行为功能(直觉辨认、分类、内检、口头报告等),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有待回答,那就是这些功能的执行为什么会伴随着经验而发生?”②Ibid.,p.202.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也是相对于简单问题而言的。简单问题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技术人工物的目的、功能均能在“形式服从功能”或“结构决定功能”的关系下获得说明,但它的硬问题在于如下两方面的结构—功能关系解释困难③Wybo Houkes & Anthonie Meijers,“The Ontology of Artefacts:the Hard Proble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art A,Vol.37,No.1,2006,p.120.:
(1)双向不充分决定(UD)——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多重实现。技术人工物既存在着单一功能以不同结构实现的情况(即从功能到结构的自顶向下的下行情况),又存在着以单一结构实现不同功能的情况(从结构到功能的自底向上的上行情况)。
(2)可实现性约束(RC)——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多重实现限制条件。我们既需要解释从技术人工物及其功能推出其物质基础结论的可能性,反之亦然,又需要为物质基础与技术人工物的互动关系提供相应见解。
在荷兰学派那里,任何关于技术人工物的理论模型,都应当能够解释这两种现象。也就是说,UD和RC是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关系解释,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两个标准。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被坐实为结构与功能两个基本概念或双重属性。结构方面描述了技术人工物的物性,功能方面描述了它的整体状态。UD和RC描述的是,技术人工物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一些必然联系。如果说UD描述的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非一一对应关系的话,那么RC表现的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对严格关系。
意识的本体论硬问题辨识,是基于对心智独立与心智依赖的本体论区分。按照这种区分,技术人工物与自然物的不同在于,人工物的制造和使用受功能或意向指导,因此技术人工物是功能性的自然物。但是,这种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因为有些自然物,如哺乳动物的心脏等生物有机体,同样也是功能性自然物。由此人们会认为,技术人工物与有机体的不同在于,它作为一种功能性自然物,其实践功能是由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意向决定的——技术人工物依赖于目的、意向等人的心智状态。在这种意义上,所谓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实际上可以放大为物性与意向的关系问题。这虽然将诸如心智独立的动物世界甚至非人的无机世界与心智依赖的后像世界或人工世界给予区分,从而赋予人工物以高阶地位,但却无法解释技术进展带来的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的差异缩小现象。例如,计算机程序因与生物有机体一样能够产生变异、复制和相互竞争而被称为“数字有机体”,老鼠因植入的电极指导其行动而被称为“机器人鼠”、生物电池因利用微生物发电而被称为“细菌电池”,等等。这里的结构与功能或物性与意向之间的模糊性关系表明,技术人工物之为技术人工物,既不在其物性和意向的独立归属,也不在两者之间的机械性逻辑关系。因此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与其说是当代技术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关系实在的理论问题;对这一硬问题的哲学解答,与其说是对结构—功能关系的分析或描述,毋宁说是在物性与意向之间寻求价值关联的意义解释。
二、从二元论描述到一元论解释
将人工物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最早见于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有关“提修斯之船” (the Ship of Theseus)的故事。雅典人提修斯曾被派执行任务,他乘坐的是一条带有30支划桨的船。这条船之所以由雅典人一直保存到菲乐鲁斯(Demetrius Phelereus)时代,是因为他们把腐烂的旧木架换成新的更坚硬的木板。就此而言,这条船成了哲学家为人工物的生成或发生的逻辑问题提供辩护的持久例证:一方面认为它保留了原样,另一方面又争论说它已经成为一条新的船。在当代哲学中,罗威(E.J.Lowe)把普鲁塔克的故事转换为如下哲学问题①E.J.Lowe,“On the Identity of Artifact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0,No.4,1983,p.221.:
在某一时间t0,我们有船A。当它的构成部件一点一点地被新的部件更换后,到时间t1时,我们便有了由这些新部件组成的船B。在时间t1,也可以将旧部件重新组合,形成船C。B和C是明显不同的船,那么B和C究竟哪个(或它们任何一个是否)与A是一样的呢?
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解答是,它们都是一样的船。因为船的构成部件是否为原来部件,并不是决定船的身份或地位的充分必要条件。现在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时间t0不对船A进行部件更新,到时间t1时用这些部件组成船C*。在这种情况下,C*与A明显是一样的。这样,物质基础的一致性,便成为主张C*和A一样的充分条件。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条船会从t0保存到t1。这一例证突出了人工物构制的两个问题:一是历时问题,强调时间依赖的存在物是构成人工物的充要条件;二是共时问题,强调物质结构的存在是构成人工物的首要条件。这两个问题表明,复制物具有同等的物质结构,它们均要求把各种构制客体的物质性存在物作为人工物构制的原始来源,共同指向的问题是人工物的身份或特征是否持续保持并在创新和复制过程中传递下去。但是,由于复制物毕竟不再是原型实体,所以人工物发展的物性—意向关系便呈现出如下三个机制:
(1)传递机制,如果A = B和B = C,那么A = C;
(2)拆卸和组装机制,一个客体拆卸和组装能够确保不丧失其原有功 能;
(3)创新或变革机制,一个客体能随时间变化而保持其功能。
让我们按照以上三个机制,来看看对罗威人工物哲学问题的解答:B与A相同,服从的是创新或变革机制;C与A和B与C相同,服从的是拆卸和组装机制。在这种情形下,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必须要说B与A相同,而不是B与C相同。综合来看,罗威的人工物哲学问题在于,人工物可以参照物性加以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需要提供其他附加条件和标准。这当然也是荷兰学派以本体论硬问题为指导,启用构制理论(constitution theory)和随生理论(supervenience theory)进行结构—功能二元论属性研究的要求所在。
在哲学中,“构制” (constitution)是解释物质世界的普遍术语。贝克(L.R.Baker)为了赋予人工物与自然物相同的本体论地位,将其物质构制理论应用到人工物解释。在他看来,构制不是物质等同,不是部分—整体关系,因此物质之物与其构制之物并不等同。正如亚里士多德对人工物的本体论区分一样,他认为人工物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物,是因为它拥有自然物不具备的由其外部的生产者意向决定的人工性质(如实践功能)。贝克启用构制理论,就是要解释人工物作为物质实体在本质上何以具有这种“非内在性质”。贝克的构制理论之所以被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是因为他声称人工物具有本质性的功能属性。这样构制便成为一种偶然关系,如青铜本身即使不构成任何东西都可以存在,当将它用以构制人工物时,既可以做成雕塑品,也可以做成其他如酒杯、香炉等东西。为了解释这种偶然关系,他引入“基本种属” (primary kind)和“存留条件” (persistence condition)两个概念,认为人工物的物质构制基于如下思想①Lynne Rudder Baker,Persons and Bodies:A Constitution 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5,p.41.:一种人工物只有在使其所是的存留条件下,才能拥有其基本种属,具有某些本质属性或“专属功能” (proper functions),也因此才能成为“意向客体” (intentional object)。贝克尽管不接受仅仅按照物性解释人工物的思想,但他又把人工物的构制部件描述为自然种属:在物质意义上,人工物是各种部件的聚集。当然,他并未把人工物构制看作一种部分—整体关系,而是将它看作一种背景和条件(如意向行动、设计和使用参照等)关联物。沿着这些附加概念,贝克将其人工物构制理论表述为如下形式逻辑②参见Lynne Rudder Baker,“The Ontology of Artifacts”,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Vol.7,No.2,2004,pp.100—104。:
在t时间,物质聚合物A构成技术人工物X,当且仅当A的基本种属(如锄头构制的木棍和铁块)与X的基本种属(锤子),以及对实现X的功能F有利的环境或背景,使得如下情形称为可能:(1)A成为其基本种属(木棍和铁块)的专属聚合和X成为基本种属(锤子);(2)在t时刻A和X具有空间一致性;(3)在t时刻A处于对X的功能F有利的环境。在这些情形下,A从一个衍生的人工物构制成为技术人工物。否则,A就不能成为一个技术人工物,即便其基本种属已经是技术人工物。
按照以上分析,可以将一种功能由多种结构实现的下行UD现象理解为聚合物A(木棍和铁块)和聚合物B(铁棍和铁块)都能构成X(锤子);可以将一种结构实现多重功能的上行UD现象理解为聚合物A(乙酰水杨酸或阿司匹林)在时间t构制成为X(解热镇痛片),而在时间t*构制成为Z(血液稀释剂)。同时,由于构制理论强调由聚合物A构成的技术人工物X具有专属功能F,这样技术人工物X的功能便只限于专属功能,其他偶然的、可能的功能意义被排除在外,所以一种结构不能实现一切功能的RC现象便得到解释。
如果说贝克将其物质构制理论引入人工物解释,是引入了基本种属和留存条件概念的话,那么霍克斯和梅耶斯则是将扩充的随生理论应用于人工物解释。在当代心智哲学中,金在全(J.Kim)提出了随生理论,力图以心身之间的非还原论关系,讨论查默斯的意识硬问题。在他看来,任何领域或世界W(它由不同的个体构成,x和y等)(如作为有机体世界的人类大脑),均包括基础属性P(物理、化学与生物结构和性质)和随生属性M(心智状态,如意识、目的、意向等),P的同一性决定M的同一性。根据不同随生基础,金在全划分出多重随生性①参见Jaegwon Kim,“Supervenience”,i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edited by S.D.Guttenplan,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Inc.,1994,pp.575—583。:
(1)弱随生性,如果构成W的任何两个个体x和y都是P识别困难的,那么x 和y也是M识别困难的;
(2)局部随生性,只有个别的个体x或y的P决定世界W的M;
(3)全总随生性,如果任何两个世界Wj和Wk都是P识别困难的(一切领域的物理性质超越个体以同样的方式分布),那么Wj和Wk也是M识别困难的(它们的心智状态分布没有差别);
(4)强随生性,如果世界Wj中的个体x与世界Wk中的个体y是P识别困难的(Wj中的x与Wk中的y具有同样的P属性),那么Wj中的x与Wk中的y也是M识别困难的。
以上多重随生的形式逻辑,由于包含了从心智状态到身体结构的多重实现情况,所以能够用来解释UD的下行情况——同一功能由不同结构实现。UD的上行情况似乎可以表述为:如果Wj中的任何两个个体x和y是P识别困难的,那么x和y在WJ和Wk中是M可识别的——不同功能由同一结构实现。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话,Wk中的任何两个个体x和y也应是P识别困难的——Wj和Wk是不同结构的。因此UD的上行情况与强随生性和弱随生性都出现矛盾:x和y不管是属于同一W,还是属于不同W,都是P识别困难的。鉴于这种不能满足上行UD的理论情形,霍克斯和梅耶斯采取了如下三种扩充策略②参见Wybo Houkes & Anthonie Meijers,“The Ontology of Artefacts:the Hard Problem”,pp.118—131。:
(1)将随生基础扩大到人工物设计和使用背景,也即人工物的结构属性S(相当于金在全的基础属性P)在一种背景下具备功能F1(相应于金在全的随生属性M),在另一背景下具有另一功能F2;
(2)考虑技术人工物功能相关内容,随生基础不仅包括人工物的物质基础,还应包括心智属性,如受到意向影响的被刻意设计、生产或使用;
(3)将随生基础扩大到全总随生程度,也即如果两个人工物Wk和Wj的结构属性相同,都是S,且Wj中的随生属性为功能Fl和F2,那么Wk中的随生属性也是功能F1和F2。
在霍克斯和梅耶斯对随生理论的扩充策略中,(1)虽然使扩大了的随生基础与某一功能建立了随生关系,但问题在于,这样会导致对随生关系进行界定时,随生基础属性必须要参照人工物功能。这种情形不符合随生理论强调的基础属性决定随生属性的上行决定关系,且会导致循环论证。(2)把心智属性包含进来,使人工物实际上成为一种意向依赖客体。这样更为麻烦,因为随生理论的本意是为高阶的随生属性突现提供解释,主张高阶随生属性由低阶基础属性决定,但不能还原为低阶基础属性,而扩充后的物质属性与心智属性处于同阶水平。(3)似乎表明人工物世界的随生关系复制及其历史,不过对人工物结构—功能的本体论联系没有太多启发性。与此同时,由于随生理论强调的是从高阶对象到低阶基础之间的单向依赖关系,所以它的单项多重实现并不能满足RC规定的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双向多重实现关系。
与随生理论相比,构制理论较为成功地满足了UD情况,但问题在于这种解释并不充分。例如,锤子既可用来打钉,也可用来作挡门石。但是,锤子并不是被设计成为挡门的东西:一方面,锤子用作挡门石并不意味着木棍和铁块的聚集物可以构制成为挡门石,构制理论由此无法以其专属功能解释这种多重功能实现现象;另一方面,即使木棍和铁块的聚集物,在某种背景和条件下被当作挡门石是合理的,原来的“产品设计” (专属功能)也被“使用计划设计” (偶然功能)替换。对后一方面来说,同样适合阿司匹林的例子。阿司匹林最初的生产是用来解热镇痛,后来便用作血液稀释,阿司匹林的专属功能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功能失范现象。尽管贝克启用附加背景和条件做了补充解释,将这种现象看作人工物功能的复杂性,但仍然缺乏对物质结构知识的深度解释。
与此同时,构制理论虽然解释了一种结构不能实现所有功能的RC现象,但对一种功能不能被任何结构实现的RC现象进行解释却存在问题。它强调人工物功能的必要条件,是与它在空间上一致的专属聚集物。这种聚集物的各种部件包括适合的结构,进而能恰当地构制成为人工物,但这只能解释物质材料“适合于功能F”,且能够获得“恰当组装”,而无法解释这种组装是否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如锤子顶端铁块的重量是否正常地用来打钉等,一种功能被多种结构实现的情况由此也无法获得有效解释。
以上随生理论和构制理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是针对人工物的本体论硬问题假定的清晰的结构—功能关系而出现的。与结构或物性相比,功能由于不仅与其物性相关,而且还与人的意向相关,因此更加具有理论上的解释弹性。在这种意义上,随生理论和构制理论与其说是力图寻求结构与功能之间清晰的逻辑关系,毋宁说是在物性与意向之间寻求对人工物的功能性解释。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与自然物的比较中,将人工物功能作为其外在属性的话,那么一旦如霍克斯和梅耶斯将随生基础扩大到由意向指导的设计、使用背景,以及贝克引入基本种属和留存条件,实际上就将技术人工物看作一种背景实在,使功能位于物性与意向之间,成为人工物的内在特征。这样,技术人工物解释便可以从结构—功能二元论描述转向功能一元论解释(见图1)。

图1 人工物解释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理论转换
将结构—功能二元论转换为功能一元论,使我们可以用与它相关的一切基础、属性和要素进行功能或意义解释。这种转换的理论优势,是不再将功能作为人工物的外在特征,而是在引入设计和使用背景之后,可以把功能看作人工物的内在本质。在设计和使用背景下,物性或结构、意向或目的在价值方面,虽然具有低阶和高阶之分,但在解释学上具有平等地位。在解释技术人工物时不再纠结于本体论硬问题,而是针对功能启用一切解释因素。事实上,荷兰学派最终还是将功能作为物性与意向之间的中介做理论处理。正如莱德(J.de Ridder)指出:
由于人工物的设计、创造和使用,是为了它们能够展示与其功能相关的一种或几种行为,所以需要选择并加以解释的典型行为,应该是与人工物功能相应的行为。①Jeroende Ridder,“Mechanistic Artefact Explanatio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7,No.1,2006,p.81.
对于技术人工物来说,功能具有明显的意向色彩,较之物性或结构更为基础。但是,正如弗兰森(M.Franssen)认为,功能又蕴含着人工物的物性或结构,如石头用来砸碎核桃,这种物性与人的意向没有关联,但核桃夹子的结构设计是用来达到夹碎核桃的功能,即使出现不能夹碎核桃的功能失范,也仍然是核桃夹子。②Maarten Franssen,“Design,Use,and the Physical and Intentional Aspects of Technical Artifacts”,Philosophy and Design,2008,p.23.功能作为人工物的表征属性,兼具物性和意向两个方面。从物性和意向两个方面解释技术人工物功能,可以引入设计和使用背景因素。这样一来,心—身问题包含的把功能还原为结构的还原论问题,便可以被悬置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实现贝克赋予人工物以与自然物相同的本体论地位的构制理论目标,而且也可以消除霍克斯和梅耶斯的随生理论因扩大随生基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三、技术人工物的功能承担理论
一般来说,功能是指这样一种逻辑概念①L.Wright,“Functions”,Philosophical Review,Vol.83,1973,p.161.:X的功能是F,是说(1)X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做到F;(2)F是X存在的后果(或结果)。围绕技术人工物功能解释,目前存在高阶的意向主义(intentionalism)和低阶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两种倾向。按照低阶的自然主义倾向,X具有功能F是说X因其在以往被选择来实现功能F而存在。这显然是一种物性的历史选择理论,如心脏具有血液循环功能,是说以往的心脏被选择用于实现血液循环。这种选择理论同样适用于人工物解释,如钟表、椅子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它们在以往被选择用来实现计时、坐息等。与低阶的自然主义不同,高阶的意向主义仅仅用于人工物解释,强调人工物的专属功能与人的特定意向相关,认为人工物X具有功能F,是说X被制造或生产出来或被置于某种使用情形,是考虑到它能实现功能F。
必须要看到,大量有关功能解释的文献,都会在低阶的自然主义意义上涉及生物有机体功能,但一旦将对生物有机体的功能解释用于人工物功能解释,便都进入到高阶的意向主义。在当代技术哲学中,即使是专注于技术人工物功能解释的荷兰学派,也没有改变这种理论情形。例如,构制理论和随生理论,虽然都从低阶的自然主义出发,但最终都以高阶的意向主义而告终,因为人工物毕竟与自然物不同,正是设计者或制造者的意向使人工物成为人工物。
高阶的意向主义将人工物设计和使用,作为带有高阶认知色彩的范式行为,甚至将人工物看作与语言一样的区分人与动物的品质或特质。这种把某一功能归于某一人工物的概念分析方法,考虑的是人工物设计的原始意向。对于这种高阶的意向主义解释,丹尼特(D.Dennett)提出如下三方面批判:
(1)意向解释的不充分决定性。以意向解释功能,实际上是从某一人工物的正常工作,推断出设计者的原始意向。这是一种“意向误置” (intentional fallacy),因为依靠设计者的原始意向无法解释一个人工物成功的原因,功能解释也并不等同于意向解释。一个核桃夹子,不管其设计者和使用者意欲如何,它都是核桃夹子。丹尼特甚至认为,即使是设计者本人在创造某一人工物时,也不知道其意向是什么,“发明家不过是一个不同的使用者,只是在特定条件和可行性意义上,对其设备的功能和使用享有特权而已”②Daniel Dennett,“The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Texts and Other Artifact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Fall Suplement,1990,p.186.。也就是说,意向并不是功能的可靠指示。
(2)设计者意向无法确保人工物功能不变。任何一个人工物,都不能免于失去其原始意向。老式熨斗会变成书夹,教堂也可以用于非宗教活动。这些都意味着原始意向改变。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能从原始意向推出当前功能,原始意向与现有功能完全没有关系。
(3)功能概念既可以用于人工物,又可以用于生物有机体。人的解释、生物特性、文本和人工物,“都是对不同的客体进行的同类筹划”①Daniel Dennett,“The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Texts and Other Artifact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Fall Suplement,1990,p.177.。但是,生物功能并非按照意向设计,意向在其生物种类的功能描述中并不占据中心地位。
在以上批判基础上,丹尼特提出一种“人工物解释学” (Artifact Hermeneutics),认为这种解释学是这样一种方式:人们寻找人工物发挥作用的最优化方式。这里为了在最优化意义上确定人工物功能,需要忽略人工物物理构制或结构的某些细节(或由此带来的可能混乱)。这样,被解释的人工物便能显示出其设计应该扮演的角色或功能发挥,而不至于导致功能失范。这种人工物解释学近来以不断发展的功能承担理论(affordance theory)表现出来,在低阶的自然主义与高阶的意向主义之间,成为一种在理论上消除物性与意向的相互分离的可选择方向。
英语“affordance”一词,在汉语中有多种翻译,如可操作性暗示、支应、用途预设、示能、易用性等。在生物学意义上,它被当做对象或环境与有机体之间的功能关系,为该有机体提供行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翻译为“功能承担”。就人工物来说,功能承担不是指该人工物的物性,也不是指使其成为人工物的意向,而是能将物性与意向连接起来,成就自然化意向或意向化自然,代表着人工物物性与意向关系的行为或行动。吉布森(J.J.Gibson)较早在其生态心理学观察理论中,以功能承担概念解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承担关系,强调大多数环境对象拥有一种以上用途或效用,人们将对象用于何种行为取决于其心理状态。②参见J.J.Gibson,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9。继吉布森之后,诺曼(D.A.Norman)将功能承担概念应用于设计,认为人工物本身会说明自身的用途或功能。③参见D.A.Norman,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New York:Basic Books,1988。在他看来,人工物能够表现出两种功能承担特征:一是客体实际承担的物理特质;二是使用者察觉到客体的提示性。与吉布森强调功能承担提供行动的可能性不同,诺曼将功能承担看作一种对使用者的感知提示(表1)。不难看到,与吉布森主要探讨人对环境的知觉及由此获得相应信息问题不同,诺曼致力于考察使功能容易获得感知的环境操作或设计,因此认为功能承担依赖于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或文化。

表1 吉布森和诺曼的功能承担理论比较
生态心理学,为人工物简易操作提供了一种简洁描述。例如,对楼梯要依照人的攀爬能力(即人与楼梯之间可测量的关系性质)进行感知,这时人们感知到攀爬楼梯的功能承担。这种功能承担参照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属性,但问题在于感知与主体行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诺曼依照自己的功能承担概念,参照操作的容易程度对门把手进行了解释,指出不同的门把手为不同的行动提示了不同的功能承担,如垂直型的门把手适合于拉门,水平型的粗门把手适合于推门。但是,盖维(W.W.Gaver)指出,诺曼的这种被感知功能承担(perceived affordance),不过是来自实际感知的有用信息,属于显性功能承担,但当“这种显性功能承担超越设计意向,提示其他不同行动时,就会产生常识性错误,这时信息预示便成为必要”①W.W.Gaver,Technology Affordances,CHI’91 Conference Proceedings,1991,p.80.。他为此将功能承担与其有用信息分离,按照是否具有功能承担和感知信息,区分出四种功能承担类型(表2)。

表2 盖维的四种功能承担类型
在上述分类中,可感知功能承担有些类似于诺曼的被感知功能承当,也称为显性功能承担,它包含有用的感知信息。但是,如果缺乏应有的感知信息,它就变为隐性功能承担,必须要从其他证据获得推断。如果感知信息提示某一不存在的功能承担,就会形成导致行动失败的错误功能承担。例如,可旋转门把手似乎仅仅适合于拉门操作,但一旦抓住把手柄,只要随意下压就立刻会传递一种旋转把手的触觉信息,当旋转完毕时,便又会产生新的功能承担构型——拉门和开门。在这种意义上,盖维参照可感知功能承担行动所处的能预示新的感知信息的特定情境,引入“序列功能承担” (sequential affordance)概念,解释功能承担随时间而获得连续显示的情形,从而赋予可感知功能承担以“参照间性” (inter-referentiality):
使功能承担可以感知得到,是一种简易操作系统设计方法。这种可感知功能承担具有参照间性:与行动相应的客体属性有利于感知,被感知者用于行动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被感知属性必须以表征为媒介,与相应的客体属性相关联。你对门把手适合于拉门的感知而不要求诉诸媒介,是因为与拉门相关的客体属性有利于感知。你知道一把钥匙可以在一把锁内转动而要求诉诸媒介,那是因为相关属性不利于感知。①W.W.Gaver,Technology Affordances,p.81.
盖维认为功能承担独立于感知,无论感知者是否意识到,功能承担仍然会独立存在。但是,这恰恰表明参照间性的必要性,因为只有依赖参照间性才能将功能承担与感知关联起来。按照参照间性的观点,实际上在人工物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一个“界面” (interface)。这个界面提供了用于行动的人工物信息,也提供了人工物的功能承担。如果按照不同媒介为不同行动提供的可用感知信息来理解功能承担,如计算机屏幕深色按钮适合于按压,那么这会传递文字输入、打印、格式化、通话等信息,因此其标记与参照对象相关联,对感知者具有指导性。
一般来说,当人工物所传递信息与行动相关的系统属性一致时,这种信息就是功能承担。沿着盖维用于人工物使用的功能承担解释线索,麦克格雷奈勒(J.McGrenere)等人将功能承担理论运用于技术人工物设计解释。②参见Joanna McGrenere,and Wayne Ho,Affordances:Clarifying and Evolving a Concept,The Proceedings of Graphics Interface 2000,Montreal,May 2000。按照他们的观点,技术人工物设计的目标,首先是确定必要的功能承担,然后尽可能促进功能承担简易程度和可感知信息最大化。必要的功能承担的确定与人工物的有用性(usefullness)相关,而功能承担和可感知信息改进又与合用性(usability)相关。也就是说,技术人工物设计,不仅要关注其使用者感知的可能行动,而且也要关心功能承担是否与使用者目标一致。无论如何,技术人工物功能承担是一个复杂的行动系统。正如盖维指出:
功能承担概念,指向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性质构型。这意味着,物之被用于行动的物理属性与行动者的要求相匹配;也意味着,能够以与感知系统相匹配的形式获得有关这些属性的信息;还(含蓄地)意味着,这些属性及其产生的可能行动与文化和感知者相关。因此,分析人工物,就是要弄明白人工物与这种性质构型是一种怎样的紧密关系,进而弄明白人工物究竟传递了什么样的功能承担。①W.W.Gaver,Technology Affordances,p.81.
上述引证表明,技术人工物的合用性,因解释特定功能承担的可感知信息设计而增强,而这种可感知信息设计必然包含设计者和使用者的不同归属,如专业水平和文化习惯等。因此,对人工物功能承担的实际感知程度,必然取决于人的文化习惯、社会环境、经验和意向。因此,如果说吉布森在其生态心理学中并未考虑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当将功能承担理论用于技术人工物解释时,就要把人工物看作一种价值关联物,把人工物功能承担看作一种复杂的文化性质构型。
四、技术人工物的规范解释指向
技术人工物解释的规范性,源于它的功能承担的价值指示:可感知的功能承担,告诉我们人工物“应该做什么”。人工物功能解释涉及的是设计和使用的范式行为,属于物性与意向之间的间性解释。如果在最优化意义上不能做到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功能承担就是错误的或被正确地拒绝的,也就是功能失范,或通俗地讲是糟糕的人工物样品。例如,“这是优质的钻孔机”,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判断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规范事实:该钻孔机能发挥正常功能,不仅能达到物性与功能承担的一致,而且也符合人使用钻孔机的钻孔意向,从而给予我们使用钻孔机的规范性理由。
之所以说钻孔机的优质性具有规范性意图,是因为它引导人们对某一行动持赞成态度。弗兰森为此把钻孔机的规范性事实上升为一般见解,认为“不仅是一个人工物执行其功能好坏这类陈述,而且对一种功能归于一个人工物的所有陈述,都能被看作是对规范事实的表达”②Maarten Franssen,“The Normativity of Artefac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7,No.1,2006,p.42.。这种对规范事实表达的扩大,既涉及人工物的物性条件,也涉及人工物的设计历史、可感知的功能承担,甚至人的伦理态度。正因为如此,人们充分相信,无需语言表征而运用功能概念,可以对技术人工物作出广泛的理解或解释,以至于形成了将技术人工物的一切属性均还原为功能向度的功能主义。这种功能主义,将技术人工物表现出来的一切属性,如物性、目的、效应、计划和任务等均归于功能范畴,几乎涵盖从感知、等级和认知功能到动物的人工利用及其对人类的作用的一切领域。克莱莉(N.Crilly)超越技术人工物的物理功能,将其一切非物理目标划入功能范畴①Nathan Crilly,“The Roles that Artefacts Play:Technical,Social and Aesthetic Functions”,Design Studies,Vol.31,No.4,2010,pp.311—344.:一是按其目的、效应或手段,分为物理功能和身份功能、技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以及美学功能和非美学功能;二是按其选择、意向和识别,分为专属功能和系统功能、设计功能、使用功能和服务功能以及显示(显性)功能和潜在(隐性)功能。
功能主义的人工物规范事实表达扩大,尽管有其合理性,但它除了功能绩效考量外,并不能为对其物性的其他规范判断留下多少余地。例如,对于制造商来说,“这是优质的螺丝钉”。这一陈述表达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该螺丝钉符合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这种规范性并不必然来自用户对其使用的赞成态度,它的赞成态度尊重的是生产标准:在给定ISO螺丝钉更容易生产出来这个事实的条件下,制造商便有自身的规范理由生产ISO螺丝钉,而不是生产其他螺丝钉。类似地,“这是优质的软件包”表达的事实是它的数据源具有开放性;“这是优质的引擎”表达的事实是它使用的是清洁能源;“这是优质的产品”表达的事实是它具有良好的市场销路;“这是优质的插头”表达的事实是它堪比常用插头;“这是优质的T恤”表达的事实是它是在可接受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等等。所有这些陈述引出的赞成态度,也许来自技术人工物的使用情况,也许来自它的生产、购入或出售、维修、复制、标准设定、环境影响等,但都具有规范性力量。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意向的范畴较之功能更为广泛,那么人工物的规范性便也更为广泛”②Krist Vaesen,“The Functional Bias of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efacts Progra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2,No.1,2011,p.196.。
为了避免功能主义的功能解释偏见,技术人工物规范解释指向,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技术人工物置于人与世界之间,诉诸直觉方式对其非功能属性或意义做更广泛解释。因为正是技术人工物的媒介作用,改变着人的直觉方式,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信息、知识和价值。技术人工物显现出了人的直觉无法以非间性方式加以把握的世界存在方式,如利用红外线成像技术和其他手段进行诊疗、军事观察和海洋探索等,由此获得的“实在”是一种不同的可解释的“实在” (图2)。与非间性直觉相比,人通过技术人工物获得的对世界的间性经验,应该包括人与技术人工物关系和技术人工物与世界关系两个方面。技术人工物与世界关系,依靠功能承担理论强调的人与技术人工物关系而得到确立。就人与技术人工物关系来说,人的技术人工物间性经验至少包含如下六种含义:

图2 技术人工物的直觉经验比较
(1)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是以对人工物的特殊规定来指示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操作实践。正如功能承担理论表明的,人有目的地操作机器或设备的先决条件,是要获得最优地使用该机器的技巧或习惯,而这种技巧或习惯获得源于不断的操作实践。人越是熟练地使用或应用技术人工物,技术人工物对人越是变得透明,也越能改变或变成人的身体程式。
(2)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有助于我们推动“技术目的”的实现,但其最终结果往往会超越这种目的,发生较之单纯的直觉更为激烈或严重的变化。美国航天飞船“挑战者号”失事爆炸事故,印度博帕尔市化工毒气泄漏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泄漏和爆炸事故,这些都是人工物大规模失灵导致的严重灾难,它们对人类形成的威胁会影响到这类技术人工物的进一步发展。
(3)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往往会引起人的直觉的根本改变,产生新的世界经验结构。上面提到的人工世界巨大灾难,使人类由以往的“自然恐惧症”转向了普遍的“技术恐惧症”。
(4)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在许多情况下是对物的经验或人与世界之间的情景嵌入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绝不会是只有一种技术人工物,可能是多个技术人工物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即使是一个技术人工物,也不是孤立发挥作用,而是处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形中发生作用。
(5)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是单向度或多向度的间性参照经验。人通过技术人工物理解和控制世界,不是仅仅限于视角,而且会从多个层面对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获得自身的不同世界经验,因此往往会进入某种争执之中。
(6)人的技术人工物经验,在意向性行动或实践上是与伦理相关的。人作为机器或设备的设计者、操作者或使用者,也许不会意识到其行动的意义或结果,但人通过机器或设备获得世界经验,最终要以伦理实践为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技术人工物代表着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改变着人的世界经验,也改变着世界或以改造的方式展示世界。这些改变发生在人与非人之间的各种价值关联中,而这些关联的相对性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或透明的。这种相对性表明,无论其行动者或能动者在价值关联中是占据支配地位还是处于被支配地位,技术人工物及其与人的关系都要在世界视域中展开。这种视域就是在其对人的人工物经验的解释图式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生活世界,因为它“不是将技术人工物还原为使人工物成为可能的世界展示的技术形式,而是探求究竟什么样的世界展示形式因技术人工物而成为可能”①P.Verbeek,“Don Ihde:Technologicallifeworld”, in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edited by H.Achterhuys,translated by Robert N.Crease,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122.。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技术人工物可以传达完全不同的直觉或意义。例如,在西方航海中,指南针使用包含了对海洋方向、经度和维度等一系列因素的数学表达系统,但在南太平洋航海中,航海者在缺乏指南针情况下一直是根据波浪的形状进行掌舵,一旦拥有了指南针,便只是用来引导直线航程,而完全忘记了对波浪的直觉。②参见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与此相似,虚拟实在兴起后,几乎一切空间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图像技术应用和计算机软件研发都与原来不同了,目前如地理信息统计、神经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城市地理、航空控制系统、生态系统等空间构图技术研究,都采用了使原有空间直觉近乎消除的“无标度”方法。在这里的时间和距离似乎被抹去了,以至于经验只是一扫而过。无论如何,技术人工物并不是什么中性实体,它在生活世界视域中总是与人存在着价值关联。
(责任编辑:肖志珂)
B15
A
2095-0047(2016)04-0089-17
李三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教授,校刊编辑部主任,《探求》杂志主编。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间性理论”( 项目编号:13BZX02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