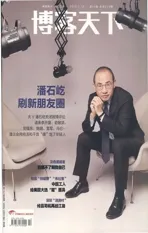中国工人给美国大选“戴”面具
2016-09-15施展萍编辑王波
文 施展萍 编辑 王波
中国工人给美国大选“戴”面具
文 施展萍 编辑 王波
希拉里和特朗普应该不会想到,他们的竞选竟能给中国的面具工厂带来商机。

“金华派对乳胶工艺品有限公司”样品室里的总统面具
在记者蜂拥而至后,21岁的彩绘工人侯忠丽和大部分工友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的那个“女人”叫希拉里。她黄头发、高鼻梁、牙齿白得发亮,眼角与额头有轻微细纹。这些细节都需要在面具里体现出来。
侯忠丽就职的“金华派对乳胶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的工厂里。她已经记不清,从2016年3月开始,究竟有多少张希拉里的面具从手中经过。有时,她会为面具画上银色耳环,有时是将一排排肉色的牙齿涂成白色,还有时,她为这位叱咤风云的女政客抹上标志性的大红唇。
过去一个多月里,共有50万个希拉里或特朗普的面具从侯忠丽所在的工厂被装箱运走,当中夹杂着少量桑德斯和克鲁兹的面具。
从工厂出发,满载面具的大货车会经由郑家坞进入诸暨,途经兰亭上邵诸高速,后转入G92高速。顺利的话,5小时后,车子将停靠在宁波北仑港区,面具在这里装载上船,经1个月海运,到达美国。
“奥巴马”带来的商机
在那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正在进行。尽管特朗普刚刚成为共和党在俄勒冈州的胜利者,如果他知道,不久前,此地一位反对者将他的乳胶面具架在象征生殖器的物体上,恐怕不会太高兴;另一位叫Haleigh的美国女孩在数年前买过一张希拉里面具,并戴着它度过了当年的万圣节。“伪装成希拉里参加聚会,只是为了好玩。”她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并不是用面具表达政治立场。
为了生产这些面具,侯忠丽的生活中大多时候充斥的是车间里机器运转的声音、风扇的呼呼声、工人推动框子与地面摩擦时发出的刺耳的吱吱声,以及乳胶和颜料混合的气味。他们必须靠得足够近,才能听见对方说话。
走出车间,侯忠丽最近发现生活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先是在车间楼下的粉色宣传栏里看见有关工厂的报道版面,很快,她的QQ空间被一篇《美国大选中国商人嗅到商机,竞选人面具走俏》的文章刷屏。她马上带着些自豪转发,甚至会和工友一起在本地的新闻网站上与网友发生争论。
“这些面具哪里可以买到?”有人问。
“这些东西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多的是。”有网友这样回答。
侯忠丽看到了,感到懊恼,想要解释,工厂里的东西都卖到外国去了,怎么可能出现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但她又不太确定:“我没去过小商品市场,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她的上司、公司总经理陈隆头痛的则是记者不断地被“希拉里”和“特朗普”吸引过来。接连接受了十多家媒体的采访后,他开始拒绝,“最近有点烦”。
6月21日,陈隆拒绝了国外一家著名新闻社的约访,他告诉对方,自己最近不在金华。但这并不是事实。当天夜里,在办公室的梨花木茶桌前,他熟练地泡起大红袍—产自福建武夷山的茶叶。
“不过是利用我们来宣传美国大选罢了。”这个福建人一边往茶壶里倒水一边说。他身高184cm,皮肤略黑,身材魁梧。他认为记者无非是冲着希拉里和特朗普来的,作为商人,应付记者的提问实在有点浪费时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我的时间应该花在工作上。”
业务员杨帆第一次看见有人佩戴自家工厂生产的面具是在4年前。电视画面里,奥巴马要发表演讲了,现场看客渐渐多起来,3名身穿休闲装的人戴着“奥巴马”面具、举着牌子,从镜头前走过。
杨帆在电视里见到的“奥巴马”,正是他们工厂生产出的第一种总统面具。4年前,在一位中间商的建议下,他们做了些小规模尝试,但很快收到大洋彼岸传来的好消息:总统面具在美国卖疯了。敏感的商人从中嗅到了商机,2016年伊始,陈隆就迫不及待地向美国朋友打听大选候选人的情况,得知特朗普与希拉里在竞选中表现突出,尤其是特朗普,相对幽默,又有钱,被很多人喜欢。陈隆马上要求工程部设计出10款不同材质及表情的特朗普、希拉里面具,并在上半年收到超50万张面具的订单。
起初,有一批货是以3:2:1的比例装箱的。3是“特朗普”,2是“希拉里”,1是“桑德斯”或“克鲁兹”。但很快,“桑德斯”和“克鲁兹”就从生产线上消失,成为摆放在样品室中的陈列品。“桑德斯已经被干掉了。”杨帆说。就像他几年前看到的那款“奥巴马”,已经停产很久了。
从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命运中,陈隆找到了自己的商业逻辑:必须不惜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以防止被市场淘汰掉。“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必须退出这个行业。”他说。
这种危机感有一部分源于整个制造业。2008年初到义乌时,从每家每户赶工的盛况中,陈隆觉得自己见证了中国制造业最辉煌的时刻。那时,他甚至坚定地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
他眼里衰败的迹象从两年前开始。先是周边的工厂接二连三地倒闭,很快,那些过去出手阔绰的义乌朋友,“连饭都吃不起了”。过去,一到春节,镇上满街都是外地口音,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足足有14万,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2万,夜幕降临,镇上立刻黑压压一片。
陈隆感到,黑暗中有一只老虎在追着自己跑,虎口大开,等着一口吞掉他。他不甘心像周围那些落败的工厂一样,依靠价格战消耗掉自己。他意识到,必须抛掉中间商,直接对接终端,根据终端的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
如今,有1万多款不同造型的面具被摆放在300多平方米的样品室里。陈隆常常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发现与自家产品相似的商品,但他没有侯忠丽那样不确定,他看上去野心勃勃:“没关系,你永远都是跟着我的步伐在走。”带着点儿胜利者的姿态,陈隆挺直腰板,伸出一只手指,指了指空气,又指了指自己,重复道:“不是我跟着你的步伐,是你跟着我的步伐在走。”

“希拉里”的口红
从亚马逊上的买家留言看,总统面具多被用在万圣节或日常派对上。
Haleigh证实了这点。如果有人戴着政治人物的面具来表达立场,她会认为对方在恶搞。事实上,那张希拉里面具她只使用了一次—在万圣节夜晚,戴着这张面具与朋友一同敲响邻居家的门,说“不给糖就捣蛋”。她已经很久没碰过这张面具了,也想不出可以再次使用它的场合。
而为了确保Haleigh等美国顾客能尽早戴上这些面具,侯忠丽和工友们加班的日子已经持续数月了。对一家工厂而言,按时交货永远被排在第一位。
最近有段时间,从早上7点半开始,工人每天在岗位上劳作13小时。夏日的车间燥热难耐,睡意通常会在下午3点时达到高峰,为了抵抗疲惫,他们有时会站起来干活,或者在车间里走走。
在这里,“特朗普”与“希拉里”是一张张软趴趴的乳胶皮。从模具中取出后,它们被整齐地倒挂在一排排弯钩上等待风干,差不多像东南沿海家家户户晒咸鱼那种场面。进入喷绘车间后,数不清的“特朗普”与“希拉里”被随意堆放在蓝色框子里,只在刚刚喷完漆或上完色时,才有被整齐排列等待晾干的“特权”。多数时候,两位政客看上去并不风光,他们的眼珠与鼻孔被挖掉,与魔兽里的古尔丹、美国队长的盾牌和造型恐怖的娃娃为邻。
700多位工人就淹没在这些码得高高的蓝色框子及一个个比他们脑袋还大的面具中,淹没在乳胶、颜料与汗水混合产生的气味里,神情有些木讷。见到陌生人,他们并没停下手上的活,但目光会一直跟着,面对陌生人的微笑,他们脸上会浮过一丝不知所措,然后继续盯着,穿过柱子,穿透距离,好奇又防备地盯着。
这里的每件产品都有编号。编号是一串难记的数字,为了方便记忆,工人们会自发给产品取代号。
希拉里在车间的代号是“美女”。侯忠丽想不明白,这个“老太婆”年纪这么大了,为何还要在唇上涂这种颜色艳丽的口红。在侯忠丽21年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支口红是2015年结婚前自己买的。丈夫比她大几岁,相识一个多月后,在侯家的菜地里,捧着一把当晚就下锅的菜,跪下来求了婚。
婚前,侯忠丽拿着丈夫给的钱郑重其事地到城里买了一支玫红色口红,六十多块钱。那支口红被她放在抽屉中,没有多少使用过的痕迹,偶尔心血来潮,她会在宿舍对着镜子抹两下,出门前,又匆匆擦掉。

2016年上半年,这家工厂共产出50万只特朗普或希拉里面具
现在,每为“希拉里”涂一次口红,她就可以有1毛3的收入。
发生在这位“老太婆”身上的事,侯忠丽并不关心。她浏览最多的新闻都是从QQ弹窗里主动跳出来的。那些发生在浙江当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是工友间的谈资。几天前,她看到一则新闻:浙江某地的一位母亲贪玩,将孩子关在家里,孩子从窗户上掉下来,摔死了,父亲拎着摔死的孩子殴打老婆。
这让她想起在云南文山老家的5个月大的女儿。女儿生下来时,侯忠丽只带了她10多天就生病住院,病还没好,就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以至于很多时候她并没有已为人母的切身感受。但有些片刻,她会突然觉得胸前空落落,特别想抱一抱那个小人儿。担心孩子长大后责怪妈妈没有陪在身边,侯忠丽打算在工厂做完这一年就不做了,回家带孩子。
一整天辛苦劳作后,侯忠丽和工友们一样,回到住处,洗个澡,躺在床上能立刻睡着。偶尔,她也会想想这些面具究竟去了哪里,“他们拿去拍电视剧吗?可是中国也拍呀,为什么都是外贸呢?”思路往往到这里就断了,这些事情对她来说还是太遥远了。
对喷漆工人唐燕而言,情况也类似。面前的机器正发出沉闷的轰鸣,不断用流水吸走喷漆时产生的灰尘,她站在机器前,缩着双肩,戴着口罩,显得很娇小,被一筐筐等待喷漆的丧尸面具团团围住,她身后圆柱状的铁架上,倒挂着12个面目狰狞的丧尸头。由于长时间举着喷枪,唐燕的右手指节分明而弯曲,左手袖套永远分成两截,下半截干净,看得出那是一只白底红樱桃图案的袖套,但上半截每天都会被不同的颜色厚厚地覆盖住。
她有足足半年没有见过孩子了。上次离家时,女儿躲在被窝里哭,儿子好像突然懂事了,假装镇定地对她挥手告别。但长时间不见面,疏离感不由分说地横亘在母子间。3个月后,女儿不怎么接妈妈电话了。一天夜里,这位年轻的妈妈躲在车间的墙角边,一个人哭了很久,“我想到,没劲啊,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你们俩,还不接我电话,没劲呀。”
尽管唐燕曾无数次为手中的女士喷上一头黄色头发,并因其发型特殊为喷漆带来的困难而苦恼,但直到现在,她都不能完整叫出“希拉里”的名字,通常的说法是“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对比的那个”。
唐燕和侯忠丽一样,都希望自己勤快点,多赚点钱,减少孩子们的负担。对于美国,她们唯一的概念是,那似乎是个很多有钱人想去的地方。
被问到是否知道面具的产地时,美国女孩Haleigh不太确定,但猜想它或许是“中国制造”,然后她用中文打出了这四个字。
华为路2号
工程部主管罗永斌的电脑上,至今仍贴着一张写着“路透社采访”的黄色便签,用来提醒自己。事实上,那场采访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结束了。而后的一个月里,他陆续见到不同国家的记者。
或许是被反复问过“支持希拉里或特朗普”,罗永斌看上去有备而来,一上来就主动表明了态度:“我支持希拉里,因为希拉里沉稳,觉得她竞选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特朗普有点狂,他从商出身,骨子里还是个商人,很多东西和利益挂钩。”
本文所探讨的数字货币不同于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加密货币,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催生的产物,它和电子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以下几点:
人工雕刻一张希拉里或特朗普的面部模具,前后大约需要10天。10天下来,罗永斌自认已摸透这两个人的特征:特朗普是“由”字脸,发型不多见,像香港早期流行的那种,一小绺刘海往前走,眼神严谨,眉头紧锁;希拉里的眼中则有一种人到中年的慈祥。
罗永斌到义乌3年了,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和他一样对工作满意的还有43岁的四川男人唐开才。这个语速缓慢的圆脸男人在2009年工厂筹建阶段就已到来,见证着厂房由一栋变成两栋,再变三栋,又扩建了占地40亩的新厂,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
每次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工厂出产的人物造型出现在大银幕上时,他总是忍不住在黑暗中和身边的工友一同尖叫:“这是我们工厂生产的!”周围的人不知道他们在乐什么,皱着眉头给他们脸色看,他们就闭紧嘴巴,但心里还是激动。
唐开才似乎弄混了一个概念。是先有了蝙蝠侠、美国队长和古尔丹等银幕形象,才有了工厂里的这些产品,而不是先有了工厂出产的产品,然后它们出现在了电影银幕上。
唐开才喜欢看国际新闻、热爱分析时局,但目前最关心的是厂里的效益。在工厂筹备阶段,他和陈隆在一个车间同吃同住,他叫陈隆“老大”,陈隆喊他“阿才”。他觉得老大待自己不薄。现在,唐开才依然待在工厂起家时的那间车间,不同的是,这里多了很多工人及嗡嗡作响的机器,他也成为主管。
他记不得有多久没叫过陈隆“老大”了,公司越来越规范,主管就是主管,经理就是经理,层级分明,这个憨厚的四川男人觉得自己马虎不得。工厂越来越大,也意味着老板越赚越多,这样他也能够赚得更多些。
作为老板,陈隆坦承对员工非常严厉。他最欣赏的企业家是任正非。来义乌前,陈隆在深圳创业,听过不少任正非与华为的故事。几位曾在华为工作过的朋友被炒鱿鱼,“他们自己也困惑,我是很有才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华为做不下去呢?为什么无数个夜晚加班通宵,就是做不出来?”他总结,“还是能力问题。华为的淘汰率非常高,他(任正非)要的就是业绩,没有业绩,就把你整个部门都淘汰掉。”
“这样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
“不。企业就是要追求利益。我从未听说过世上有哪个企业家被形容为仁慈。”陈隆说。他笃信一切企业管理都应该向军队管理靠齐。任正非刚出书,他就购入。
巧合的是,他的工厂所在的路叫“华为路”。工人们的说法是,当地政府原想邀请华为入驻该工业区,但华为拒绝了。
员工们的梦想
在做外贸生意的工厂里,每个负责商业扩展的业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几位“外国朋友”。
他们在展会上结识这些外国朋友,并进行生意上的往来。业务经理唐颖发现,她的“欧洲朋友”多数很感性,个人喜好以及与业务员的关系亲疏会决定他们是否下订单;但“美国朋友”不是,美国朋友要最好的价格和服务,要足够详尽的数据,拒绝听到“做不了”这3个字,要的是“做不了”之后的至少3个后续方案。
工作之外,他们也会有一些其他交流。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唐颖的美国朋友多数支持奥巴马。她特地翻出奥巴马的视频看,觉得眼前这个黑皮肤、小卷发的男人很有激情,能在美国经济最低迷时给人信心。因此,到了这次总统大选,唐颖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美国朋友会更喜欢特朗普,因为他张扬且自信,“张扬体现在美国人的优越感里”,这种“优越感”也有她不能理解的部分,“美国人欺负人家、发动战争,他们都觉得这是对的。”
杨帆有一位在美国的中国朋友。那是他在老家的邻居,目前在硅谷开发软件。两人偶尔交流,对话多止于互问近况。杨帆觉得自己和他不太一样,“他可能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我就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
但他们留着相似的发型:都将两侧的头发剃光,留下中间的三分之一,长长了,就在脑后绑成一道细细的马尾。发型是杨帆从一些欧美视频当中学来的,他觉得这样能让自己在众多业务员中显得与众不同,被那些分不清中国脸的老外记住。对于发型带来的实际效果,杨帆非常满意,客户见一次就记住了,当他缺席一些展会时,客户会向同事问起“那个头发很长的小男孩”。
最近,杨帆打算学学特朗普。他觉得特朗普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魔性,极具煽动力的表达方式似乎可以用于与客户沟通上。每周,他都会上网观看特朗普的演讲视频。但目前,除了特朗普坚定的眼神外,他暂时还没有总结出其他可供实际操作的点。
“魔性”的特朗普在杨帆心中象征着美国感性的一面,希拉里则是理性,感性与理性正在拉扯。他觉得这种较量的背后是一种弥漫全球的迷茫,不太确定最终哪一方会旗开得胜,带领世界继续向前。对此,他有些困惑,但作为一心想帮助公司壮大的业务员,他更希望可以同时满足感性与理性双方的消费需求,将他们的钞票统统收入囊中。
罗永斌的想法则要简单得多,他最喜欢的美国人是库里,最大的心愿是去美国看一场NBA,但又觉得梦想似乎遥不可及—“我们要加班,要想方案,搞开发,没有时间。”
侯忠丽的想法更简单。她并不想去美国,只想到海边走走,像她在QQ空间里看到的那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海南三亚是最好的选择,实在不行,距离金华最近的宁波舟山的海也可以。她听朋友说,那里的海根本不算海,但她还是想去。她从没有见过大海,在她的想象中,大海是蓝色的,是看不到边的,是咸的。她想在海边拍张自拍,这张照片里一定要有礁石,背后全是海,海面有波浪起伏。然后把鞋子一脱,安稳地踩在沙滩上。
说这话时,她正在嘈杂的车间中,一脸憧憬的她不得不提高音量。

上图:喷漆工人正为特朗普面具上色 下图:总经理陈隆戴上特朗普面具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