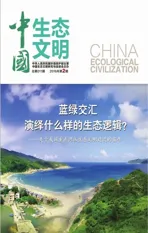环境史观,要极端还是理性?
2016-09-14王利华
□ 王利华
环境史观,要极端还是理性?
□ 王利华

环境史研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历史,既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环境史在最近40余年迅速兴起,正是由于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
环境史关注以往史家不甚重视的气候、土壤、水体、物种、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其忧患的是气候变暖、物种减少、水土流失和水体、土壤、空气污染等。
从学术史上看,历史观的更新和变革常常发轫于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判是新史学常具的特质,在环境史领域更有突出表现。但在当下,我们尤其应强调进行反思和批判时需要理性精神。
在西方,与此前普遍讴歌和高度赞美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成就明显不同,过去几十年环境史学者对工业社会过度张扬工具理性、奉行利润至上的经济逻辑进行了尖锐批评,对资本主义制度无限放纵物质欲望、严重摧残地球环境进行了深刻揭露。这种反思和批判明显受到环境保护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环境保护主义者痛陈“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病,强烈主张奉行“生态中心主义”,言辞激奋,振聋发聩。
我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反思和批判不像西方那样直接尖锐,但所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仍值得注意:一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对农业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的眷恋与怀想,尽管那种“和谐”许多时候只是历史的幻象;二是过度溢美古代生态智慧和环保制度,回避历史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三是“经济开发等于环境破坏”的简单论说相当多见,否定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从这些思想倾向很容易推导出“一部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环境破坏史”的极端结论。当然,迄今为止“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尚未决出高下,我国环境史理论方法远未成熟,环境史观还处在相当“混沌”的状态,环境史研究群体患上不同程度的“思想幼稚病”也难以避免。
应该认识到,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弊病,并非要走向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回归“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态;批判历史上错误的环境行为,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匡正工业文明的严重失误,但决不可能脱离工业时代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学术史上的经验表明,情绪激昂的反思和批判有助于突破桎梏、激发思想和警醒世人,但历史价值判断终究需要回归理性。
树立理性、成熟的环境史观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一个艰苦曲折的思想求索过程。我们应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意气之争,抓住环境问题的历史本质,把“以人为本”的生命关怀、“与万物相亲”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相关事物和现象放回“历史现场”予以“同情之理解”,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情境抽象地褒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认清当今环境危机的积聚过程和历史本质,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