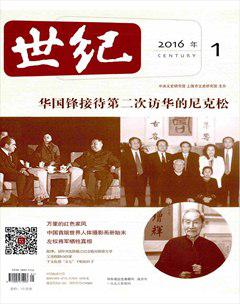冒险刊发陈敏之纪念胞兄顾准文章
2016-09-12口述郭志坤撰稿
陈 绛/口述 郭志坤/撰稿
口述历史
冒险刊发陈敏之纪念胞兄顾准文章
陈 绛/口述 郭志坤/撰稿
《近代中国》是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学术辑刊,一年一辑。《近代中国》第一辑由丁日初任主编,我和沈祖炜任副主编。第二辑起副主编增加徐元基。从第六辑起不设副主编,增加沈渭滨、杨国强、顾卫民为编辑部成员,但看稿、看清样,仍主要由丁、徐、沈和我四人承担。2002年丁日初去世,中山学社决定由我从第十三辑(2003年)起继任主编。我请了复旦历史系同事沈渭滨教授和我同在上海图书馆盛档组工作的丁凤麟(《解放日报》退休高级记者)担任副主编,便于就近商量;还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易惠莉也担任副主编。几年来我们几位合作很愉快。
在《近代中国》刊发的文章,我记忆中比较突出的有好几篇有分量的文章,其中第五辑刊发的陈敏之关于顾准的文章我印象尤为深刻。
出版胞兄遗著一波三折的陈敏之向《近代中国》投稿

1995年我们收到顾准弟弟陈敏之给《近代中国》投稿,题为《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这是作者陈敏之当面交给丁日初的。陈敏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 1936年9月在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由顾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陈敏之一直在编辑他的胞兄顾准的遗作、撰写了与顾准相关的著作。陈敏之在向丁日初递交文章时说了一席伤感的话,丁日初将这番话转告我,顾准的著述上海不敢接纳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在上海投了3个出版社,他们认为“吃不准”,要向上级有关部门送审,陈敏之不想为难上海的出版社,于是投香港三联书店,在1992年6月出版。陈敏之后来编的《顾准文集》,也是问了上海几家出版社,他们认为,顾准是敏感人物,吃不准,都婉言拒绝出版,陈敏之通过朋友关系投贵州人民出版社,才得于1994年出版。
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几经周转才在香港三联书店获得出版时,陈敏之感慨万千,曾经多次对丁日初等人说:“现在,历经艰辛,这本书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帧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胞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丁日初明白这番诉说所表达的是陈敏之的伤感,更是他的兴奋喜悦之情,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的期望和信任。丁日初接到陈敏之这篇题为《顾准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当天就找我(当时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商量,对我说,文章题目后面四个字是学术问题,而前面四个字却是涉及政治。我们的刊物能够刊发吗?我拿稿子回去细读后表示同意刊发,因为我过去对顾准有了解。

我了解的顾准其人其事
我最初听到顾准的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反” 运动初期在华东局统战部时,上海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刊载中共上海市委重要干部黎玉(市委秘书长)、曹漫之(市民政局局长)和顾准(市税务局局长)等领导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在统战部一次小型会议上,许涤新说,顾准一向是“福将”,这次也“翻船”了,言下有些惋惜之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报刊上陆续读到一些有关顾准的文章,才开始对顾准其人有些认识。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于20世纪80年代逝世前郑重指出,他自己于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就是受到顾准的影响。1975年孙冶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他每天清晨都要去三里河边散步,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已故)非常自信地说:“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们两人情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见一面。这是一桩令人痛心的遗憾。
当丁日初同我商量时,我表示:“要刊发就早些刊发,别处不发表,就在《近代中国》发表。”于是丁日初将陈敏之文章以及其他稿件交我处理。
晚上回到家,我重新又把这篇文章阅读一遍,进一步了解顾准的生平和业绩,从陈敏之文章中我深感顾准是位具有相当理论水准的老革命。他于1930年(十五岁)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这时还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曾任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和文委副书记。1949年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1956年顾准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
“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顾准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对于顾准一生悲剧,我深表同情,认为应该把他的生平公之于世,教育后人。尽管遭受种种迫害,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可是,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1980年2月,顾准终于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
陈敏之的文章写道:多数读者只知道顾准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因为在他连基本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读书、思考、写作。现在保存下来并得以公开问世的遗作,是在一种十分奇特的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1972年冬陈敏之在北京寻找他和同他的晤见,没有1973至1974年这两年间顾准、陈敏之兄弟之间频繁的通信以及在通信中进行的学术讨论,就没有这些文稿面世。陈敏之这样说:“有趣的是1973 至1974 这两年,他在生活上的处境相对平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隙,那么,他的这些学术思想大概也无法逃脱伴随他的躯壳一起离开这个尘世的命运。”
关于学术问题。我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它几经周折才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王元化是最早读到此书的一位。他说:“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他欣然命笔为本书作序,序言这样写道:“(此书)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他对于从 1917年到 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此前,我还读了陈修良的文章,题目为《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见《上海滩》 1994年第 6 期),文章说:“上海,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先驱。但是,集革命家和思想先驱于一身的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勇士。我想,我们的老战友顾准应该是跻身这一行列而无愧的。”这是对顾准其人其事公正的客观的评价。
的确如此。说顾准“一生坎坷”,并非过分。在他身上,绝对找不到一分奴气或媚骨。“少年得志” ,也许过于顺利而增强了他的自信;而自信常常表现为傲气。这种傲视一切的气概,在倡导每个人成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的社会里岂能容得;而他又是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心口如一、说话毫无遮拦的直白人;这是他的优点更是他致命的弱点。
如今陈敏之在顾准逝世20周年之际撰文纪念,很有必要。
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顾准著述的出版刊发,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确实刮起了“顾准旋风”。
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李慎之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中引用泰戈尔的诗句来形容顾准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许多学者读了陈敏之文章都赞叹,顾准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照亮黑暗的革命家和思想者。
(口述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已退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