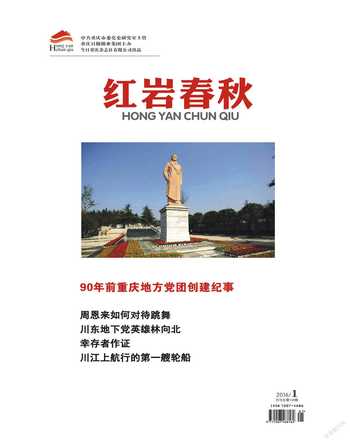写给一座城的情书
2016-09-10马拉
马拉
我把《重庆晨报》“城与人”专栏《重庆摄友爱拍门》那一期,摊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一张比半边城门还大的会议桌上,请同样有城门情结的研究员杨筱确认一个细节。当读到“通远门对面的街上,有个好像叫‘一四七’或是‘三六九’的小酒馆,玻璃橱窗后面摆起卤得黄桑桑、香喷喷的猪耳朵、鸭脚板,坐着一些老头在喝酒。”杨筱一拍桌子说:“我可以肯定,不是‘一四七’,是‘三六九’。因为小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给我们老汉(四川方言,即父亲)打啤酒。”
“三六九”正对通远门
“三六九”正对通远门,按老重庆的话来说,是抗战时期来自江苏的“下江人”开的馆子,跟城里古籍书店旁边那个有名的“陆稿荐”属于一路的风味,素菜精致,招牌菜有卤汁豆干和烤麸,烤麸是一种很好吃的面筋。“当时我就背着军用水壶去打啤酒,老汉是军人,家里有的是军用水壶,全身披挂,一去就打两水壶”。
这是杨筱对通远门最初的感觉,带着夏天和啤酒的味道。当时她的家并不在通远门边,通远门只是她日常生活地图上的必经之地,在妈妈教书的南纪门和爸爸工作的重医之间。
重庆晨报副刊曾连载杨筱的长篇学术随笔《通远门》,里面的《柔软的城墙》《校场》《杨柳街》《城内心事如麻》等多篇城门故事,是一个重庆女儿写给母城的一篇篇情书。当年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田大畏,是抗战时期曾在通远门和九块桥之间遛达的田汉之子,对杨筱《通远门》的评价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柔软的城市史”。
通远门曾经在杨筱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说不清楚,她说:“拿笔来,我来画。”她“唰”地一下,在一张A4纸上划出了两条曲线,“这是长江,也叫大河,也叫岷江。随后,一些街巷和城门,就在河边顺坡而上,延伸开来”。
通远门旁边有一个通车的隧洞,很多人误以为这是通远门或通远门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本地人叫“穿洞”的隧洞,是1946年为抗战胜利而开通的“和平隧道”。洞口前面那条路,合并了原来的五福街和走马街,就因“和平隧道”而得名“和平路”。当年张献忠破门之后,正是顺着这条路杀向较场口的。
这条路也是杨筱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和妈妈一起从南纪门中学出发,穿过下半城,走过和平路,穿过通远门到2路(后来的402路)电车站去乘车到爸爸的单位。“经过马蹄街、天官府,郭沫若曾住天官府,田汉住九块桥,从火药局爬上来,过穿洞去赶车,要一刻钟的样子。前面的五福街、走马街、金汤街、水石巷,苍坝子,都是一些细碎小街。我来回都看得见通远门,问过妈妈,她说叫通远门,但没解释。后来才知道是古城门”。
通远门上曾喂猪
在长篇随笔《通远门》中,杨筱曾捕捉到了通远门上下民间生活原生态的场景:
“由七星岗从通远门进来,是金汤街,街至今还在;下面接五福街。两边有水市巷、曹家巷、铜鼓台、火药局、至圣宫等;到了上回水沟和潘家沟之间,开始变成走马街,两边有仓坝子、百子巷、蒋家院子等,弯弯地通向校场;校场中央围绕着一个很小的圆心,构筑成一排排平行的小街棚,每一条小巷都是一个小小的专卖市场,比如新衣服街、老衣服街、草药街、瓷器街、木货街等等。棚街密集但不结实,用木板构筑,它像一碗牛奶一样,深切地荡漾着重庆微温的生活的辛勤与侥幸、苦涩与幸福,市民就像小麦圈,漂浮在那碗牛奶浸润的生活中。”
现在很难想像,通远门上面,曾经是一个片居民区。“老百姓的房子古色古香,穿斗平房连成一片,默默无闻的小日子好过得很”。上面非常繁复的居民区里面,清一色像模像样的穿斗式民居、坡顶、四柱,还有柱础。2003年杨筱带朋友上去看时,一片茶馆之间,老百姓叫的一个“大砣儿”雕塑还立在正中。
在门外柴灶上烧火的一个婆婆说,她住这里30几年了,前几年屋头还养起猪的。他们没怎么觉得这是城墙,而只是自己家里的一堵墙,所以水池、煤池、花台都靠在城墙上。旁边的鼓楼巷很安静,“像一个古代的市民女孩。”杨筱说。
属于民间的城
长大后,杨筱到南川插队下乡,远离通远门以内的母城,只能像一个好吃狗痛忆美食一样咀嚼城里的月光,哪个弯是啷个拐的,哪里有块很滑的青石板,哪条小巷的名字很好听。“我一定要调回来,我就在想我那个城,两年半,我一定要回来”。
杨筱1986年曾调到敦煌工作,小姑娘时代的母城记忆,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颗种子:为了这个城,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回来。“上次作家王朔到重庆对记者说,重庆是一座让你瞬间就可以复活过来的城”。
写了《通远门》之后,杨筱出版过一本《陪都遗迹寻踪》,“原来的名字叫《苍茫的城市》,通远门是把重庆古城推向近代的一个关节点”。跟她在随笔和书里写的那个城相比,现在的重庆,马路还在,但两边有些东西不在了。“只有重庆饭店那样的建筑还在,但这不是我怀念的东西,因为重庆的这种洋式建筑,上海也有”。
在漫长的筑城史中,重庆跟西安、北京、南京的皇家气象不一样,重庆不是京城的样范,而是沿着长江水边,一个居民点连着一个居民点,一坡梯坎接着一坡梯坎地慢慢爬上来的。“重庆的城市和城门是从我们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长江沿线城市都跟重庆学”。在民间和皇家之间,北京显然是皇家的城,而重庆更多是属于民间的城。
即使抗战时期,重庆陡然获得“战时首都”这个皇家称号,杨筱在《通远门》随笔中还是发现“这个骨瘦如柴的城市,支持着陪都人的蔬菜、水、肉、米、油、纸、书、戏剧、电影、文学、版画,抵抗着远东战场中心的大轰炸,用枯黑的瘦手一片石头一片石头地挖出防空洞,那些英勇的防空洞,现在很多在搞餐饮,种植和丝印业呢”。
外公的老巴县口音
由于母亲从小就住在通远门内和平路下面的上回水沟一带,所以杨筱现在都不愿意搬出这个半岛,死守这个半岛,只要闻得到半岛的味道,就够了。而这个味道是曾住在枇杷山的女儿山山发现的,山山说:“枇杷山有枇杷山的味道,重医有重医的味道,解放碑有解放碑的味道。”
杨筱说:“我喜欢这种味道,如果别人问我,我就说我是300年重庆人。我们都是从康乾年间湖广填四川来的,这么算起来,就是300年。”
当年日本人炸重庆,炸没有炸我们的城门呢?我的这个提问,一下子就把大轰炸、城门和杨筱的外公联系在一起了。1941年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发生前四天,日机就炸了通远门一带,幸好没炸中,但金汤街被炸得很惨。
杨筱的外公丁荣灿当时是管防空的。民主人士丁荣灿1933年毕业于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属于重庆第一代高级警官。20世纪40年代,丁荣灿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防空司令部第三处少将处长,他曾说:“说到第三处,全称消极防空处,意即人民防空处,第一处叫积极防空处,用高射炮打飞机,因为空军已经不管用了,第二处叫情报处,情报精准无与伦比。”
第三处搞的人民防空,是防空司令部最正式的业务,1941年防空司令部升格为中央级,此时任用专业人员,丁荣灿升职少将。这位将军的一生是屡败屡战的一生,他见证了一座失去制空权的古城,怎样在大轰炸的火海中挣扎。
将军的最后一次挣扎,是晚年拼着老命,写完他的《陪都防空史略》。“他挣扎着写了2万多字,把自己写空了,第二年就死了。我核实过他写的,大的时间上,一点都没错。外公说:‘我的故事多得很。’但我当时远在敦煌,没办法听。外公一口老巴县口音,很土,但很好听”。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