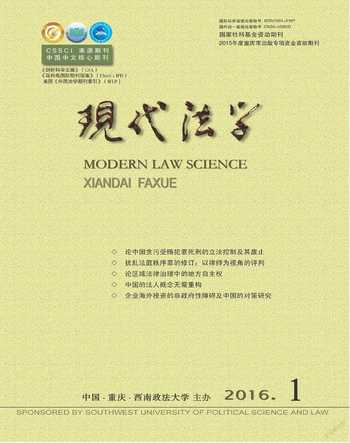论代理权授予与基础行为的联系
2016-09-10殷秋实
殷秋实
摘要:
代理权是否受到基础行为的影响,对于代理权的有无和范围的判断非常重要。有因无因两种解释方案的选取,需要以何者能够更好的平衡本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为根据。无因性将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切断,使得相对人可以只根据授权行为判断代理权范围,极大地保护了交易安全。虽然无因性也具有诸多劣势:一方面,无因性提供的不区分的保护会将恶意相对人也纳入保护范围之中,无因性也不能对相对人的所有合理信赖都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在基础关系全部消灭或者孤立授权时,由于被代理人没有基础关系和其他法定求偿权可以借助,而只能求助于侵权法或者后合同义务制度的保护,对被代理人的保护力度十分薄弱;但无因性相比于不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有因性来讲仍然具有巨大优势。在有因性和表见代理制度的组合下,不仅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可以被有效替代,被代理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并且,考虑到代理根本上是为了被代理人利益的制度,有因性的选择更具有正当性。综合来看,辅之以表见代理制度的有因性是更好的解释选择。
关键词:授权行为;基础关系;有因性;无因性;表见代理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08
代理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代理效果是否发生,也就是被代理人是否要承担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效果。而这种效果首先取决于代理权有无和范围的判断。由于代理涉及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因此产生了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否会对代理范围发生影响的问题。考虑到代理权的发生来自授权行为,代理权的范围也来自对授权意思的解释,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授权行为有因无因的问题。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授权行为是否要受到基础关系的影响,学理上倾向于整体上采用无因性[1][2];或者区分情况,在授权是直接对相对人做出的情况下接受无因性的原则[3],总之,至少在部分层面上采无因性。这种观点应是受到德国和我国台湾学说和理论的影响。时至今日,代理法的理论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我国《合同法》在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看起来和无因性理论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重合。而本就在保护本人利益上有优势的有因性理论如果能通过表见代理弥补在相对人保护上的不足,有可能是比无因性更好的解释选择。解释论上做何种选择,需要考察两种方案在本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保护上的优劣,以判断哪种解释能够更好地满足法律和经济社会的需要。
一、 授权行为无因性及其功能
授权行为无因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演变而来。在代理制度刚被承认之时,代理被认为是基础法律关系的外在层面,应受到此基础关系的支配。这样,代理、代理权授予和委任被认为是同一意义,代理既然和委托密不可分,自然也与之同时成立或消灭[4]4。抽象性的产生得益于《德国普通商法典》(Allgemeine Deutsche Handelsgesetzbuch, ADHGB)的规定。当时商法典关于代理的规定不是建立在学说之上,而是为了满足商业实践的需要,其特点就是经管人拥有与其职责相适应的一般性的权利范围,而且这种授权相对于第三人来说不能被有效约束,因此出现了不受约束的授权的新概念
Rappresentanza,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Volume XXXVIII, Giuffrè, 1987, p.459.。这样,无论有没有内部限制,落入法律规定权限范围内的合同都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1886年,Laband以《德国普通商法典》的规定为基础提炼出独立而抽象的代理权。Laband认为代理和委托并不是同一个关系的内部和外部,而是构成要件完全不同的两个制度,而且Laband推广了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再将之局限在具有一般权限范围的商事代理(经理)权,而是也可以适用于单个事项的代理中。被代理人是否受到代理行为的拘束只考察代理人的表现是否符合外在的代理权。对相对人来说,重要的是代理权,委托合同并不重要——哪怕相对人是恶意的
La rappresentanza, in Il codice civile commentario, art 1387-1400, diretto da Francesco D. Busnelli, Giuffrè, 2012, pp.64-69.。抽象性的观点被德国民法典所采,并对之后各国的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征服了全世界”[4]6。
笔者认为,授权行为的抽象性和独立性密切相关,对授权行为无因性的全面理解,需要以独立性的讨论为起点:授权行为的无因性其实就是授权行为在各方面完全独立于基础行为,两者之间互不关联。由于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均为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由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构成。授权行为相对与基础行为的独立和因此表现出来的抽象,实际上也反映在以上三个方面。
在主体上,虽然比较法上也有认为可以通过双方法律行为来授权的观点[5],但授权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单方行为
我国法上也如此解释,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65条的规定体现代理权授予应以单方行为进行。(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79.)。通过双方法律行为进行的授权,授权行为的主体和内部关系的主体一致,体现不出区别。通过单方行为的授权则有所不同,这体现在授权意思表示的对象上。如果代理权授予只能由代理人进行,则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在主体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之前提及我国有部分学者认为至少在外部授权的情况下,授权行为具有无因性。可见在授权的对象上,我国学说采纳了和德国法相同的观点:授权可以对代理行为相对人或者代理人为之,分别构成外部授权和内部授权。更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授权人把已经授予的代理权向第三人宣告,这是向外部宣告的内部授权。而且,对外告知已经授予的代理权被认为是代理权的再次独立设定。两次独立授予代理权并列存在,而且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命运[6]。对授权行为的这种复杂安排,也服务于无因性的目的和功能。
授权行为内容上的独立性,表现在代理权的范围和委托合同中事务处理权的范围可以不同。如果代理权授予和基础关系确实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行为,自然可以各自具有独立的内容。代理权的范围原则上取决于授权的内容,而不受内部关系所表明的目的之约束[7]。当然,如果代理权的范围小于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具有的权限,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问题;但代理权的范围大于事务处理权的范围时,意味着部分授权行为是没有基础行为做依托的,这更深刻的表现了代理和基础关系的分离。不过,归根到底,这种内容的独立是法律事实独立性的反映。因为内容的差别可能会因为两种原因产生:在授权之初,授权范围就大于委托合同权限的范围;或者由于基础关系嗣后的部分撤销或者消灭而导致授权范围大于委托范围。两者分别是代理产生与消灭独立性的部分体现。
法律事实涉及到法律行为产生、消灭和变更的事实。
授权行为产生的独立性首先体现在授权和委托的分离之上。一方面,委托合同中可以有代理的存在,也可以没有代理而只存在单独的委托。另一方面,代理也可能以其他关系为基础: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等都可以作为代理的基础关系
德国法曾经将类似指令付款、服务行为等作为无委托授权讨论,但这些都伴随着内部的法律行为,因此这种代理并没有和内部关系区分开来。可能由于代理和委托在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一致关系,这种理论在当时的目的和重要性在于将授权和委托区分开来。(参见:Giovanni Di Rosa, La astrattezza della procura, alle origini di un dogma, in Contratto e impresa, dialoghi con la giurisprudenza civile e commerciale, 1994, pp.108-110.)不过,也有人认为所有代理的基础关系都是委托的理论。诸如合伙、雇佣中的义务人享有代理权是基于一个单独的委托合同,而不是基于合伙或者雇佣。(参见:Salvatore Pugliatti, Studi sulla rappresentanza, Giuffrè, 1965, p.207.)。这种分离意味着授权和委托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表示,可以分别独立作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个意思表示不能混合在一个行为之中,缔结基础行为的意思表示也可同时包含授权的意思。但这只是意味着两者可以结合,并不意味着两者因此同一。不过,授权行为独立性更重要的表现是代理权的授予可以“孤立”进行,也就是完全没有基础关系的代理权
即便《德国民法典》第168条规定:意定代理权的消灭,依照所由授予意定代理权的法律关系定之。德国学者也认为本条仅规定消灭而不适用于产生,因此意定代理权在没有基础关系的情况下也能产生。(参见: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04.)在我国大陆地区民法语境下,由于没有这种消灭上牵连性的规定,承认孤立授权更无障碍。。这可基于本人授权时明确只授予代理权,但是不缔结任何基础关系;也可基于基础关系虽然存在,但由于无效等原因而消灭。后者实际上是消灭事实独立性的体现。
授权行为消灭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基础关系的无效、被撤销或者不成立,不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
虽然德国法遵行无因性的法则,但是《德国民法典》第168条仍然规定意定代理权随其基础关系的消灭而消灭。表面上看,这是对无因原则的严重违反。不过,该条的适用被限制在纯粹内部授权的情况,对于外部授权和向外部宣告的内部授权来说则并不适用。(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19.)。这不仅仅表现在基础关系整体的无效、被撤销或者不成立上,也表现在基础关系的部分撤销之上。由于基础关系(以委托合同为例)通常都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设立,出于意思自治原则,委托人当然可以自由撤销委托合同,这种撤销可以表现为对委托合同整体效力的消灭,也可以表现为对受托人行为范围的部分调整——委托合同部分的撤销表现为内部的指示和限制。委托关系的无效、被撤销和不生效力不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也意味着内部关系上的指示和限制(即委托关系上的部分撤销)不影响代理权的范围。内部关系上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所做出的指示和限制不会对代理人代理权的范围产生影响,是无因性理论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8]。
综合来看,代理权授予的独立性和抽象性在诸多方面均有体现。概括来说,抽象性意味着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的完全分离,两者是彼此完全独立的法律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有重合和关联,但重合只是偶然,分离才是根本。这种分离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两者效力事由上的彼此独立。因为内容上的独立实际上和授权的产生和消灭事由息息相关,而主体上的独立性以及授权对象的复杂安排也是服务于无因性在效力切断上的目的和功能。因此,无因性真正重要的表现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孤立授权的存在,授权可以脱离基础关系而单独授予;二是基础关系的无效、被撤销等不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和范围。这两个方面不仅在全有全无的层面上存在,也可以只在部分层面上运行。我国学者通常理解的授权行为无因性的表现在于基础关系无效、不成立或者被撤销时,授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9]。这种理解虽然抓住了无因性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略显不足。而要全面分析有因性和无因性在功能上的区别,就需要更全面地理解无因性。
考虑到无因性将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完全分离的技术特性,以及代理中涉及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相对人三方主体的特性,无因性所欲达到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由于相对人通常不能了解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体为何、是否有指示和限制、基础行为是否有效等情况,如果代理权的范围受到这些内部因素的影响而受限或者消灭,相对人因为这些自己不可知的因素而承受无权代理的效果,对相对人并不公平,也会对交易安全造成很大风险。相对人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投入很大的调查成本,这也不利于交易的快速进行和经济的发展。如果相对人因此而不愿意和代理人发生交易,对整个经济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无因性通过切断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的关系,免除了相对人探求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内部关系的义务,相对人可以直接依据授权行为判断代理人的权限,从而解决了相对人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现代代理制度实行抽象原则,主要出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考虑,从而保护法律的安定性[10]。
二、有因性与无因性的选择:本人利益的角度
法律制度常常涉及多方主体和他们彼此冲突的法律利益,因此制度设计和解释也应该注意平衡当事人之间冲突的利益。如果过于偏重一方的利益,致使另一方完全得不到保护,只会让当事人对这种制度避而远之,而采用其他的制度安排。代理亦是如此,代理也需要在被代理人和相对人利益之间取得妥适的平衡。无因性和有因性理论的选择,也是看何者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目的。在两者的比较中,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角度一向是比较的重点,本人利益则一直处于相对被忽略的角度。但是,授权行为毕竟来自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如果被代理人利益得不到妥当保护,会影响民事主体选择这种制度的积极性。考虑到代理在现代民商事法律生活中的重要性,本人利益的保护也应该得到重视。
(一)无因性下对本人利益的保护
面对代理人的无权代理或者代理权滥用等行为,被代理人能够采取的保护方式无非两种:代理行为对本人不发生效力,从而被代理人不必承担代理人行为的法律后果;代理行为发生效力,被代理人从代理人处获得补偿。在孤立授权和基础关系消灭的情况,由于授权行为可以脱离基础关系而发生效力,代理行为总是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代理人的行为就符合本人的意思表示,事实上,代理人的不当行为极有可能会造成本人的损失
基础关系没有效力时,很难认为本人仍然愿意保留代理权。尤其是基础关系被本人撤销时,可以推知本人并不欲代理人实施行为,若代理人继续实施代理行为就可能给本人带来损害。。这时,被代理人只能寄希望于可从代理人处获得救济。由于这种情况下已经排除基础关系的存在,被代理人不可能通过基础关系获得赔偿。这就需要在我国法下寻找其他可能的请求权基础。
基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请求权是个可能的选择。然而,这受制于侵权法一般条款的解释。这是由于被代理人的损失通常并不是由于绝对权受损害而导致的,因而只是一种纯粹经济损失。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侵权法一直持比较克制的态度。如果依据相对宽松的模式,需要纯粹经济损失具有不法性、经过价值衡量之后应该得到赔偿[11]。如果按照比较严格的解释模式,需要纯粹经济损失符合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者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要件[12]。不过,即使在比较严格的模式中,由于善良风俗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道德判断,而建立在类型化的基础之上[13],因此,不管采取哪种模式,被代理人能否获得赔偿决定于其损失是否可以被类型化为一种值得保护的损失。另外,代理人的主观方面可能也有故意的要求。这些都让被代理人比较难以获得救济。
被代理人也可以通过后合同义务来追究代理人的责任。虽然对后合同义务产生的责任,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学说也没有详细讨论
关于后合同义务的初步讨论,参见:焦富民.后合同责任制度研究[M].河北法学,2015(11):23.,但是依据《合同法》第92条的规定,既然在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则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不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的行为也归入到后合同义务的范畴中应该并不困难。不过该制度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尚不明晰,具体依据哪条作为请求权基础也不明确,有待于学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被代理人请求的依据和效果也就陷于不确定的境地。
如果代理制度中直接规定有法定请求权,也可以解决问题。《民法通则》第66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似乎具有这种作用。有学者认为如果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没有基础关系,则应当根据其过错向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2]655。这似乎试图构建没有基础关系时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独立请求权。
不过,笔者认为该条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条文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构成要件。“不履行职责”的表达似乎暗示代理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但是义务的来源却并不清楚;单纯的过错可以作为归责原则存在,但从来不是只有过错就可以归责,而且过错也要回溯到违反某种义务。但是,授权行为本身并不能产生代理人的行为义务。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基础关系(如孤立授权)的情况下,代理人在完成代理行为时仍然有不能给本人造成损害等注意义务——而且认为这种义务是代理权行使中天然具有的、应该照顾本人利益的一般性的忠实义务,违反这种义务会产生合同责任
Dei contratti in generale, in Commentario dei codice civile, art 1387-1424, a cura di Emanuela Navarretta, Andrea Orestano, diretto da Enrico Gabrielli, UTET, 2012, p.55. 我国学者有类似观点,认为代理权在内容上包含了一定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和纯粹的民事义务不完全相同,更多是一种职责,其体现之一是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必须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必须履行诚信义务等。(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29.)。这种构建本身就违反了代理权无因性的前提:代理权和基础行为的分离,使得义务停留在内部关系的层面上。否则相对人就不能只就授权行为判断代理权范围,无因性也就无法达到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按照无因性的理论,授权行为只是授予代理人能够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为的资格,却不产生任何权利义务。代理权授予并非债的发生事由[14]。而且,从教义学的角度来看,授权作为被代理人的单方行为也不应该让代理人负担义务。事实上,上述观点中提及的代理人义务,和基础关系中的附随义务等并无质的区别。如果基础关系被撤销后,这样的义务仍然存在,无异于重新引入了一个基础关系,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就不是全然分离的。因此,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缓解无因性对本人的严苛性,但其在实质上已经背离了“纯洁无垢”的无因性。
事实上,对于这些义务和过错的理解恰好是要回归到诸如侵权行为、后合同义务等情形。在无因性理论下,该条本身应该作为注意性规定,提醒法官此处可能有代理人责任。真正的请求权基础仍应落实到其他具体的规定,如《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或者《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等。而且,从体系上看,本条也无法承担保护被代理人的重担:第66条第2款处于无权代理的规定下,也应该适用于无权代理的情况。而无因性条件之下,即使基础关系消灭,授权行为依旧有效。因此不满足第66条第2款的适用前提。
孤立授权的情况稍有不同。孤立授权通常出于本人对于代理人强烈的信赖
没有管理关系为基础的授权通常是对家人、朋友发出的授权。Alessandra Salomoni, La rappresentanza volontaria, CEDAM, 1997, p.39.,代理人的任何行为似乎都处在代理权的范围之内,被代理人因而应该承受这种后果。被代理人既然做出这种选择,就应该承受代理人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似乎也不应该有无权代理或者代理权滥用所带来的追责问题。不过,法律是否应该如此解释孤立授权是存疑的:被代理人总是承担代理人行为的效果相当于被代理人事前放弃可能的请求权,而这种放弃应当受到《合同法》第53条的限制;而且,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通常也有信赖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免除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等行为的责任。因此,被代理人应该得到救济。但是,此时可供被代理人选择的请求权基础就更少了——由于没有事先存在的合同,也就没有后合同义务的存在。被代理人的请求权就只能依据侵权行为,希冀代理人的行为能够符合侵权法保护纯粹经济损失的条件。
虽然被代理人并非不能通过侵权行为或者后合同义务的方法来获得救济,但这总是一种需要寻求进一步解释和实践支持的曲折路径,不如合同救济或者直接请求权的方式那样明晰确定。这种对本人利益保护的不周全是无因性理论的逻辑使然。原则上,有权代理之下,代理人的行为具有正当性,被代理人应该承担代理人行为的后果,而不能向代理人追偿。这种正当性建立在本人意思之上。无因性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切断了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时,代理权的维持可能是违背被代理人意愿的,代理行为虽然是有权代理,但被代理人需要救济。而有权代理的前提又使得被代理人在救济上需要辗转于侵权行为等途径。改善这种境况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之间的联系,如德国司法实践中引入《德国民法典》第139条关于部分无效的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判断授予代理权和基础法律行为是否结合成一个第139条意义上的统一的法律行为[1]112。这也是无因性对本人利益保护不足的一个佐证。
(二)有因性下本人保护的优越性
有因性下,代理权也可通过单方行为授予,只是由于在效力等方面没有切断和基础行为的联系,授权行为的独立性只是在形式上有意义,或者说只具有有限的独立性。这首先对孤立授权的情况有影响。有因性下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因此授权行为不能脱离基础关系而存在。孤立授权和基础关系消灭会导致授权消灭是无因性的两面。在“孤立授权”中,如果确实没有基础关系,就会导致授权行为本身不发生效力,但是考虑到当事人确实有授予代理权的意思,出于尽可能保存当事人意思表示效力的考虑,有必要赋予这里的代理权以一个基础关系做支撑。实现这种目的的法律手段是将本人的代理权授予行为解释的同时也是和授权对象达成基础关系的要约,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行为可被认为是承诺。当事人之间既然达成合意,其他的要素可以由任意性规定(主要是委托合同的规定)补充,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照顾义务等附随义务因此可以成为合同的内容。这样,在有因性下不存在孤立授权的问题。既然存在基础关系,被代理人的利益可以比较容易的获得较为全面的保护。
基础关系消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理论上讲,有因性下被代理人的指示和限制会对代理权范围产生影响,基础关系的撤销、无效和不生效力也会导致代理权的消灭。此时代理人的行为已经是无权代理行为,本人可以采用代理行为对自己不生效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是最强的保护方式——这也是有因性被诟病的原因:过于保护本人的利益,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被弃之不顾。
不过,表见代理制度的发展已经极大的限制了有因性这种过于恣意的适用,改变了有因性下本人利益保护的格局。在表见代理制度下,即使代理权已经随着基础关系部分或者全部的消灭而消灭,被代理人仍然可能承担代理人行为的后果。只是这样,在基础关系消灭(如被撤销)但是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被代理人的处境看似和上面无因性的情况类似:有因性和无因性下被代理人似乎都只能借助于侵权行为、后合同义务等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有因性对本人利益的保护看似被表见代理降低到和无因性同样的水平。
其实不然,笔者认为有因性和表见代理的组合仍然会给这种处境下的被代理人提供更多更好的保护。
这首先体现在被代理人有否认代理行为效力对自己发生的机会。因为在表见代理中,并非相对人的纯粹信赖就可以导致表见代理效果的发生。毕竟,相对人的信赖只是相对人可以获得保护的一个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保护必须要以被代理人利益受损来提供——代理人也可以以损害赔偿的方式来弥补相对人。因此,应该区分纯粹的表象和被代理人有“过错”的表象,后者才能让被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当然,这里的“过错”并不是传统语义上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过错,因为被代理人并不对其他人负有义务,这里涉及的也不是对他人法律领域的侵犯,而是做出不当行为者的法律领域。这里的“过错”只是表明让本人承担代理效果正当性的根据——事实上,只要表象是由本人风险范围因素内的因素导致的即可[15]。笔者认为,在基础关系被撤销、无效、不生效力等情况,被代理人负有将这些情况以合适方法通知、公示的不真正义务。这也就意味着,在表见代理可能适用的情形,被代理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履行了通知或者公示的义务来避免表见代理结果的发生,
如我国学者提出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提出:本人遗失、被盗公章、营业执照、合同书及授权证书,或者与行为人特定的职务关系已经终止,已经以合理方式公告或通知,相对人应当知悉的,不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89.)这是通过击破相对人的善意信赖实现的。表见代理既然不被认为是纯粹基于相对人信赖的客观责任,被代理人应该有这种摆脱责任的机会。
如果确实构成表见代理,有因性下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请求权也可能和无因性下不同,这建立在表见代理和有权代理的区别之上。虽然同样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但是两者的逻辑前提不同:无因性下,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是基于代理人行使的是仍然有效的代理权;而有因性下,授权已经随基础关系的消灭而消灭,表见代理因而是无权代理的一种情况。虽然都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但无因性下是真正的有权代理,有因性下却是本人承担的一种责任。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这种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表见代理虽然需要可以归因于本人才可以让本人承担责任,但是这种归因并不是由于本人违反对相对人的行为义务。相对人的信赖其实是由代理人的行为引起的,是代理人实施了违反本人利益和意思的无权代理行为。于是,表见代理的结构就是代理人实施的行为,导致被代理人依据法律规定承担责任。所以,被代理人实际是在为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具体来说,在无权代理中,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的责任被认为是一种“担保”责任[16]。基础关系消灭时,代理人的代理权也随之消灭。如果代理人在这种时刻仍然为代理行为,则理论上代理人就应对相对人承担自己有代理权的担保责任。表见代理也是无权代理,但是在表见代理中,却是被代理人承担了代理行为生效的责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代理人承担了本应是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代理人的责任因此被免除,被代理人应该有向代理人追偿的权利。这样,被代理人遭受的损害就不应该停留在被代理人处,而是应当由代理人承担。在有基础关系救济的场合,本人可以直接通过基础关系获得救济,自无异议。在没有基础关系的场合,代为承担责任的行为应当赋予被代理人以求偿权。从利益关系上看,这实际上和《担保法》第31条规定的求偿权的原理相近。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66条第2款的规定在此语境下可以获得独立意义:其不仅仅是提醒法官适用其他请求权的注意性规定,而是本身就可以在无基础关系的情况下为被代理人提供求偿权
有学者似乎持类似观点,认为本条似乎不问有无基础关系,只要造成损失,代理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86.)。毕竟,这里和无因性的情况根本不同:在无因性的前提下,是违反本人意愿的代理权的继续存在,导致本人对代理人求偿的困难;而在有因性辅之以表见代理制度的情况,则是本人替代理人承担了责任。
(三)小结
本人可以通过代理行为对本人不生效力和本人对代理人求偿两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无因性下,由于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的完全分离,基础行为不生效力不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代理人的行为总是有权代理。因此本人无法主张代理行为对自己不生效力的保护。在孤立授权和基础关系消灭的场合,本人对代理人也无法从基础关系角度来求偿,因而只能通过侵权行为、后合同义务等方式曲折的获得赔偿,保护效果并不理想。而在有因性下,在可能适用表见代理的场合,本人也可以主张自己已经进行了通知、公告等行为来避免承担代理行为的效果,因此有可能采用代理行为不生效力的保护方式。即使本人需要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由于表见代理是一种法定责任,而且被代理人实际上承担了本应由代理人承担的责任,也应该认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有法定求偿权。因此,有因性能够对本人提供更快捷和充分的保护。
三、相对人利益的保护
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被视为无因性相对于有因性理论的巨大优势,也正是基于此,无因性得到了立法和理论的接纳。不得不承认,单纯的有因性理论确实不足以对相对人提供充足的保护——确切的说,有因性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保护。考虑到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重要性,当时的立法和理论摒弃有因性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表见代理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这反映在表见代理对无因性功能的有效替代和无因性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不足之上。
无因性通过分离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之间的联系,的确对相对人提供了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对相对人不加区分的全体保护。在无因性理论中,对本人仅仅在内部关系上对代理人做出的限制,就算相对人明知或者被代理人已经通知相对人,也不妨碍代理行为效力的发生,
La rappresentanza, in Il codice civile commentario, fondato da Piero Schlesinger, diretto da Francesco D. Busnelli, Giuffrè, 2012, pp. 65-66.因为授权和基础行为是两个彼此区分而无联系的行为。在基础法律关系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如果相对人明知这种情形存在但仍然与代理人为代理行为,由于授权行为没有被撤销,故相对人并不构成任何恶意
似乎只要本人没有撤销授权行为,就应该仍有让代理权继续存在的意思。(参见: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36.)。因此,不管相对人是否善意,以及善意是否存在过失,相对人都可以获得无因性的保护。
相比而言,表见代理的保护对象是被限定的。在我国法下,表见代理不仅要求相对人相信代理权存在的表现,而且要求这种相信是善意无过失的
学说与实务都是如此。关于学说,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J].法学,2013(2).关于实务,参见: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S].第13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因此,就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而言,表见代理制度可以替代无因性提供的保护。而且,和无因性相比,表见代理提供的保护虽在在量上不及无因性,在质上却胜出。因为无因性的保护将恶意和有过失善意的相对人都纳入保护范围,这实际上是以损害本人利益为代价去保护不值得保护的相对人,是一种过度保护。而表见代理制度具备筛选机制,可以将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以外的主体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是更优的技术选择[1]114。因此,表见代理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范围内)替代无因性。
无因性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也有不足之处。这表现在被代理人对授权本身进行修改或者撤销之时。和代理权授予的外部授予与内部授予的区分一样,对代理权的撤回也可以有外部和内部之分。而且,授予和撤回之间并不需要具有对称性,外部授权可以内部撤回,内部授权也可以外部撤回[17]。理论上讲,这里被代理人针对的是代理权而不是基础关系,因此一旦撤回,代理人就丧失代理权,也就没有无因性适用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人此时不存在合理信赖:外部授权或者向外部宣告的内部授权被内部撤回时,如果相对人不知道这种撤回,则相对人仍然存在信赖。而且这种撤回可以只是部分撤回,也就是被代理人对授权进行修改的情况
对代理权的修改实质上就是代理权的部分撤销。(参见: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Volume II, contratto, Giuffrè, 2000, p.101.)。这个时候,相对人理论上就无法获得无因性的保护。无因性理论要解决这种情况,就需要理论上解释出代理权仍旧存在——譬如德国法理论认为将内部授权外部宣告时相当于又进行了一次授权,这样内部撤回只是撤回一个授权,另一个授权行为依旧有效存在。但是,在授权人没有向相对人告知授权的情形,无因性理论就不能提供保护。相比而言,表见代理却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无因性的不足还体现在对代理权滥用的处理之上。代理权滥用是一种代理人违反被代理人利益或者意思的行为,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权滥用时,代理权消失。由于滥用代理权的行为表面上处在代理权的范畴之内,无因性理论对此无能为力。在代理权滥用时,如果第三人恶意,则内部基础关系就成为划定代理权的依据。[16]342在无因性的前提下,代理权滥用理论不外乎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代理权的范围和基础关系再度结合。[8]91因此,对于代理权滥用的情况,无因性理论处理起来捉襟见肘,不得不重新求助于有因性理论和表见代理制度。
当然,无因性也可以和表见代理制度搭配来解决自身保护范围不足的问题。但是在无因性下,既然两者都具有保护第三人的功能,就需要划定理论各自的地盘,这会导致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被严重限缩。在无因性起作用的领域内,表见代理不能代替无因性规则,因为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无因性适用于基础关系和代理权授权范围不一致的情况,表见代理则是解决无权代理情况下的问题。如果基础关系被撤销时,只能适用有权代理而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因为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无权代理,而这里依据无因性授权依然存在[2]644。这样,和有因性与表见代理制度的组合相比,无因性下是“大有权代理+小表见代理”的组合;有因性下则是“小有权代理+大表见代理”的模式。这虽然可以解决无因性保护范围不足的问题,却不能解决无因性保护范围过宽的问题。而且,同样是为第三人提供保护,在有因性的情况下,只需要一个表见代理制度就可以解决;在无因性的情况下却需要两个价值判断上不统一的制度。这也是无因性本身的逻辑导致的缺陷。
因此,虽然无因性相比单纯的有因性是一个利大于弊的选择,但是无因性本身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弊端。相比之下,经过表见代理制度补充的有因性足可在相对人利益保护方面提供更加有效和更加统一的解决方案。表见代理在保护相对人利益时具有优越性的原因,在于表见代理制度和无因性保护方式上的不同。无因性通过切断授权行为和基础关系之间的联系,构建总是有效的授权行为的方式来提供保护。虽然无因性以保护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为目的,但采取的方式却是间接迂回的——其是从被代理人授权角度出发。而且,这种切分虽然在技术上简洁明了,但“一刀切”的方式也使其失去了灵活性。相比之下,表见代理制度采取的手段更加直接——其直接以相对人的信赖为基础构建制度,构成要件上更具有灵活性,也能提供更加全面的保护,可以解决无因性理论无法良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解决相对人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时,表见代理配合有因性的解释选择更有效率。
四、有因理论的正当性
在代理中,本人利益似乎并不重要。虽然代理的基础关系通常涉及受托人对委托人事务的管理,本人利益因而具有重要性。但是在代理中,重要的是代理人的行为要以本人名义,至于是否为本人利益则并不重要[18]。笔者认为,这恰好贴合无因性的理论构造。在无因性下,基础行为与授权行为分离,本人利益因而保留在基础关系层面上;代理权的行使就不必受到本人利益的约束,只要在代理权范围内,便可以让本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效果。
然而,授权总是要为某个主体的利益,不存在纯粹的不为任何主体利益的授权。而这不外为了被代理人利益的授权和为了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两种情况。当然,这里的利益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简单财产利益的计算,而是一种真正的法律和经济利益
Commentario al codice civile, a cura di Paolo Cendon, art 1343-1469bis, Giuffrè, 2010, p.681.。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利益实际上是指代理人处理的是谁的事务。而无因管理中对于他人事务的界定方法值得参考。毕竟,和委托相比,无因管理只是欠缺当事人约定这一前提。在无因管理中,他人事务或者是客观的、可以依据权利确定属于他人的事务;或者是主观的、依据为他人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14]333。照此理解,为本人利益的授权就是以处理本人事务为标的的授权;而为代理人或第三人利益的授权,则是以处理代理人或者第三人事务为目的。亦即,这种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存在指向代理人主观权利的利益
Alessandra Salomoni, La rappresentanza volontaria, CEDAM, 1997, p. 229.。譬如:甲是乙的债权人,丙是乙的债务人时,乙可以授权甲代自己收取对丙的债权并保留款项,丙一旦支付,则丙对乙和乙对甲的债务均告消灭;亦或甲从乙处购买物品,并欲将之转卖给丙。为了避免可能的多重征税或者可能的登记手续等繁琐,甲在支付价款后,从乙处获得授权,以乙的名义将物品卖给丙,而由甲保留丙支付的价款。
为他人利益的授权看起来可以独立于基础关系。因为授权本身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也可以为代理人利益而赋予。而委托等基础关系通常是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存在。在为代理人和第三人利益的授权中,授权人在此并无利益,或者利益已经得到满足。此时,行为的利益和风险都由代理人一并承担。
Giovanni Di Rosa, Rappresentanza e gestione: forma giuridica e realà economica, Giuffrè, 1997, p.149.既然如此,法律也没有必要赋予基础关系——或者说,即使这里存在委托等基础关系也没有意义,因为并没有需要照顾的利益。这样,授权和基础关系可以完全分离,表面来看,这里也有无因性的适用,而且恰好体现代理人的行为不需考虑本人利益的情况。
不过,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种为代理人或者为第三人利益的授权能够实现的条件,在于授权之时或者授权之前当事人之间额外的约定。本人对代理人的授权是对这种约定的一种履行。事实上,只有这种授权是一种特殊的履行行为时,才能授予这种代理权。只有授权人能够承担允许意定代理人进行法律行为的义务并且已经承担该义务时,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才能被允许[19]。
这揭露了更深刻的利益关系。所谓为了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虽然确实是为了满足代理人等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其实产生自额外的合同关系。代理人行使代理权的后果虽然让行为的经济效果归属于自己,但是由于其仍然使用了本人名义,因此行为的法律后果仍然归属于本人。更重要的是,本人在这种法律结构中并非没有经济利益。事实上,代理人的代理行为也让本人的经济利益获得满足——虽然是以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这样,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因此并没有排斥本人利益,相反其仍然是为了本人利益——这也是本人授权的最终目的。因此,受托人仍然要管理委托人的利益,受托人的利益是通过进一步的关联合同来实现的
Natoli, La rappresentanza, Giuffrè, 1977, pp.40-41. Anche Paolo Papanti-Pelletier, Rappresentanza e cooperazione rappresentiva, Giuffrè, 1984, p. 88.。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并不排斥基础关系的存在或者说基础关系此时没有意义。只不过这里的基础关系不是单纯的为了被代理人利益的委托合同,而是委托合同与其他安排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约定的结合。代理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被代理人的利益。为了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不能以损害本人利益为代价。
因此,此时基础关系仍然非常重要,没有这种基础关系,为代理人利益的授权就无法有效运作。由于基础关系对于这种代理权的重要性,以至于这种代理权不能被孤立授予[19]1053。在基础关系无效和不生效力的时候,这种代理权也应该随之失去效力。不过,这里不涉及基础关系被撤销的情况,实际上,由于涉及代理人的利益,这种基础关系和授权本身没有正当理由都无法被撤销
C. Massimo Bianca, Diritto civile, II, contratto, Giuffrè, 2000, pp.103-104.。所以,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中,授权行为是关联于基础关系而存在的,仍然是有因的。
在为了本人利益的授权中,虽然代理人看似可以只基于授权而活动,不必顾及被代理人的利益。但是,本人利益在代理行为中仍然是基础性的,如此对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行为的禁止才有意义
这种规定的立法原因在于对利益冲突的禁止。(参见: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谢怀栻,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31.),同时,代理人违背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可能构成代理权滥用而被规制。
当然,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和为被代理人利益的授权在很多细节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两者中本人利益都处于重要的、根本性的地位。这说明在意定代理中,只要是本人作出的授权,无论是为本人利益还是为代理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授权,最终都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本人利益的存在就要求在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应该有基础关系的约束,以确定代理人的行为标准,防止代理人恣意妄为的行为,并能够让本人可以方便的获得损害赔偿。代理权授予需要有基础行为的配合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本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代理权既不应该孤立授予,也不应该在基础关系被撤消后仍然存在。意定代理制度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是为了扩张民事主体的活动范围,是一个为了本人利益的制度。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虽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全然牺牲本人利益——这违反了代理制度的经济社会目的,而代理的经济社会目的是代理制度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代理为本人利益的这一特性是有因性理论最根本的正当性,也是无因性的不当之处:虽然来自意思自治,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原因关系,很难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可以干涉他人法律领域的权利
Paolo Papanti-Pelletier, Rappresentanza e cooperazione rappresentiva, Giuffrè, 1984, p. 26.。
这也是授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中,负担行为是双方各为自己利益的行为,但是处分行为的价值是中性的。
因此,物权行为也不会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因此,处分行为被构建成无因行为,和负担行为脱离关系在技术上是正当的选择。然而,授权行为并非价值中性的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了本人的利益,授权行为也会受到效力评价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授权行为无因性的构造在技术上的正当性并不充分。从根本目的上看,授权行为不能和基础关系剥离。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为了本人的利益而服务。
结论
无因性和有因性在解释上的选择,取决于何者能够更好的平衡被代理人和相对人的利益,在维持代理制度价值和该制度对本人吸引力的同时保护交易安全。无因性的确具有诸多劣势:首先,无因性提供的不区分的保护会将恶意相对人也纳入保护范围之中;其次,无因性也不能对相对人的所有合理信赖都提供保护;再次,在基础关系全部消灭或者孤立授权时,由于被代理人没有基础关系和其他法定求偿权可以借助,而只能求助于侵权或者后合同义务制度的保护,无因性对被代理人的保护十分薄弱。但是,无因性将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切断,使得相对人可以只根据授权行为的范围进行交易,极大保护了交易安全。单纯的有因性由于不能对相对人提供任何保护,相比于无因性原则存在巨大劣势,的确不是好的解释选择。基于这点,无因性获得了诸多立法例的接纳。
但是,表见代理制度的介入改变了有因性的这一劣势。由于表见代理制度直接针对相对人的信赖构建,其既可以对值得保护的善意无过失相对人提供无异于无因性的保护,也可以对无因性所不能保护的相对人信赖进行保护,在相对人利益保护方面提供更优的选择。在本人利益保护上,表见代理制度可能会让有因性丧失一定的优势,但在可能适用表见代理的情况,本人一方面依然有否定代理行为效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表见代理中本人承担了本应由代理人承担的责任,这里应该有法定求偿权的存在,因此本人仍然可以获得优于无因性的保护。或者说,表见代理在有因性理论下能够比在无因性理论下发挥更全面和充分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实现制度价值。在有因性理论下,表见代理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对本人利益的过度保护,同时也对相对人利益提供了全面适当的保护。表见代理制度是有因性舞台上的主角。而在无因性理论下,表见代理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相对人提供补充保护,却无法解决无因性保护范围过宽的瑕疵。
另外,代理并不是与本人利益无涉的制度。相反,本人授予代理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本人利益的实现。因此,能够约束代理人和代理权的有因性理论更具有正当性。相比而言,无因性理论(及其和表见代理的组合)在被代理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两方面都劣于有因性和表见代理的组合
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无因说保护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优点,有因说也具备;无因说的缺点,有因说可以克服,因为应该坚持授权行为的有因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28)当然,应该明确的是并非有因说具备保护相对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优点,而是表见代理具备这一优点。“小有权代理+大表见代理”的组合优于“大有权代理+小表见代理”的组合。。后者因而是更优的制度选择,应该被我国法理论与实务接受。
参考文献:
[1]叶金强.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有因构造[J].政法论坛,2010(1):109.
[2]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42,643.
[3]杨代雄.民法总论专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28.
[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5]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M]. 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3-234.
[6]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39.
[7]卡尔·拉仑茨.德国民法通论[M].谢怀栻,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856.
[8]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9.
[9]邓海峰.代理授权行为法律地位辨析[J].法学,2002(8):53,54.
[10]崔建远.民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30.
[11]薛军.损害的概念与中国侵权责任制度的体系化建构[J].广东社会科学,2011(1):236.
[12]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J].中外法学,2009(5):352.
[13]于飞.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J].法学研究,2012(4):57.
[14]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92.
[15]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J]法学,2013(2):64,65.
[16]朱庆育.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352.
[17]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14.
[18]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13.
[19]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51,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