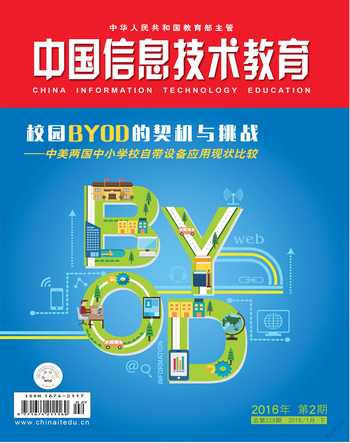学习者角度的MOOC建设新思辨
2016-09-10崔聪罗娜魏松杰
崔聪 罗娜 魏松杰
摘要:近些年来,MOOC作为一种“互联网+教育”的教育课程产物风靡了全世界。借鉴国外的MOOC发展经验,国内的MOOC平台也开始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学习者的角度,对MOOC的优势进行分析,并针对目前MOOC的高辍学率提出了一些本土化的建议:建立学习者对MOOC课程内容重构的体系与提供新的移动学习平台改善学习者的学习体验。
关键词:MOOC;学习者;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674-2117(2016)02-0081-03
引言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是一种“互联网+教育”的新生代的开放教育模式,是一种具有学员大规模化、学习开放性、课程免费等特点的新型网络课程平台。MOOC起源于2001年,先由麻省理工学院发起了开放课件运动,之后全球的诸多顶尖高校也加入到此运动中。在2008年有人提出了MOOC术语的概念。2012年,MOOC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景,被《纽约时报》冠以“MOOC元年”的称号。时至今日,MOOC已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数百万的学习者加入了MOOC这个大家庭,可以说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
目前,国内的研究与实践多立足于全局或者教育者角度,集中在MOOC发展优势、平台的建设、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视频的录制等方面,而缺乏站在学习者的角度对MOOC进行辨析。本文将从学习者的视角对MOOC进行思辨,提出MOOC本土化的改进建议。
学习者角度的MOOC
传统的高校教育往往采用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统一教育模式。[1]学校将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相异、知识水平良莠不齐的学生聚集成班级,采用相同的课程内容、教学目标,进行集体教育。这样的教育模式与互联网时代开放、平等、自由、协作、分享的特征相比,就显得过于落伍。而MOOC的出现给了广大学习者一个释放潜能与活力的平台,使学习者可以实现真正的择己所好、择己所能、择世所需进行学习。
1.学习机会的无限性
首先,MOOC是一种开放的网络课程教育形式,没有时间、地点、人数的限制。[2]这样既不会出现高校热门课“一课难求”的现象,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课程。其次,平台中的所有课程材料与学习资源都是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就像无门槛的大学一样。最后,学习者可以依据自己的习惯和偏好选择适合的媒介工具接入不同的平台进行学习,如使用平板浏览博客、手机参与社区讨论等。
2.学习资源的深广度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数据库正在加速形成,各类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MOOC通过互联网聚集这些优质的学习资源供学习者参考研究。此外,MOOC采用“教学众筹”等新型教育模式,通过互联网汇聚各个知识领域的顶尖学者和拥有多种教学专长的各类教学人员,共同协作分工,从而实现知识的精与深。另外,MOOC将知识碎片化,学习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知识碎片,实现知识体系的多元重构。
3.学习管理的自主性
传统课程中,教师提供的资源和活动处于学习和互动的中心,它们限定了知识探究的边界,学习者学什么和怎么学都是预先计划好的。[3]而MOOC让学习者可以摆脱这种传统课堂的学习模式。学习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知识水平的课程进行学习,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情况控制学习的进度,还可以反复多遍地研究同一个教学内容,推敲难点与重点,进行反思、深究。同时,学习者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参与讨论,获得课程以外的相关知识。
4.学习内容的创新性
MOOC的另一大特点就是通过思维的碰撞产生新的知识。学习者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可能是领域专家、公司职员,也可能是学生、退休工人。MOOC会针对不同课程主题开展讨论学习,所有学习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疑问,寻求其他观点或解答,从中获得启发,完善自己知识体系的构建。此外,MOOC也鼓励学习者在所学课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法编撰新的内容。
虽然MOOC初始时仅提供预先准备的课程资源,如教学视频、练习题、讲解稿等。但MOOC将吸收社区讨论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新知识,迭代更新课程内容,不断完善平台学习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MOOC本土化的改进——学习者角度
调查显示,在我国使用过国家精品课程的人中,有规律使用(平均每周一次及以上)的学生占有总人数的16.4%,教师占7.8%。[4]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前,在与比尔·盖茨的一次会面中曾留下了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语,“为什么IT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就算“互联网+教育”中最为流行的、发展最好的MOOC也存在居高不下的辍学率问题。目前,国外MOOC学习的完成率一般在7%到9%左右,这意味着辍学率达到90%以上。[5]透过高辍学率现象,不难发现MOOC并没能真正地“抓住”学习者的心,这确实值得人们反思。因此,MOOC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以便更好地吸引、留住学习者。
1.学习者对MOOC的重构
连通主义思想认为网络环境下的学习,不再是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活动,而是将专门的学习节点与信息源连接起来形成学习网络的过程。[6]这种学习网络开始于个人,学习者借助外界的平台进行知识的分享与交流,使自己的知识网络得到拓展与延伸的同时也为该学习平台提供了新的观点与认知,产生知识网络的碰撞,从而构建新的知识节点与信息来源,使平台的知识网络能够无限延伸下去。
MOOC正是这样一个大规模地提供知识网络碰撞的平台。学习者们的知识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思维方式与学习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若平台能够更好地搜集整理学习者的博客、课题讨论、学习笔记以及疑问与解答,那么MOOC将不断地构建更新课程内容,表现出更吸引学习者的活力与无穷的生命力。反观如今的MOOC,虽然有社区、博客等其他平台用于学习者发表见解、学习者之间互相交流与沟通,但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用于搜集、整理与重新组织发布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新知识,更难以实现对课程内容的更新与重构。那么如何有效地搜集与管理,以保证新知识内容的正确性、连贯性和整体性呢?
笔者认为,MOOC本土化应针对每一门课程内容组建一个专家团队,刚开始可以是由授课的教师或者其他该领域的专家人士组成。在学习者发表学习笔记或博客、社区讨论时设置一个选项“是否希望专家审核”,如果学习者希望专家审核,专家团队将对搜集到的这些资料进行知识内容正确性与价值性的评定与审核,审核通过后的新知识将进行统一组织与发布,以及用于课程内容的重构。这个评定与发布可以是一周一次,或者更短。经过一段时间后,专家团队可以抽取部分积极交流且采纳率较高的学员组建成新的专家团队,这些新晋专家的加入可以缓解专家团队的工作量,同时他们也将拥有一些相关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团队将越来越壮大,也就能更方便、更高效地对学习者的知识信息进行整合管理,极大地发挥学习者对课程内容重构的作用,不断丰富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形成更完善的知识网络。
2.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体验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等人曾定义过“何为互联网思维”,其中之一就是“用户思维”。本土化的MOOC也应凸显对学习者的关怀,体现“用户思维”,即应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应该落实到照顾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各个环节和细节中的体验,如隐私、共享行为等。
由于MOOC学习是互联网环境下的远程教育,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的交流互动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缺失,易给学习者造成学习过程中的孤独感与低参与度。为了实现同伴学习者之间的沟通与帮助,国外的MOOC多借助社区讨论、博客、Twitter等平台。若国内的MOOC也照搬国外的经验,显然不是很适合中国学习者的情况。记得伯特兰·罗素在《论中国人的性格》中曾提到: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确实,中国人更习惯在自己生活的圈子中、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互动,展示自己,而一旦置身于陌生环境、人群中往往将自己定义为旁观者,保持一种缄口不言、保护自我的状态,自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学习者都希望与外界一大群人取得联系。
因此,MOOC本土化时应注意为学习者提供一个相对舒适、放松又相对安全的学习交流环境。现如今,移动学习携带了社交网络,社交网络自然也能促进移动学习。平台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多种移动学习的参与渠道,如网上社区、微博关注、微信朋友圈等形式。近年来,国内的微博、微信快速流行,几乎每位网民都会频繁参与其一。微博相对于微信朋友圈更加开放、面向社会群体,利于分享内容的扩散,而微信朋友圈则只有互相关注的朋友才能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学习体验,能够更好地保护学习者的隐私。若MOOC能与这两者取得联系,建立MOOC相应的微博板块、微信社区,学习者可以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拥有充分的交互自主权,选择在微博板块或微信社区的朋友圈进行学习互动,这对MOOC的推广与长久发展、学习者的学习成长而言都大有裨益。
此外,MOOC可以通过PC端、移动端搜集到隐含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学习偏好、学习规律等海量数据,针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获取准确有用的学习者信息,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产生MOOC自己的推荐系统,用于推送相关课程、学习者可能感兴趣的主题讨论等。
参考文献:
[1]吴瑜,刘欢,任友群.“互联网+”校园:高校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阶段[J].远程教育杂志,2015(04):8-13.
[2][3]李青,王涛.MOOC:一种基于连通主义的巨型开放课程模式[J].中国远程教育,2012(03):30-36.
[4]徐晓,张世波.MOOC模式在高校整合中的应用前景探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11):20-23.
[5]王立国,窦艳辉.MOOC起源及快速发展[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4(07):57-60.
[6]周煜.当代电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嬗变——从MOOC开始[J].现代传播,2015(9):11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