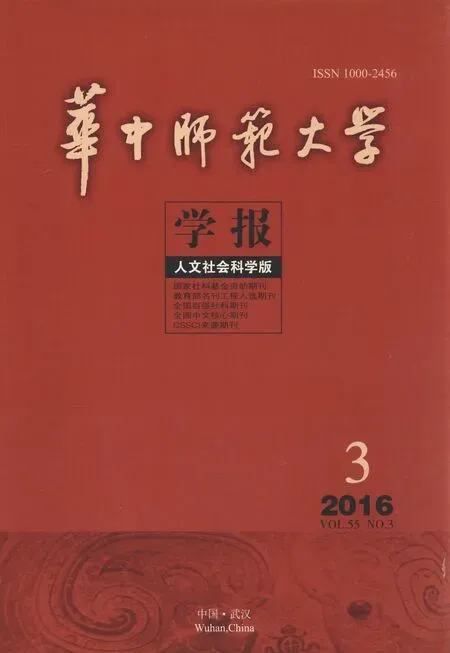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1716—1859)
2016-09-08欧阳哲生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1716—1859)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1860年以前,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驻了十三届传教团,它在中俄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管理驻京传教团,俄国方面制订了一套管理制度对之加以规范和督导;传教团在京拥有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传教团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搜集与北京相关的材料与情报,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迄今中文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的内容。
俄国; 东正教; 北京; 中俄文化交流
在18世纪欧洲驻京人士中,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集传教、商贸、汉学研究、外交于一身,在中俄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管理驻京传教团,俄国方面制订了一套管理制度对之加以规范和督导;传教团在京拥有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等资产;传教团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搜集与北京相关的材料与情报,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对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所获北京文献这些迄今中文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的内容加以评述,以深化对其承担多重使命和在中俄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认识。
一、俄国东正教驻京传教团的管理
有关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历史的分期问题,基于史学家本人活动时期的局限,不同时期的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阿多拉茨基(1849—1896)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685—1745)从东正教进入中国到第三届传教团,“这一时期传教团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管理阿尔巴津人牧众,二是培养学生”。传教团受到了清朝的保护和优待。第二时期(1745—1808)从第四届到第八届传教团,“由于俄中关系出现障碍、某些传教团成员在知识与道德方面存在缺憾以及物质供给不足,驻北京传教团陷入被遗忘和悲凉的境地”①。英诺肯提乙(1863-1931)则将传教团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712—1860)从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去世到《天津条约》的签订。传教团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俄国公使馆角色,其大司祭则事实上履行了俄国政府驻华公使的职能。第二阶段(1861—1902),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布道团职能回归传教,开始组织汉译《圣经》。第三阶段(1902——1916)东正教的纯传教活动获得较大发展。②本文主要讨论前十三届俄国传教团的历史。
俄罗斯东正教的教阶按修士未婚和已婚分为黑白两种:黑神品从上至下为牧首、都主教(派往国外的称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大辅祭、修士辅祭、修士;白神品有司祭长、大司祭、司祭、大辅祭、辅祭、副辅祭、诵经士等。黑神品教士不能结婚,修士司祭者以上统称为神父,以下人员为神职人员。白神父可以结婚,但不能晋升为主教。派遣赴京的前十七届传教团传教士最高职位为修士大司祭,其教阶层级明显较低。“在北京的传教士起初依据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的文书行事,而后接受外交部的领导,特别是执行了圣务院的指令”③。而“在头一百年当中,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一直受到离中国距离最近的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高级僧正的管辖”④。在考虑第二届传教团团长人选时,俄罗斯东正教曾试图派遣主教英诺森·库利奇茨基随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一起赴京,但未得清廷允准⑤。以后派遣修士大司祭任传教团团长成为定例。
从第三届传教团起,俄国圣务院制定了《修士大司祭及其属下职责和行为管理条例》,共十一条,以规范修士大司祭及传教团成员的行为⑥。
第三届传教团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再担任清朝官职。第一届传教团初到北京时,康熙给予每位传教团成员加封官衔: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被封为五品官,修士司祭拉夫连季和修士辅祭菲利蒙被封为七品官,七位教堂辅助人员被封为披甲,并“赏给房子、奴才、俸禄钱粮银以及一切食用等物,随同前来之乌西夫等七人,在娶妻时均赏给银两,于我处俄罗斯庙内念经居住”⑦。并按月给其发放薪水。第二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1728年10月31日在给沙皇彼得二世的报告中,述及第一届传教团成员在京被博格德汗封官和被编入俄罗斯佐领任职的情形,他显然对此表示不满,以为“这在耶稣会士面前很丢我们大俄罗斯人的脸”⑧。第二届传教团因为俄罗斯方面的薪俸常常不能按期送达,同样从清政府那里领取了定期发放的薪水,据1733年5月17日抵达北京的俄罗斯信使彼得罗夫大尉记述:“驻北京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伊万·贝科夫、卢卡·沃耶伊科夫、伊拉里昂·罗索欣、格拉西姆·舒利金及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曾请求蒙古衙门借给他们每人五十两银子,但是遭到了拒绝,而且这种无耻行为受到了申斥,因为他们除领取俄国发给的薪俸外,还由中国国库发给他们——学生和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三两银子,而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则加倍发给。”⑨俄国商务专员郎喀1737年4月离京时曾就各种问题致函理藩院,特别请求“将上述大神父特鲁索夫及其属下两处教堂的神父和教堂差役均置于贵院的庇护之下,最好不与其他衙门打交道。希望不要在这里(北京)赏给他们任何官职,包括俄罗斯佐领内的职位,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惯例,无论是神父,还是其他教堂差役,都不准担任其他官职。”清朝理藩院接受了俄方的这一请求⑩。





二、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
俄国传教团在北京的资产包括:俄罗斯北馆(圣尼古拉教堂,在北京城东北角东直门的胡家圈胡同)、俄罗斯南馆(奉献节教堂,在东交民巷)、墓地(或称罗刹坑,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内东北角,原为东正教圣母堂)、土地(1728—1741年俄罗斯人在北京郊区获取了四块土地,1765年又购买了第五块地)。国内学者除了对教堂加以关注外,其他方面的资产很少提及。



朝鲜使节金景善在其所著《燕辕直指》卷三《留馆录》中的《鄂罗斯馆记》对南馆的形制记载颇详:















三、俄罗斯传教团的北京文献
俄国东正教驻京传教团派出医生、画家、植物学家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与中国互换图书,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这几未被人们所提及。俄罗斯传教团的北京文献代表性作品有:第九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比丘林的《北京志》,第十一届传教团学生科瓦尼科的《北京周围地质概要》(载《矿山杂志》,1838年,第二辑,第2册,第34-59页)、第十三届传教团监督官科瓦列夫斯基的《北京郊区的采煤和中国的黄金开采》、学生赫拉波维茨基的《明朝灭亡时期北京大事记》、学生斯卡奇科夫的《北京运河上的郊区茶馆》(附插图)(载《俄国艺术报》,1958年第35期)、第十四届传教团学生波波夫的《北京的民间传统和迷信故事》(手稿)等。北京文献构成俄国早期汉学的重要内容,故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第二类是传教团成员的游记,这是他们游历北京的真实体验记录。这类作品有:第八届传教团大司祭格里博夫斯基的《修士大司祭C.格里博夫斯基1806年从北京到恰克图之行》,第十届传教团监督官叶戈尔·费多罗维奇·季姆科夫斯基的《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到中国的旅行》(附地图及图片),第十三届传教团监督官科瓦列夫斯基的《中国旅行记》,第十三届传教团司祭茨韦特科夫的《从北京到伊犁》,第十四届传教团随团画家伊戈列夫的《一位俄国画家在北京附近山区的旅行》(载《恰克图快报》,1862年第18期,第4-12页),巴拉第《1870年从北京经满洲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旅途札记》(圣彼得堡,1872年)、《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论哥萨克佩特林中国之行观感》(《俄国考古学会东方分会论丛》1891年第6期,第305-308页)、《1847年和1859年蒙古旅行记》(附贝勒施奈德所绘东部蒙古路线图,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1892年第22期)、《修士大司祭帕拉季评马可波罗的华北之行》(圣彼得堡,1902年,第47页)等。

第三类是传教团成员的工作、研究报告,这是他们从北京向俄罗斯方面发出的信息或情报。这类作品有:第四届传教团卡尔波夫的《北京传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固里给亚洲司的报告》、《十七至十九世纪在中国的俄国教堂和希腊正教教堂》,第六届传教团学生帕雷舍夫等合编的《1772—1782年间大清帝国的秘密行动、计划、事件和变化纪要》(手稿,合著),第八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格里博夫斯基的《关于中国(即清帝国)的报导》,第十届传教团卡缅斯基的《明亡清兴,或叛民李自成生平》、《中国内阁关于处死王子和坤的报告》,第十届传教团列昂季耶夫斯基的《中国阁员简介》(手稿)、《示我周行》(手稿)、《大清(中国)军队概览(一个俄国目击者的记述》(载《北方蜜蜂》1832年第266—267期)、《大清人(中国人)对俄国的看法》(载《北方蜜蜂》1832年第282期),第十三届传教团奥沃多夫的《平定罗刹方略》、《论俄中关系和中国军队中的俄国连》、医生巴济列夫斯基·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来自北京的经济研究消息》(载《内务部杂志》,1852年2月)等。




俄国传教团上述对北京研究的成果,其数量之多、涉及之广、分量之重,几可与同时期在京耶稣会士留下的文献媲美。由于传教团在19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涉足北京以南的城市,故他们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以北京为主要考察点。北京研究文献实际上是他们“北京经验”最重要的文本体现。
四、余论
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俄中交往中扮演主要角色,传教团在北京从事的传教、留学、翻译、研究、外交诸方面的活动亦构成清代中期俄中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俄国传教团除了在前往北京和返回俄国的路途外,其活动的地点就只有北京,其在北京的经历所构成的“北京经验”与他们的“中国经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叠合为一。在俄国与中国的早期相互认识中,俄国方面因传教团的汉学研究成就取得了先机。在语言、文化、历史、地理、天文、植物、医学等方面,传教团均从中国获取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知识,构筑了系统的俄罗斯汉学知识谱系。与西方传教士拥有广阔、丰富的中国游历经验不同,俄罗斯传教团的“中国经验”其实就是“北京经验”,故19世纪中期以前的俄罗斯汉学充满了对中国的溢美之词,这与他们只是接触到北京这一中国文化的精粹有关。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的“北京经验”为其汉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从一开始就听命沙皇,具有为沙俄政府服务的性质,成为沙俄外交政策的工具。从这个意义可以说,传教团实是沙俄向东方扩张时在北京插入的一个楔子。

注释
①(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提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Innocent, Archmandrth.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China.”TheChineseRecorderXL,VII,no.10(October 1916):678-685.

⑤参见(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第78页。有关英诺森·库利奇茨基未能成行,俄罗斯方面还有另外两种解释:一说是因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的诡计,致使英诺森主教身退。参见(俄)尼 ·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0-41页。比丘林的《英诺肯季主教赴华记》认为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对他的态度不好”,参见(俄)Π·E·斯卡奇科夫著、B·C·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第130-131页。一说是“由于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宫廷施以的倾轧,他最终没有得到前往中国的许可。”参见B.谢利瓦诺夫斯基:《东正教会在中国》,香港:中华正教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9页。
⑨(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0页。



































责任编辑梅莉
The Management,Assets and the Beijing Document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s (1716-1859)
Ouyang Zhe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Up until 1860, the Russian Orthodox had sent out 13 missions to Beijing, who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a-Russia exchanges. In order to administer the missions in Beijing, Russia worked out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to regulate and monitor them. The missions in Beijing had churches, houses, graveyard and l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inology studies of the missions is the study of Beijing. They searched for and collected the Beijing related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all of which constituted the important part of “Beijing Experience”. This part has hardly ever been mentioned in the research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Russian Orthodox; Beijing experience; China-Russia cultural exchange
2016-02-20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人士的‘北京经验’研究”(11YJA770040)、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鸦片战争前北京与西方文明研究”(12BZS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