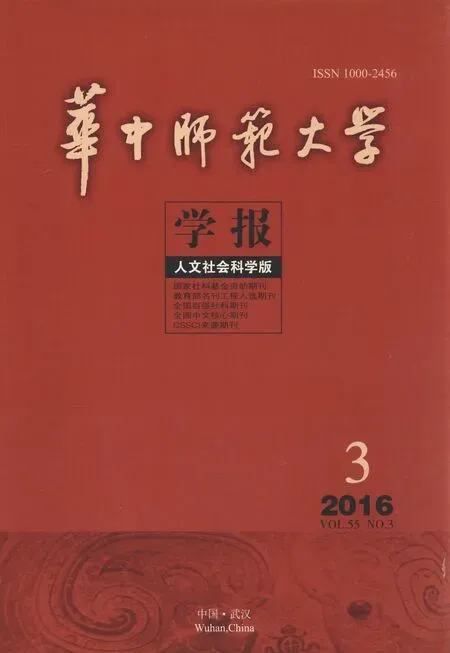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辑佚的学术规范与价值判断
2016-09-08金宏宇
金宏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现代文学辑佚的学术规范与价值判断
金宏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辑佚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古今之间有同有异。现代文学的辑佚往往针对的是“集外”文,即作家自己或他人编有作家的单集或全集,但仍有一些文字散佚在“集外”,辑佚就是收集这些集外文。辑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中“发现的技艺”,存在诸多方法,首先是从判定报刊和佚文的性质入手,其次是追踪线索,还可由笔名而发现佚文,也可通过作品的广告去发现佚文。在发现的喜悦之中,更需要对辑佚的学术规范和价值层面进行“二重批判”,质疑、审思辑佚成果。有价值的辑佚学术实践已转化为一些不同的著述形态,如佚文单集、拼合型佚文集、佚文论等,都将有益于现代文学辑佚学的建构。
现代文学; 辑佚; 学术规范; 价值判断; 著作形态
辑佚往大处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中的一种学术传统,辑佚之业兴于宋而盛于清。往小处说,是指古典文献整理的一种方法,“就是将亡佚图书的存于他书的内容抄录出来,重新编辑成书以恢复或部分恢复亡佚图书面貌的方法”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和治学方法,但是内涵和方法等与古典文献辑佚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20世纪30年代杨霁云为鲁迅作品辑佚开始,现代文学的辑佚工作广泛展开,形成了大量的辑佚成果,为现代文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在辑佚过程中,学者们也各自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文学辑佚经验和技术,只是还缺乏辑佚学层面上的系统总结和整体研究,当然更谈不上从批判思维角度去质疑、追问和审思这些辑佚的成果。这就为本文的展开留下了学术空间。
一、古今异同
古典文献的辑佚是指原书亡佚但又残存于他书,辑佚就是辑出这些散佚文字以恢复原书或部分恢复原书。现代文学的辑佚往往针对的是“集外”文,即作家自己或他人编有作家的单集或全集,但仍有一些文字散佚在“集外”,辑佚就是收集这些集外文。《鲁迅全集》中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这些名称就很能突出现代文学辑佚的特点。古典文献辑佚主要来自于书籍,是“书海寻书”,现代文学的辑佚主要来自报刊,是“刊海寻书”。“包括纯文学刊物、报纸文艺副刊以及也刊载一些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刊物等;如此等等的现代报刊不仅在数量上确实浩如烟海,并且由于缺乏整理和编目……搜求一位作家散佚的诗文,那是不能不令人‘望洋兴叹’的,其难度比诸从‘书海寻书’的古典文献辑佚,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②加上现代作家有更多的笔名,辑佚难度更高。现代文学生产的“先刊后书”顺序决定了现代文学的辑佚也须“先刊后书”,即先必寻之于报刊,现代文学的集外文的渊薮是报刊。报刊不存的,也可寻之他书。现代文学的集外文也还有一部分是未刊稿,包括散佚于他人之手的作家文稿、日记、书信等。如闻一多写于《奇迹》之后的一首诗《凭借》,原稿藏于梁实秋处,梁实秋在1984年出版自己的《看云集》时才把它发表出来。③搜集这类未刊稿也是辑佚。未刊稿中有一部分作家的文稿、日记等为作家本人或遗产继承人所掌控,日后整理披露出来,虽也算作家佚文,但已不是单纯的辑佚性质了,如宋以朗披露出的张爱玲的《小团圆》《少帅》等。
古典文献的辑佚往往具有时代的间隔,即本朝为前朝辑佚。同时辑佚的内容也有时代间隔,如取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以辑周秦古书,取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等等。现代文学的辑佚在同时代就已经开始且作家本人就已参与。鲁迅作品的辑佚开始最早,鲁迅本人就参与了自己的《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的辑佚。同代的辑佚有健在的作家或编辑等亲历者可以求证确认,如杨霁云可以咨询鲁迅本人,唐弢辑鲁迅佚文可以求证于周作人等,甚至严家炎在辑穆时英的佚作《中国行进》时还可以写信求教于穆时英的同学赵家璧。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辑佚有一个人证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期的辑佚比古典文献的辑佚更简单容易。但随着当事人、知情者的作古,现代文学的人证不复存在,辑佚工作的难度加大,辑佚的学术含量也随之增加。所以,今后的现代文学辑佚需要更多地遵从学术规范,更娴熟地掌握辑佚的技术;需要更多的辨析和考证,更深入的审思和批判思维。
不少学者都论及的古典文献辑佚规范也可挪用于现代文学的辑佚,当然也应认识到其间的差异。人们谈到古典文献辑佚书的通病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漏:有遗漏未收的。
滥;不应收而误收了的。其误收之故,一是臆断,二是非本书文而误当作本书文收入。
误:一是不审时代,二是所据是误本,故所收的材料亦有讹误。
陋:一是不审体例,二是不考源流,三是臆定次序。这是指书的编排而言的。④
要避免这些弊病,自然应标举它们的反义,可以举“全”、“真”、“正”等,这些自然也就是现代文学辑佚应遵从的规范。不过,我们还是应据梁启超的辑佚书优劣标准做出更具体的申述。他认为辑佚书优劣标准有四:“(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现代文学佚文可能存于某个选本,但更多是先发表于某个报刊,这不同的出处当然都要注明。有些佚文先后刊于不同报刊,如吴兴华的《现在的祈祷》先刊于北平的《燕京文学》,又刊于台北的《文学杂志》,且有修改。⑤除注明不同出处外,还需要汇校异文,考察源流。这就需要涉及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知识了。“(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求备或求全只能说是一种辑佚的理想境地,实际很难达到,现代文学辑佚尤其如此。辑佚是代代相沿的事业,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辑本相对更完备。最新的作家全集往往收的佚文最多,但“全集不全”始终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悖论。“(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现代文学辑佚的求真,贵在辨伪。需仔细考证,没有直接证据,或只有孤证,不可臆断为真。“(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⑥现代文学中的长篇佚作或可涉及篇第整理问题,一般佚文的复原主要是勘误和校对的问题,此时,须正、误文字同存,不可妄改臆定。梁氏所言,实际上可概括为“求源”、“求流”、“求备”、“求真”、“求原”等,这是现代文学辑佚应遵循的基本规范。能遵从,即可避免“漏”、“滥”、“误”、“陋”之病;能做到,还须借助版本、校勘、辨伪、考据等多种学问。因此,现代文学辑佚绝非梁启超评清儒辑佚所谓“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⑦
二、发现的技艺
辑佚是对佚文的重新发现,这种发现也有其技艺。人们谈古典文献辑佚时,往往把辑佚来源和方法混谈,如梁启超关于宋元以上的辑佚所谈的五条。⑧概括起来讲,古典文献的辑佚来源和方法不外乎利用类书、史书、总集、地志、古书注解、杂纂、杂钞等。现代文学的辑佚主要来源是报刊,凭借日益完善的报刊目录书的指引,可能会发现佚文。当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方法。




四是通过作品的广告去发现佚文。在现代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和现代文学报刊上都曾有大量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的广告,这些文学广告可以为辑佚提供路径和帮助。首先,这些广告文字的发表一般都是匿名的,既不署作家本名,也不署笔名,加上作家本人对这类文字不重视,所以大多沦为佚文,而它们实际也应是作家写作的重要部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叶圣陶、徐志摩、施蛰存、胡风等都写过大量的文学广告,但都很少编入文集或全集。相对最全的新版《鲁迅全集》(2005版)也仅收鲁迅的广告文字四十余则,肯定还有许多佚于集外。其他作家的广告文字入集情况更不理想。有时候作家的署名文字一旦沦为广告也可能成为佚文。如1930年代赵家璧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曾邀参加编选的11位作家(包括蔡元培)各自撰写了《编选感想》,这些文字以手迹影印的形式发表于“大系”样本和单张宣传广告上,40多年后才被作为佚文发现。至今,只有《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知堂书话》等收入了他们各自的《编选感想》,其他作家的《编选感想》依然佚于其作品集外。可见,现代文学的广告已经成为辑佚的一块有待开发的重要园地。其次,现代文学广告能为现代文学佚文的发掘整理提供线索。查阅书目工具书是现代文学辑佚的途径之一,而现代文学广告中最简洁的一种正是书目式广告。这类广告在辑佚时是现代文学书目工具书的很好补充,有时候书目工具书未录的书目恰好可在这类书目广告中找到。因此,研究现代文学丛书的学者常常就依靠这种方法补全散佚的丛书目录,为进一步辑佚提供帮助。如《良友文学丛书》出版到第20种时曾在《良友》画报等报刊登出该丛书后20种的书目广告,其中就有穆时英的《中国行进》,这也为该作的存在提供了一条证据。现代文学广告中的短文式广告对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辑佚更有价值,因为它们往往会对作品的内容或形式特点有更具体的宣传。如1929年7月出版的《华严》月刊第1卷第7期上刊登的于赓虞诗集《落花梦》的广告:“《落花梦》是一部用尽心力的所谓‘方块诗’,在一种体制下的五十首诗,作完后整整修饰了三年有余,所谓‘方块诗’之功罪当于此集表现净尽也。”此诗集目前还没找到已出版的版本实物,辑佚者正是依据此广告提供的篇数、体制进行了重辑,并收入《于赓虞诗文辑存》中。这类短文式广告中有许多就是摘自一些同时代作家已写的现成文章,这时广告会为原文的辑佚提供线索。如《新月》杂志1卷12号刊有凌叔华《花之寺》的广告,广告上标明“节录徐志摩本书序文”,说明徐志摩曾为《花之寺》作过序。这则广告保存了徐志摩序文的片段,也为这篇佚文的寻找提供了依据。当然现代文学广告中也有一些只是关于作品的预告,只是预告了作家计划写但实际上未写出的作品。如《良友文学丛书》书目广告中曾预告了郭源新(郑振铎)的《子履先生及其门徒们》、施蛰存的《销金窟》、郁达夫的《漏巷春秋》等几部长篇小说,但最终只是广告虚名。这类广告又可能成为辑佚的信息干扰。
三、二重批判
现代文学作品的辑佚必是在熟知作家作品入集情况并进行了大量阅读、查找的基础上完成的,在经历大量的阅读劳动后发现佚文,发现者必会沉浸于发现的喜悦之中,但此时更需要的却是理智的审思并进而展开学术的批判。这种批判应该是两个层面上的,一是辑佚的学术规范层面,一是辑佚的价值层面,可称之为二重批判。





从文学经典化的角度看,辑佚当是一种反经典化的学术行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当然是一项复杂的文化工程,但一般来说,常态的文学经典化遵循的都是文学价值上的汰选原则,即按照思想性和文学性统一的标准精选出相对更具有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而淘汰掉肤芜之作。作家自己编单集时就是首次经典化,他首次从发表于报刊的大量作品中汰选出一批作品编入某个单集。日后的各类选本如《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又反复汰选,都是经典化的动态过程。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将使一部分作品散佚,尤其是作家自己的首次汰选遗弃的大量作品都可能成为佚作。如郭沫若编《女神》集只收诗歌56首,遗弃此前诗歌52首。鲁迅编《野草》集,未收早期《自言自语》7篇。这些作品都可能成为佚作。经典化所遗弃的正是辑佚时要收拾的,故此,辑佚是与文学经典化悖反的学术活动。现代文学的大趋势是走向经典化,但辑佚可以成为为经典化纠偏的手段之一,它也许能使经典化避免遗珠之憾,还可能从肤芜之作中打捞出现代文学的一些吉光片羽,更具有一种还历史原貌的价值功能。
从史料学角度看,辑佚是搜求文学史史料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它最终是服务于文学史的完整叙述。辑佚似乎是为了完备地搜求作家之文:作家编单集时是在编选本,一些作品会被遗弃而成为佚文;他人编作家全集时会搜求这些佚作而列于其单集之旁的“集外”;其后,辑佚者又在对“全集不全”的质疑中继续辑佚。但作家之文的求全其实是为了作家个人文学史料的完备。对作家研究来说,所辑出的佚文也许不是他的重要作品,却可能是关于他的重要史料,让我们能看清作家的成长过程和写作全貌。从作家的少作或习作中可以确定其创作起点,看到作家文学才情的萌芽状态,如辑佚者发现的张爱玲中学习作。从一些佚作中,又能看到作家的各种艺术尝试和突破,如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中的新诗形式试验,穆时英的长篇小说写作操练。从某些遗弃文中,又能看到作家陷入歧途,如新中国成立后批判运动中的文字。对作品研究来说,佚文的发现,可以让我们理清作品之间的某些历史关联。如穆时英《中国行进》与其他短篇之间的重合、缩写或从属关系。鲁迅佚文《自言自语》的重现不仅能让我们能看到其中的某些篇章与鲁迅后来的某些作品之间的内容、情节等的相似关联(如《古城》与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的父亲》与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等),而且能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出这组作品其实就是《野草》这部经典散文诗集的艺术形式的先行试验。总之,辑佚有助于作家及其写作的相对多面的、完整的历史叙述,并进而丰富、调整乃至重写整个现代文学史。由此,可以确知佚文的重要性和史料或历史价值。


四、著述形态

一是佚文单集:即把作家的集外佚作单独编为一集,有的干脆取“集外集”的集名。如杨霁云所编《集外集》(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5月版),收鲁迅1935年以前未收入集子的诗文。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10月版、1952年3月版),收1938年复社版《鲁迅全集》所漏收的部分佚作。其他有曾广灿等编《老舍小说集外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3月版)、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编《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冯光廉等编《臧克家集外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陈子善编的张爱玲佚文集《沉香》(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9月版)、王炳根编的冰心佚文集《我自己走过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陈学勇编的凌叔华佚文集《中国儿女》(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等。这些佚文单集一般都会按时间顺序编排或作一些分类,有的甚至做了一些增加史料性的处理。如《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对所辑序跋中的人和事尽可能都做了简要注释,并在书后附上《〈郭沫若文集〉序跋目录》,让读者可以检视郭沫若序跋的整体情况。这些佚文单集一般应该是辑佚者精心搜集、排除疑似、考证确凿的结果,但往往只留一些简单的证据信息,如标明佚文刊发时间、所出自的书或刊物名称及作者署名等。有时辑佚者也会在自己的序跋文字中对佚文作一些简单的价值说明,一般都无法呈现更多的证据和考证过程,更无法充分阐发每篇佚文的文史价值。只有少数的佚文单集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如李存光编著的无名氏长篇小说佚作《荒漠里的人》(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月版)。辑佚者对佚作误植作了校勘又保留原文字,保留了佚作原注又加了新注,提供了照片、书影、刊影、广告、附录作品等大量证据,还有编辑凡例说明、文本整理说明,更有作为“前言”的长篇考辨文章对佚作的标题、章节、写作过程等的辨析及佚作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深入阐发。这是一部真正体现现代文学辑佚规范和“二重批判”精神的佚文单集。

三是佚文论:主要是指对佚文的考与论,可以是论文或论文结集的著作,通常会附录佚文或将佚文嵌入论文之中。陈子善发表过大量的佚文论,在他的《文人事》等书话著作中收入不少这类论文,涉及周作人、胡适、郁达夫、茅盾、梁实秋、戴望舒、张爱玲等众多现代作家的佚文。他的论文一般篇幅短小,偏重于“考”,即考证佚文的出处、真伪等。而结集为佚文论专书的有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刘涛的《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等。他们的佚文论别具一格,其实是一种混合型的研究,对所附录的佚文有校和注,然后又以札记形式解读佚文文本的思想性、文学性、文学史意义等,重点不在“考”,而是偏于佚文价值阐发的“论”。而考、论相结合的是孙玉石、方锡德的论文。它们论据充分、考证细密,同时持论公允、阐发得体,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论的正宗和典范。

注释
①④安作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3页,第406页。
②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③陈子善:《捞针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58页。
⑤解志熙:《考文叙事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4页。


⑩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雪松
On the 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cademic Discipline and Value Assessments
Jin Hong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s an academic tradition,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ollection. There are many methods that can be adopted in the document finding and editing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ith the joy of finding, it is quite necessary for the modern collection to form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value assessments.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collec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some different forms of writing,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on as a branch of modern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collection; academic discipline; value assessments; form of books
2016-03-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文学史料批判学研究”(13BZW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