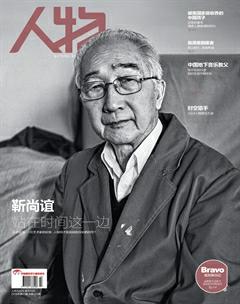故事与蝗虫
2016-09-07张瑞
资深记者 张瑞
故事与蝗虫
资深记者 张瑞

178年前,一位年轻的县官苦口婆心地晓谕他的乡民捕捉蝗虫的方法:用牛皮截作鞋底式样,或者直接将旧鞋底钉在木棍上,蹲伏于地,啪啪啪;挖三四尺深、丈余长的坑,200人,10人一队,手握长帚,四面围定,如战阵行军,步步为营,将蝗虫撵进坑中,推入浮土,捶打压实,活埋了事;埋在土里的蝗子,则由乡民翻土搜捕,官府量秤而沽,一升给钱一百文,若捉的是已经成形可以跳跃的,考虑到捉捕难度,一升还可以多给二十文。
年轻的县官,十年寒窗一朝及第,这是他的第一份差事,他的焦躁显而易见:“倘若乡地人等,挖捕不力……将村民一并严行枷责示众,绝不姑宽。”
这是故纸堆中的人和事,谈不上有趣,吸引我的,是一种陌生感:牛皮掌的扑击,装蝗子换钱的竹筐,古怪又决绝的捕蝗大阵,偷懒就要戴枷的乡民,还有烦闷的县官,都是未曾知晓的、消失掉了的东西,是不大可能重现的生命经验,曾发生的越真切,就越陌生。而“消失”,并没有增加它们的价值,只是让故事变得无足轻重。
一个时代只关心一个时代的故事,县官是怎么殚精竭虑想出捕蝗大阵的?四野乡民将怀着怎样的心绪看待被示众的父母亲戚?大概都是好故事吧,可惜的是,如果长篇大论,就有些不合时宜。作为一本本质上是讲故事的杂志(因为人是故事的集合体)和一个以写故事换生活的人,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反映时代。
常常,会被问到,为什么想记录这个故事呢?
我总会字斟句酌,语气轻微,“大概……能反映些时代?”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故事有多重要,而是有点心虚,非如此,也找不到故事被记下的理由。天底下,最不缺的,大概就是故事吧。哪个时代没有千万本书的旧迹,哪个人又没有一肚子故事呢?爱恨情仇魑魅魍魉,又或者最深奥最古怪的真理,当下的故事已足够讲述无数回,真不必求助于旧时代的人事。在我短暂的记者生涯中,在我记录下每一个故事时,大概总能想见它们变得“不合时宜”的一天。就好像县官在年老之后写下一生的志业,流之后世,但后世故事已经太多太多。我们搜集、挑选、讲述它们,而且,还要求是好的:有趣、曲折、动人。我们费尽心思,很难说没有势利的成分:忽略大部分,选择一小点。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样的主题,我们也能够找到千百个可以承载的故事,但我们只选择那些“好”的。而所有时代的故事,结局其实总不会太好,就像蝗虫随风起,平原落惊雷。
还可以谈谈蝗虫。一个故事吃掉另一个,故事也是蝗虫。我们,就像拿着牛皮掌的乡民,偶尔偷懒也轻车熟路,“啪”,就到手一只故事的蝗虫。
但蝗虫飞过去就飞过去了,这些破坏性的嗡嗡作响的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
所以,为什么还要费力记述故事?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人——除我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东西?既然故事,英语里的“storytelling”,既势利又转瞬即逝。
两个月前,写过几个工读学校的孩子,偷盗、劫掠又或者杀人,他们的脸面模糊故事清晰。一个人的生命力体现在破坏上,是好是坏,大概也是运气的问题。管理者就三番两次地和我感慨,若是战争年代,这些孩子都了不得……这样的讲述让我着迷,倒不在于这种无趣的可能性,而是隐含其间的一种时间上的间离感——这样的故事大概总是一次次发生过的,但那些故事,和故事里,偷盗、劫掠又或者杀人的孩子,却已经隐没无闻了。我想,这也是眼下这些孩子的命运。
这些孩子,将被蝗虫吃掉了,我想,我感到沮丧又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