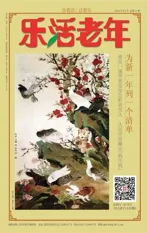锦书
2016-09-03舒容
文/舒容
锦书
文/舒容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是宋代才女李清照的词句。香闺寂寂,执一紫毫笔,把心事写在锦书——彩色的信纸上,或偷偷读着心上人寄来的锦书,这是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女子的日常剪影吧?
东汉之前,男人们是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写在竹简上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新鲜的竹简,刮去青色的竹皮,叫“杀青”,竹简刻字,不住冒汗。以后书籍出现了,依旧叫“汗青”。据说东方朔写给汉武帝的一封信用了3000块竹简,由两个大汉送信,汉武帝看了两个月才看完。写信的、送信的、看信的和竹简都冒汗。
锦书却不一样。说起锦书,不能不提到薛涛,她是唐代人,生于长安,自幼随做官的父亲住在成都。由于家道中落,这个容貌姣好、文才出众的女子不幸沦落风尘。她一生作诗500多首,多已失传,《全唐诗》中仅收录89首。让她流芳百世的,除了诗,还有她造的纸。她以芙蓉树皮为原料,用成都百花潭水研和纸浆,再撷取芙蓉花绞汁,制成淡粉色的纸笺,时称“芙蓉笺”或“薛涛笺”。至今,成都的望江楼公园还有薛涛井等遗存。
不知是不是薛涛带动的,唐代盛行彩色的笺纸,深红、浅红、栀黄、水碧、绛紫……各色笺纸装于锦匣中。明代以后,自制笺纸成为风尚。到了民国,笺纸不但带颜色,还画着画,作底纹。民国文化名人,多自制笺纸。女画家周炼霞自制的彩笺,标有庐陵周氏字样,和她的小诗“一灯细煮愁如酒,化作红笺小字诗”一起流传开来。
凡写写画画的人,没有不爱彩笺的,冷峻如鲁迅也不例外。他留下多篇关于彩笺的文字,还和郑振铎合辑《十竹斋笺谱》。还有人爱收藏原笺,如郑逸梅,千辛万苦地收集,夹在自制的白纸中,攒了四五大册。
可惜这样的雅事都止于民国了。彩笺、锦书,都如汗青一样,成为历史深处的一个词。笺纸不再被使用,而是成了珍贵的收藏。近读周有光的著作,写到“最后的闺秀”张允和,她86岁时学会电脑打字,不但不用彩笺,连白纸也不用了。有电话,有微信,十分便捷,谁还写锦书呢。可是为什么想起锦书,我们会有淡淡的惆怅与不舍?
锦书难觅,觅不到的,还有文房四宝的另三宝——笔、墨、砚。《牡丹亭》里,小姐唤丫头:“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那派头,放到现在就是个大书法家。古代读书人,无不有文房四宝。现在的人,即便学历很高,拥有自己的书房,好多人却已不知文房四宝为何物,更不知道古人的书房里,除了文房四宝,还有许多小玩意儿——金石、古董、笔筒、臂搁、扇子……古人用这些营造一种书房的氛围,一种闲而有趣、平正淡泊的文人情趣。
《文房漫录》的编者说到编书的初衷,他引用电影《饮食男女》里面“老朱”的话,说现在“人心粗了,吃得再精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他找些有趣的事,让衣食无忧的现代文化人心细起来,有意思起来。
《文房漫录》共收文47篇,作者都是大家,他们收藏的东西好,写的文字也好。比如梁实秋,他在写笔的文章中说,不但他的父亲有极品的毛笔,他岳父家还开着北平著名的笔店“程五峰斋”,他写起笔来自然言之有物。周作人收藏了许多墨,
100年前的就有8
锭,还谦虚说自己“买墨是压根儿不足道的”。张中行喜欢集砚,集了许多歙砚。“顾二娘”是清康熙年间有名的砚工,张中行不但考据了顾二娘其人、其砚,甚至去顾二娘的家乡苏州时,还去了故居寻访,他写出的《顾二娘》《歙砚与闲情》才那么好看。从这些大家的文字里,我们了解了文房四宝的来历,知道古人的墨,加了麝香、珍珠等原料,真的是香的,而不是像现在的墨汁,是臭的;我们甚至“看到”了千百年来古圣先贤流连书房,怡然自乐的情景……
文人收藏并非单纯爱物。老物件是沾了前人手泽,有生命的。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说,他爱砚,是因为从中可以体会古人书写的情景。马未都在谈到他的“臂搁”(古人书写时枕臂之物)时说:“古人会把一些名言警
句刻在上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臂搁上写的是:不到极逆之境,不知和顺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善……古人写得多好啊。”他把它们置于书桌上,时不时看一眼。赵珩说:“静静的书斋,案头杂陈精致的文具,虽置身于喧嚣的红尘中,总多少能保持着一点平静和悠闲的心境罢。”黄裳说:“细想起来,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还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而人类的文化生活就是大半因此而积累形成的。”
现在的人,想收藏一张彩笺、一锭清朝的墨,已十分不易了。但读着与文房有关的文字,想着古人的心事曾经用散发着墨香的锦书承载着,不也是个极好的享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