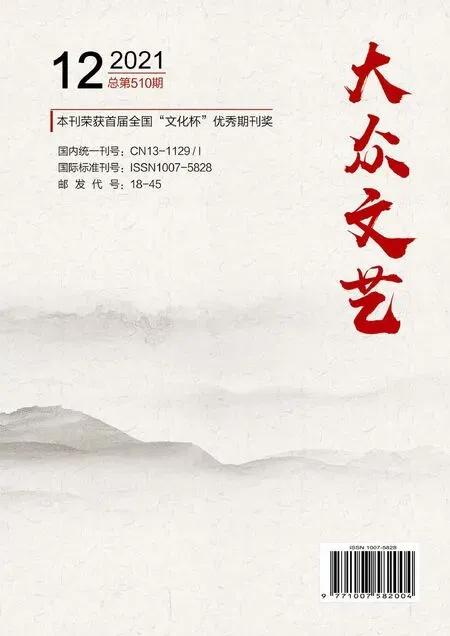现代与传统的“美丽”诠释
——解析室内乐作品《花夜》
2016-09-03梁奕飞四川音乐学院作曲技术研究中心610021
梁奕飞 (四川音乐学院 作曲技术研究中心 610021)
现代与传统的“美丽”诠释
——解析室内乐作品《花夜》
梁奕飞 (四川音乐学院 作曲技术研究中心 610021)
室内乐作品《花夜》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杨晓忠先生在2001年创作的。获文化部第十一届全国音乐作品(合唱、室内乐)评奖室内乐作品作品奖。入选新西兰威灵顿2007亚太地区音乐节(ASIA Pacific Festival 2007 Wellington New Zealand)。2009年作品出版于《亚太音乐节优秀作品汇编》。本文试图揭示作曲家是如何合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结合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来表现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方神韵。
杨晓忠;《花夜》;时序性结构;音色音响;民族民间音乐
室内乐作品《花夜》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杨晓忠先生在2001年创作的。“花夜”一词,来源于羌族婚礼习俗。婚礼前晚,新娘邀集姑娘们到家中守夜,唱“花儿纳吉”“盘歌”“格妹呦呀”等婚礼歌。它——被称为“花夜”。作曲家被“花夜”散发出的浓郁的民族气息和人文魅力所感染,用写意的手法营造出羌寨夜晚宁静而神秘的气氛;用朴实无华的歌调倾诉了新娘对父母的眷恋,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作品灵感来源于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羌族婚礼仪式,以“花夜”为切入点,融合作曲家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现代室内乐写作技术,使作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既彰显羌族音乐的独特元素,又使其富有新的内涵,让人耳目一新。
进入20世纪,音乐的发展速度已远远快于过去几百年,通过前人的研究和整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进行创作。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运用这一理论体系创作出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音乐,走出一条不同于前辈的,我们自己的创作之路。《花夜》作为21世纪的新作品,创作技法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作品,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这部作品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标准的乐段式结构,作曲家在大事件背景下,将所有的形式与内容细微化。本文将通过对《花夜》这部作品的分析与研究,试图阐述作曲家是怎样运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结合现代作曲技法,来表达和传承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情感烙印。
一、时序性的结构
这部作品采用时序性的结构,作曲家通过对“花夜”这一羌族特有的婚礼习俗的描述,作品由花夜前(陈述性)——花夜中(延伸)——花夜后(尾声)三个段落构成,即具有时序性的结构特点。不管从小的短句的处理,还是三个大的段落的处理,都充分的融入了其三部性的特点。
如作品开始处的第一个短句(1—5小节)就具有三部性的特征。先由中提琴和小提琴的中低音区拨奏开始,经过两小节弦乐三连音与八分音符的扫弦,最后回到弦乐拨奏。这种从静态——动态——静态的形式中,看出其三部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收束乐句的特点。其实也是全曲结构的一个缩影。
在第二部分(35—64小节)开始处的短句(35—39小节),同样的也具有三部性的特征。从中看出,中提琴的震音之后,小提琴揉弦再回到震音,这也是三部性的收束乐句。但是除这一特点外,较之1—5小节中八分音符扫弦的部分做了更多的延伸,形成了具有非对称短句的特点。
以上几例作曲家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方整性收束乐段、乐句(2+1+1或2+2+4)等,而是运用了非均衡的手法,让B的部分尽可能的延伸,打破其方整性。如作品中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落(1—17小节)的处理,虽是三部性,但其内部却是非对称的结构,即采用了(4+11+2)的结构,其中中间部分具有开放的性质,使其更为张力和表现力。虽然作曲家在这部作品的短句,段落中运用了三部的收束性结构,但作品并没有失去其推动力。相反的,作曲家依靠短句,段落内部大量的延伸和密度的增加,采用非对称的发展手法在三部性的收束结构中寻求音乐的流动性和推动力与作品的延展。
在最后一部分(65—80小节)的处理上,作曲家采用了所有乐器回归最常态的演奏技法来演奏一段类似民歌的曲调,前面所有出现的音高材料都可以在最后一段中找到原形。我们也能看到从前两部分非均衡的短句、段落到这里的方整性乐句、乐段,从非传统的演奏到中性的、常态的演奏无不体现了一种结论性的推导式尾声方式。
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运用时序性结构将羌族婚礼仪式的进程表现的淋漓尽致,材料运用的非常精简而有张力,不仅体现了作曲家对音乐材料的掌控能力以及使用高度统一音乐材料的能力,还体现出作曲家对整部作品结构的把握和创新意识。
二、音响延伸的途径——音色
音色就像画家手中的调色板,画家用五彩缤纷的颜色美化作品,同样作曲家用多样的音色来“装饰”作品,成为音响延伸的途径。在这部作品中音色、音响的处理显示了作曲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作曲技法与创作灵气。作曲家根据作品背景中需要的意境,对弦乐的演奏法进行了研究,使用了多样的特殊演奏技法,让音响在音色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得到延伸,推动全曲的发展。它们也是构成了其独特音响的基本音乐元素。
1.多样的音色
左手拨弦(ad lib+),这种拨弦的音响效果相对于常规的拨弦(pizz)显得清脆、紧凑。作品一开始便用了两种不同的拨弦,作曲家恰好利用了左右手拨弦的差异性描述了一种延绵与清脆,混沌与淳朴的对比,准确的表达了“花夜”前新娘矛盾的心理和羌寨静溢的夜晚。
“楠溪没有白米饭,只有番薯丝救条命。”“月里底(坐月子)吃蕃菇种——命逼倒。”说明浙南人生存条件的窘迫。
用指甲揉弦(N),演奏者用指甲揉弦是像在模仿中国传统乐器古琴揉弦的那种纯净,清晰的音色。
甚至在连接(插句)的部分(27—28小节),作曲家运用手指虚按琴弦的泛音滑奏来表现一种模糊的试图寻找某种东西的意境。
这部分与之前的拨奏、扫弦和之后的震音段落并不切合,但似乎又有着某种联系,其实作曲家也正是运用这样的插部,和听众一起努力的寻找着一个音调,从幻想到现实的音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曲家融入了幻想的音调——寻找音调——听到现实的音调,这一符合全曲三部性结构的特点。
全曲第二部分新的音色出现,弦乐揉弦对哭腔的模仿,作曲家非常形象的描述了守夜时新娘的复杂心情——悲伤和喜悦交织。
作曲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使西洋乐器模仿演奏中国乐器所独有的音色,这也正是作曲家深厚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的流露,也能看出作曲家对音色的独特见解。
2.音色序
这些音色的变化其实都是辅助音响一步步得到延伸和推进的手法。在这部作品中音色其实也呼应了全曲结构的时序性特点。

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音色在作品中由繁到简的变化过程,最终回归到最常态的音乐形象。音色在其中起到了延伸的作用。
再例如,作品第一部分开始处弦乐出现的拨弦和泛音(1-5小节和27-28小节)到第二部分结尾处又出现了与其音色不同的拨弦和泛音(59-64小节),作曲家通过这样的变化方式让音色成块的,具有了时序性的特点。
3.音色的过渡
这部作品中音色作为音响延伸的途径,在段落间也起到了过渡的作用。例如第一部分的(25—34小节)长笛声部花舌,连续运用上行,弦乐声部保持着双音的节奏性拉奏将全曲推到一个高点。
其实这部分就是为第二部分的弦乐震音音色做了铺垫,起到了过渡的作用。
又如作品第二部分长笛声部(59—64小节),也是通过几个长线条的下行运动,弦乐声部通过拨奏和泛音,逐步的将全曲从高潮退下。
这部分是向最后一部分中性的,常态音响的一个过渡,既有之前音色的出现又为后面的音响作了铺垫。还有作品中的插部的音色(27-28小节),作曲家在插部做了最后一部分音响的隐伏,其实也是一种先现。
上面两个例子中作曲家将基本音响材料大二度,纯五度横向的运用在长笛声部,并且在不同的部分用了不同的音色,起了不同的作用。这种类似于旋律线的运用也使其具有过渡连接性并赋予推动力。
作曲家不断地寻求变化,从而使其在音响上具有新鲜感和推动力。这充分显示出作曲家高超的创作手法。在这部作品中,只是采用了羌族音乐中的特性音响,就将整部作品带入“花夜”的氛围中,准确而恰当。虽然这部作品运用了不少有特性的音色,但是整部作品并没有觉得凌乱与不协和,相反的,它不仅让听众在西洋乐器演奏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并赋予其新的涵义,也使音响不断的推进延伸,音乐也有了极强的推动力。作曲家用独特的创作技法诠释了对音色、音响的理解,既不拘泥于现代,又跳出了传统的束缚。
三、羌族音乐的独特运用方式
近现代作品中,作曲家常在作品中融入自己本国,本民族的具有地域性特色的音乐,来寻求一条自我表达的方向。《花夜》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方作曲技法完美结合并赋予其新的意义的作品。作曲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羌族音乐元素巧妙的融入作品。
该部作品本身并没有一味的,直接的运用羌族民间音调,而是先将其做了归纳——整理——提取精髓的过程,然后再运用于作品中。
羌族音乐中所用的音阶以五声、六声为主,如①la、si、do、re、mi、sol、la或②la、do、re、mi、fa、sol、la。该作品中作曲家除了提取羌族音乐中最具特征的纯五度,大二度作为该作品的基本材料,还运用了音阶中小二度这一特性音程。(8-9小节中的弦乐声部和33、42小节的小提琴声部)
虽然材料简单,但通过音色、节奏、音材料的不断变化,丰富的音响,作品的意境也被完美的勾画了出来。
还有,羌族特有的民间乐器羌笛的曲调中仍然出了小二度音程(见谱例1)
谱例1:
上例羌笛曲调徐缓悠长,没有划分明显的乐句的特点,也正是全曲气息的体现,如长笛声部运用的大量长气息的句子(见25-34小节和59-64小节),也是没有明显的段落划分,在一个较长的,甚至延绵不绝的气息下,让作品延伸出去。
作品最后一部分所出现的这段最常态的音调(见65-80小节),也并不是羌族某个民歌的照搬或缩影,而是作曲家通过长期对羌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与积累而自然流露出的心中对“花夜”这一婚礼习俗的淳朴感受。虽然从旋律还是音色、音响都回归到最原始,淳朴的中性状态,但是作品却在这一部分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升华。往往最淳朴,简单的东西,最能打动听众,作曲家将这部分放在全曲的最后出现,既起到了承前的作用,又使整部作品完美的在中国传统音乐语言中得到最好的升华。作曲家并不拘泥于音调本身,而是注重于怎样将作品内涵准确的表达出来。从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出杨晓忠先生所特有的中国文化底蕴,和极深的写作功底。也从中懂得了要将民族音乐特点化为具体的艺术表现技法,若只是在占有民族民间音乐资料,收集民族民间形式的阶段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努力掌握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规律、深入理解民族音乐的精神实质,从民族性格和审美观念的角度去领会我们民族音乐真正优异和独到之处,这样才能自如而准确的进行表现技法的创新。
四、结语
杨晓忠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国内外作曲界的一位作曲家,他在创作中把精力转向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注重理论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关系,寻求中国音乐元素与西方音乐美学观和创作观念的融合。他运用自己独有的对作品结构和音色音响的掌控和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刻领悟;带着探寻多元文化交汇的通道,创建不同风格融合的有机单元的创作理念而创作出来的很多作品都获得了国内外的好评。2008年10月杨晓忠先生的作品《拂尘Ⅱ》根据道教里的一件法器——拂尘而创作。获得了由卢森堡现代音乐协会举办的“2008第七届卢森堡国际作曲比赛【International Composition Prize—Luxembourg 2008(7th)】的第四名。这是即《花夜》后又一成功的作品。
作品《花夜》的创作是成功的,不论从独特的音乐表现手法还是细腻、精致的创作技巧上都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典范。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显示了作曲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花夜》这部作品正是在中国现代音乐寻求创新时,对于“中国现代音乐”最好的诠释。音乐在前,创新为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我们并不需要过于华丽的音调,质朴的旋律才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既不是其传统音乐的精髓,又展现出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上的突破。既不弘扬了几千年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伟大,又促进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可谓是中国现代室内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和前瞻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