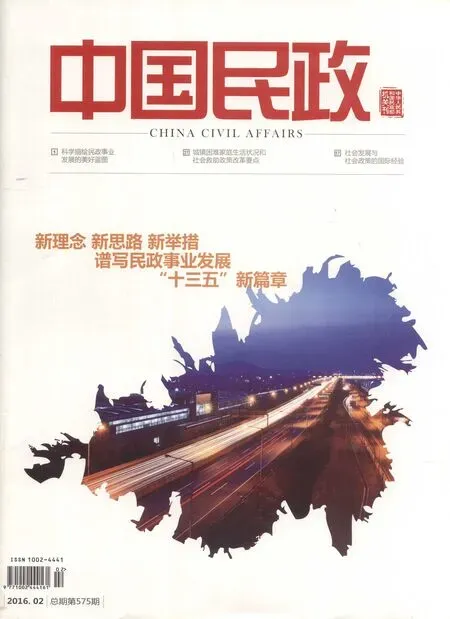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国际经验
2016-08-31周超,汪广龙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国际经验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是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放眼世界,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已经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多样化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模式、遭遇的问题以及改革举措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欧美社会政策的困境与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率下降、性别角色及家庭结构的改变、收入不平等、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背景推动了欧洲福利国家的深刻转型。欧洲社会福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应对社会政策的财政可行性问题,改革可分为4个阶段:从早期直接的福利削减政策到以妥协和协商为基础的改革;9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投资”“积极福利国家”等概念下转向基于就业最大化的改革策略;2000年后更多采取以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二元区分为基础的举措(Giuliano Bonoli,2014)。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欧洲大陆模式、欧洲南部地中海模式、英国-爱尔兰模式以及中欧和东欧欧盟新成员国模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社会保障”和“社会推广”是作为改革主要举措的社会投资的两大支柱,主要包括增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支出;增加双职工家庭需要的各类服务的支出比例;融资来源从社会贡献转为财政融资;社会保障与社会投资功能产生“制度互补性”(Anton Hemerijck,2014)。
虽然美国的社会政策面临与欧洲相同的挑战,但美国的福利改革延续了“工作导向”的原则,要求个体重拾责任并实现自我支持;强化了福利领受者的工作激励并为低收入者在私人市场中购买个人所需的福利产品提供支持;在社会福利的民营化中,公共部门辅助私营部门实现福利融资与服务传递(Neil Gilbert,2014)。

东亚社会政策的历史与趋势
东亚福利模式是“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Esping-Andersen,1990)之外最为经典的范式。作为“生产型福利国家”的东亚模式强调社会政策必须为经济增长服务。但东亚模式当前不仅面临老龄化、低生育率等与欧美相似的问题,还面临竞争政治、民众参与扩大等独有的问题。
东亚社会政策模式的历史变革。战后日本建立了一个大量依赖公司和家庭来提供收入、救助和照顾的社会保护体系。但老龄化、低生育率及女性职业化带来了家庭模式的变化,家庭之外的照顾服务需求增长;加上经济减缓带来的财政恶化,传统政策亟需变革。渡边雅男认为,未来的改革应走出国家主义、家庭主义或市场主义的传统道路,更多仰仗市民行动和社会网络的作用。香港地区将经济作为主要福利引擎并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唯一最重要的福利目标,一直沿用残补式或补救式福利模式,在退休、医疗或失业方面没有任何强制性、公共资助的社会保险项目,而是在公共住房等社会服务方面给予了大量资助。为应对经济转变、人口变迁和劳工市场结构变化加剧的两极分化,政府近年推出了诸多项目以增加就业机会并帮助失业民众获取工作(梁祖彬,2014)。而韩国政治变迁的诸多背景因素对韩国的社会政策有决定性影响。威权时期的政府为了取得政府合法性会推动有限的社会福利计划,而民选时期的政党为赢得竞选都有意维持和扩展福利国家体系。韩国这种亲福利保守模式与其他东亚地区明显不同(Christian Aspalter,2014)。
当前东亚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当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策都面临的挑战,既有特殊性同时也有共同性。台湾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变化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1945—1980年代福利侍从主义,政府主要为能巩固国内合法性的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群体提供福利;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抗争、民主化、选举政治强化了自由包容的社会福利政策;2000—2008年是调整与完善阶段,这个时期台湾的民主政治趋于稳定,社会福利政策更加现实;2008—2011年财政困境加重。台湾当前面临的困境包括财政危机引发的政策可持续性,福利侍从主义导致的公平问题以及选举政治的负面影响(祁冬涛,2014)。
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路径
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路径,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防止意识形态争论、体制僵化和推进改革的重要前提,也是防止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前提(郑永年,2014;孙立平等,2012),着重表现为4个方面。
在更广泛的层面推进社会政策改革。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社会政策在欧美和东亚等国家有着不同的模式,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和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政策,带来社会不公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近年,国家试图引入社会政策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郑永年认为,未来社会政策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要扩大中产阶级,以保障转型的平稳过渡。具体着眼点包括:将国家资助的特权和特殊利益转换成各种形式的普遍共享的权利;调整公务员以及垄断行业与国有企业雇员所享有的特殊福利待遇;财政方面要增加中央责任,纳入更加透明和民主的预算过程。
重视文化发展战略。中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战略应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是挖掘文明间共性,介绍中华文明的特性,强化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跨文明对话,推动良性互动,消解误解、隔阂和历史敌意。其二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传统、族群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学习,挖掘中华民族各群体在几千年交往中交融共享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加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格局(马戎,2014)。
抓住政策改革的关键部分。改革需要包括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在内的政策结构整体调整,具体包括从党政关系、央地关系方面改革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体制,同时从约束公权力、壮大社会力量、回归市场本位3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周超,2014)。改革要抓住关键,不能贪大求全,政府在未来的改革中应运用直接的现金支付和所得税或者间接通过向穷人提供物品和服务来减少不平等(Åke Blomqvist,2014)。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模式在推动公共参与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有关预算的制度、启动人大制度,“民主恳谈”框架之下的对话制度和公共参与,参与式预算让国家与社会之间学会用制度化的办法解决冲突(李凡,2014);而信任度、对医疗体制的满意度、加入传统社会组织、社会规范等变量对公众的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因此,要重视改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机构,为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仰提供更多空间(单伟,2014)。
“把激励搞对”。作为推动中国改革核心现象的地方创新,是探讨中国社会政策改革路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影响地方创新的变量包括地区的社会紧张程度、富裕与贫困程度、经济—社会规模状况、城乡状况、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其中晋升制度是核心,“把激励搞对”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Joseph Fewsmith,2014;钱颖一,2008)。未来应改革以纵向问责为核心的问责制度,更少地强调经济增长,更多地注重社会服务,加大横向问责力度,公开更多信息(如预算),扩展公推直选制度,核心是必须重视打造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官僚体系(Joseph Fewsmith)。
(周超 汪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