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存在”的杨义先生
2016-08-30李思清
文 李思清
作为“学术存在”的杨义先生
文李思清

杨义先生与杜德桥先生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谈(李思清/摄)
在一场澳门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朱寿桐先生论述王蒙时用了一个新鲜的说法——“王蒙的文学存在”。借鉴朱先生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广泛涉足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多个学科的杨义先生,也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存在”。
杨义先生是“好书主义者”。他不信奉“一部书主义”,不肯在一个根据地里固守,而是希望看到学术的城池一座连着一座。他目前的著述量已达一千万字,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代表作,如《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中国叙事学》,以及近年的“先秦诸子还原”系列。单单《论语还原》一书,就达到百万字的篇幅。这么大的著述量,就是单纯机械地抄一遍,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也得抄上10年。何况这是著书立说,还要加上读书、消化、酝酿、行文的工夫。有人说他是“成吉思汗”,有人说他是“徐霞客”,当然,他谁也不是,他只是“杨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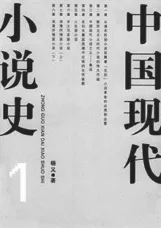
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影
杨先生常说,学者要通过自己的著述来说话。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坚持不说官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有人认为杨先生做研究不够“专一”,但他其实颇为专一。他退休前供职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40年的工作中,他一直在谈文学,谈中国的文学。他每部书的名字不是“小说”“叙事”,就是“诗学”“诸子学”,这是他作为文学研究家、小说史家的本色行当。在新学家眼里,他旧了一点;在旧学家眼里,他新了一点。他的存在多少有些突兀,显得有些孤零零。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杨先生以不变应万变,最终塑造了一个风格独特、我行我素的杨义。所谓“行”,就是不断地向前走,不知疲倦,不肯歇脚;所谓“素”,就是老实诚恳,所见即所得,看人人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能听得懂的话。从早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最近的一部《论语还原》,他的学术风格始终没有改变。他虽多次拓展研究领域,却始终谨守着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还有比这更“专一”的吗?
杨先生今年刚好满70周岁,并不算是高龄的人。这些年总有人向我问起杨先生,说到他的年龄,他们都很讶异:“他才六十几?总觉得他是80多岁的老人了。”此言并非指他相貌之“老”,而是学术辈分之“老”。想来这是他成名甚早的缘故,50岁刚出头,他便出版了10卷本《杨义文存》,名声直追前辈学者。杨义不仅写文章是前辈学者的做派,行事为人也有着老一辈学人的率性风范。在他任文学所所长的时候,每周二是返所日,如无会议或公务,他都会到每个办公室串门。他开怀大笑的声音,可以从楼道的最东端,传到几十米开外的最西端。所以,想在办公楼里找到他是比较容易的,只需在楼道里站定,数分钟内必能听到他的笑声,循声而觅即是了。近几年来,这笑声又回荡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的办公大楼里。
我跟随杨先生读书多年,深知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和随和。有一年,他带我们几位弟子去英国访问,先后到了剑桥、牛津,还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当然,他也不忘带我们去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在莎翁故居参观的时候,我们看到莎翁小时候的玩具,不禁为这些玩具的质朴而感慨。杨先生也和现场的工作人员用英语聊天,他说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工作人员和他对话时的笑容。访英期间,每到一处,他都会兴致勃勃地跟人聊天。有时犯了烟瘾,又忘了带打火机,他就随手招呼陌生的路人,向其借火,免不了又要聊上几句。在伦敦时,我住在比较便宜的青年旅社,杨先生住的稍好些,是澳门大学采购处代为预订的酒店,名叫President Hotel,我笑称其为“总统酒店”。杨先生也笑着说:“老板吧,老板酒店!”后来,我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一位男子在收银台用中文对店员说:“选好了,拜托检查下,没写Made in China的,我都要。”我想这一定是位有钱的中国老板,遂想到杨先生的妙译。
章学诚曾说过:“盖登太山绝顶,则知千万途径之所通,登者止择一径,而以他径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杨先生深明此义,坚持走自己学术的登山之径。他重视史料,也强调通识,注重在考证基础上达到对历史和文化的宏观认识。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看,杨先生在治学的规模和取向上是趋近于钱穆的。只是,钱先生的文字偏理性,是“刚”的;杨先生的文字理性之下有着感性,是“温”的。当然,杨先生本人十分反对拿他与别人作比。我喜读杨先生书中分析历史人物时的包容和体贴,他对人生世态有着相当细腻的体察,对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往往寄以令人叹服的耐心。既倾听,又剖析,这大概就是他所倡导的“触摸体温”的研究法吧。他在一篇论文中这样分析鲁迅的散文:
令鲁迅刻骨铭心的,还有父亲临终的一幕。衍太太这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应该给父亲换衣服,将纸锭和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还一再催促:“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于是一片叫声,叫得父亲已经平静的脸忽然紧张,微微睁眼,仿佛有些苦痛,一直叫到他咽了气。“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写这篇回忆散文时,作者耳中还鸣响着在衍太太催促下呼叫“父亲”的声音,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人在感情悬崖上所受到的刺激,可能烙下难以除去的疤痕。鲁迅指认,这疤痕是作为世俗礼节之象征的衍太太烙下的。他记下这如陨石袭来的变故和灾难,也就留下了他心地里至为柔软的人性人情。这里开始积蓄了鲁迅对世俗礼仪憎恶和复仇的某些因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杨先生从鲁迅散文的一个细小情节中分析出鲁迅心底“至为柔软的人性人情”及“对世俗礼仪憎恶和复仇的某些因子”,这样的分析是妥帖的。他对先秦诸子的分析,也随处可见这样细腻的笔致。除了条分缕析地说明事理,杨先生的文字还有穷形尽相、酣畅淋漓的本事,尽显文人的笔墨才情。他的演讲也是如此。有一次杨先生讲完庄子之后,我亲耳听到有人感慨:杨先生所讲的庄子是“活”的。

杨义先生在剑桥街头借火点烟(李思清/摄)
杨先生的治学道路颇为特殊。一般学者做学问是循序渐进的,如同木工做家具,是一锯一锯地锯、一钉一钉地钉,敲打琢磨,渐次成形。杨先生也经历了这样的加工过程,但他的过程非常迅捷,像是火山喷发,一转眼工夫,满眼的景致就出现了。翻读他的著作,会感到细处精致、大处宏伟、自出机杼、不落俗套,让人难以效法。他这样的学者可遇而不可求,像是自然天成的。他所强调的学术研究中的“生命体验”与“悟性透入”,以及近年来他在研究先秦诸子时提出的“触摸诸子体温”的思路,均有开风气之先的深刻意义。仅靠科班学术的训练,很难达到他这样的境界。

剑桥重游,一家餐馆中小憩
有一次,在澳门大学的学生食堂,我和杨先生饭后闲聊。提到他的学术方法,我说自己曾经读过不少关于他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的评论文章,想请他谈谈对自己的看法。杨先生说,他总结过一个“五学”。我说,“五学”是很好的总结,但还没有触及到先生的学术个性。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一个年轻人按照“五学”所倡导的方法去做,仍会有不得其门而入的可能。杨先生说,“撬瓶盖”也是一个方法。所谓“撬瓶盖”,据我的理解,应是熟悉研究对象的肌理,明了其关节和瓶颈所在,在“瓶盖”这种易于着力、易于奏效的部位入手,之后就可以深入瓶中,探研其奥秘。说到“撬瓶盖”,我又想起“管锥”。杨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一书中,曾结合《管锥编》的书名,将钱锺书的学术方法归纳为“以‘管锥’之功求‘打通’”:“从典籍文献中剥离出一些文句诗行,作为富有包孕和生发之内涵的‘知识质点’,强化其联想性和穿透性,从而在固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纸障上刺破一个小窟窿,从这个有限的视点中窥见不同时间、地域、语种、文体、学科的人类智慧关联和心智相通的无限性。”其实,这也是杨先生常用的方法。比如他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比较中西对时间(年月日和日月年)的不同表达方式,分析中西叙事学的差异,以及在《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比较文学古今、中西参照的方法论》一文中对鲁迅作品的生命密码之分析,均用了此法。如果说前一个方法是“找孔”——找到现成的“孔”,后一方法则是“穿孔”,在无孔处戳出一个“孔”。我又向杨先生提问,大意是不论“五学”还是“撬瓶盖”,都还是“技”的层面,这些方法论仍然不足以涵括先生治学的内在特质。杨先生沉思之后,未再说话。以杨先生的智慧,他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不论是“技”还是“道”,其实是有着十分清醒的思路和持守的,他只是不说而已。他觉得,这个问题不妨留给后人去思考。
还有一天晚上,杨先生利用写作的间隙,来我们博士后办公室聊天。杨先生说,他早年研究鲁迅,现在研究先秦诸子,尤其是当中的孔子,他发现我们这个民族中两个最了不起的人物,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见解竟非常接近。我们十分好奇,问先生怎么个接近法。杨先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进入了“失圣人时期”。由于近代史上袁世凯的祭孔和推行读经,以及后来军阀、政客和日本人的“崇孔”等别具用心的开倒车行为,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潮知识分子群体出于现代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把批判孔子当作诊治“中国愚弱病”的文化战略之一。其实,五四一代人所批判的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孔子,而是两千年沉积下来的人们对孔子的解释和涂饰。鲁迅对孔子所倡导的“中庸”的分析,就十分切合孔子的本意。杨先生称此现象为“鲁迅与孔子沟通说”。听过杨先生的叙述,我们兴致盎然,便问他,何以鲁迅会相隔千年与孔子沟通呢?这恐怕不是鲁迅有意为之,大约是不谋而合罢?可是,二人何以会不谋而合,或者说是殊途同归呢?我们忙请杨先生分析背后的文化原理。

杨义先生在英国期间的“读书证”(李思清/摄)
杨先生略有停顿,然后说:“譬如登山,一人从东面登,一人从西面登,越往上二人相距愈近。”我想到杨先生对文化现象时常有很妙的命名,例如“边缘的活力”等,遂请先生对刚才的“登山之喻”作一概括。杨先生想了想说,可以叫“登高趋近”。对此,杨先生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到本来的孔子》的文章,他写道:鲁迅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几乎读过全部的“十三经”,但他当时的思想趋于启蒙的异端,文艺上提倡“摩罗诗派”。他在杂文中又以调侃的笔墨做所谓“学匪派考古学”,以带有叛逆色彩的“学匪”自我戏称,对孔子抱着一种“并不全拜服”的态度,写下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文。鲁迅还曾这样调侃儒家“中庸”的思想方法:“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地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绝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它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杨先生进而分析道,鲁迅看问题,总是透入一层,深入到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看到人文学理的创造存在着某种“病灶效应”。透视这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实也是触摸到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战国之世,社会混乱,战祸频仍,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岂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可言?鲁迅引用来自儒家经传《尚书·泰誓》“除恶务尽”一语,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食肉寝皮”一语,来说明中国人并不中庸,可谓切合孔子发表中庸言论的时代情境。历史真是富有戏剧性,乍看起来,鲁迅与孔子思想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却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调侃之间,不期然而遇合。就仿佛在登山,一个从东面出发,另一个从西面出发,相距可谓遥远,但一旦“会当凌绝顶”,在“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却不期然而遇合。这种殊途同归,也许就是思想史上有意味的吊诡。但是,吊诡中存在的真实,有时是更深刻的真实。
这个“登高趋近”的原理,乍一听不是常识吗,又有何高深呢?我却以为,这是杨先生的一大发现,其文化贡献不亚于他当年所提出的“大文学观”和“边缘的活力”。因为“登高趋近”的提法,根源于他的“鲁迅与孔子沟通说”,经历了三千年的风风雨雨,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留日归国的鲁迅,可以说受到了现代文化的浇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也是人所共知。鲁迅在怎样的程度上与孔子“趋近”,二人的精神有何相连相通之处?杨先生从研究鲁迅开始,经过三十余年的跋涉,他追溯到了儒家文化的源头。他的“双视野”开始发挥效用,于是写成了《鲁迅诸子观的多维形态》。杨先生说:“在鲁迅心目中有两个孔子:一是本来面目的孔子,一是被历朝历代作为工具的孔子。前者有卓见,也有缺陷,不妨和他开开玩笑;后者则顶着越来越阔得惊人的高帽,被人用来干着种种勾当,使鲁迅冷嘲热讽之余,‘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为此,他写了文化批判长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此文立意不是考察原本的孔子,而是‘在现代中国’的风风雨雨中考量,让风风雨雨把圣人头上的纸糊高帽吹落在地,沾泥带水。”
杨先生又说:“就以对先秦诸子和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在鲁迅那个时代,许多知识者能够脱口而出地记诵孔、孟、韩、柳,需要解决的是不要落入他们的窠臼;80多年后的今天,能够顺畅地记诵孔、孟、韩、柳的已寥寥无几,需要解决的反而是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传承中加强现代性的创新。因此,当中华民族摆脱衰老贫弱、动辄挨打的处境,在80多年后崛起成鲁迅未尝预料的堂堂正正的现代大国时,我们已有足够的魄力,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他这种从学理层面沟通古今的努力,并不是人人有心思、有能力做得的,我们理应超越学派和学科的樊篱,真诚地呼应他的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中华文明的这一番探源、反思和重建的努力。
实习编辑/于溟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