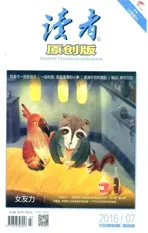少年A背后的一千个名字
2016-08-27hayashi
文_hayashi
少年A背后的一千个名字
文_hayashi

“惩罚”少年A
在青少年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日本制造的比例一直很高。以“光市母子杀害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来自天国的情书》,因千禧年少年犯罪事件频发而诞生的电影《青之炎》,都与青少年犯罪紧密相关。这既反映了日本影人对青少年犯罪题材的关注,也说明了日本青少年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此,我们借日本的《少年法》稍作管窥。
由中岛哲也执导、凑佳苗同名作品改编的日本电影《告白》,讲述了教师森口悠子在得知自己班上的两名学生杀害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之后,一步一步实施复仇的故事。森口老师在对全班学生的告白中,毫不留情地控诉了《少年法》的不处罚主义——未满14岁的儿童及青少年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对于14岁以下的犯案少年,法律不实施任何形式的刑事处罚。

《来自天国的情书》海报

《青之炎》剧照
“少年A”的称谓正是这种不处罚主义的表现之一。14岁以下的少年犯的名字不会以任何形式被公之于众,甚至杀人案件中的被害者家属也无法获知少年犯的姓名,男孩都被称作“少年A”,女孩都被称作“少女A”。自然,少年犯的其他个人信息也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在犯罪事实被确认之后,少年犯就像被放入了一套与社会高度隔离的保护系统中。经过保护、教育和改造,并被确认改过自新后,少年犯会以完好无损的状态重新融入社会。至此,对一个少年犯的处置宣告完成。
日本在1922年制定的《少年法》(现称“旧少年法”)旨在防止青少年再犯罪。二战后,由战时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持修订的《少年法》仍坚持这一原则,少年犯一般会被送往各地的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接受再教育,即使需要接受审判,处理结果也很难称得上是处罚。2015年的日剧《天使之刃》便围绕《少年法》的不处罚主义展开。剧中咖啡店老板桧山的妻子祥子被三名少年杀害,桧山在事件调查的过程中不断知道身边的人与少年犯罪有关的过去,并一步步接近真相。剧中的记者贯井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官、检察官、律师、少年犯的监护人,一群少年犯的保护者商议着对少年犯的处置,而受害者家属却完全被排除在外。”
这部法律在20世纪末的几年中遭到了最大规模的质疑。这场质疑的最初挑起者,正是《少年法》保护的一代日本青少年。
质疑《少年法》
1997年5月27日清晨,神户市友之丘初中的门卫发现了6年级学生土师淳被割下来的脑袋——他已经失踪三天了。与放置在学校门口的脑袋一起,还有一则犯罪宣言。
神户警方迅速出动,并把这起事件和引起全市恐慌的其他两起儿童被杀案件联系在一起。通过比较笔迹、走访和询问友之丘中学的教员、学生及学生家长,警方最终将目标锁定为一名14岁男生,并于当年6月28日对其实施了逮捕。这就是轰动全日本的“神户儿童连续杀害事件”(又称作“酒鬼蔷薇圣斗事件”)。
“当我杀人或导致他人身体受到伤害时,我觉得自己从持续的憎恨中获得自由。我能够从中得到内心的和平。减轻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这是犯案少年在被捕前寄给神户新闻社的挑战书中的话。露骨的声明震撼了素来以隐忍著称的日本社会。国会因为这起案件,把刑事责任的最低适用年龄从16岁下调至14岁。然而,这名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A依旧没有受到什么刑事处罚,犯案之后的7年间,少年A辗转待过两个少年院,最终于2004年3月10日假释出院,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
法律以其不容置喙的方式做出了对少年A的处置,然而公众似乎另有一番见解。少年A被捕之后不久,杂志FOCUS刊登了他的姓名和照片,虽因为被指控触犯了法律而被召回,但诸如此类的曝光一刻也没有在互联网上停止。据说有人专门搭建网站储存少年犯的资料并长期更新,甚至可以追踪到少年犯回归社会后的工作场所,并发出“你们的新同事以前杀过人”“新来的那个人是强奸犯,晚上不要和他单独出去”这样的警告信息。
但是,大多数媒体关心的似乎是另一回事。各方面的报道指向的似乎都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为了得到更高的收视率:他们分析嫌疑犯的身份和动机,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把犯罪专家、教育专家都请到演播室——犯罪专家画出行凶的时间轴,还原案发现场;教育专家分析少年A的身世背景、成长经历。唯独少有思考过大众媒体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

《告白》海报
一千个名字
“神户儿童连续杀害事件”中的少年A之后写下自传《绝歌》,这本详细记述案发经过、自我剖析犯案前的性冲动和精神状况的手记最终于2015年正式出版。在书的末尾,著者“前少年A”向受害者家属致歉:“把这些写下来是我救赎自我的唯一方式。”《绝歌》因为自我辩护和有消费受害人的嫌疑受到日本舆论的猛烈批评,但是即使如此,这些文字还是借由媒体大规模地传播了。
“少年A”的称呼背后,是一千个、一万个有名有姓的犯案少年。这个称呼可能是日本这个素来以文明、安全著称的国家身上一处颇为隐秘的伤口,极深,但因为太深了,人们往往只来得及关注表层。人们分析少年犯之所以成为少年犯,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比如是否受过虐待)、学校环境(比如是否受过欺凌),这些围绕着少年犯的小环境被人们认为是犯罪的直接诱因。以“保护”为第一要义的《少年法》和大众媒体,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庇了这些犯罪行为,甚至在无意中造成了某种暗示:犯罪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用受到处罚,还可以得到社会的谅解。这种暗示很可能催生了数量更多、情节更为恶劣的犯罪,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少年犯罪寄生的温床。
以“神户儿童连续杀害事件”为始,日本在千禧年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由17岁左右的少年犯下的恶劣罪行,甚至诞生了“愤怒的17岁世代”这样的流行语。而在“神户儿童连续杀害事件”的少年A假释出院两个多月后,11岁的御手洗怜美被同班同学“少女A”用美工刀残忍杀害,引发了国会关于再度下调刑事责任的最低适用年龄的讨论。2015年以来,川崎、船桥、刈谷又相继发生了几起恶性少年犯罪事件,几乎每一起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社会的讨论和国会的震动。继下调刑事责任的最低适用年龄之后,日本国会也终于在2014年大幅上调了少年犯的刑事责任上限。但是,亡羊补牢的思路不该用在关乎人命的领域,引起大众瞩目的也不该是鲜红的血。《少年法》如果一直在事件之后后知后觉,少年A的背后将不仅是一千个名字,还有一千堆逝者的骸骨,一千个家庭痛苦的哭泣。
相关链接
近年来,国内未成年人暴力事件频发:辱骂殴打、持刀威胁、强迫脱衣、拍摄裸照……与这些暴力事件相关的新闻,尤其是视频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2016年4月22日,山西绛县15岁少年张超凡被人殴打致死,而施暴的6名未成年人都是张超凡的同学,这一恶性事件再次引发了公众关于“是否应该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并加重刑事处罚力度”的讨论。
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才负刑事责任。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新浪微博一项关于“你赞成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承担法律责任吗”的调查中,有23045人参与了投票,其中85.6%的参与者选择了“赞成”,1%的参与者选择了“不赞成,孩子还小,应该多给机会”,另有13.4%的参与者投给了“刑事责任年龄门槛应当降低”。
支持者认为,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款是在1979年制定的,已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现在的未成年人的心智和身体成熟的时间已经大大提前。现行法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未成年人在犯罪时的放纵,而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有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侥幸心理。
此外,支持者还认为不应夸大教育感化的作用,严格依法定罪处罚,更能使施暴者认识到自身的罪责并真诚悔罪,更有利于教育和挽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呼声很高,但法律的制定或修改不应简单地顺应民意。
多位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士建议,应当完善少年司法体系,给未成年人更多接受教育和改正的机会。
反对“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原因主要有:一、应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法律应适用于普遍现象,不应对偶然的、罕见的个案过于敏感,并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二、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现象要从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法,尤其是惩罚不能代替成年人应承担的教育和监管责任,如果简单地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不免有推卸责任之嫌;三、未成年人犯罪应预防为主,惩治为辅。
2016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年”新闻发布会上,面对社会关心的“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年龄”问题时,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表示,单纯靠刑罚惩罚的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每差一岁都将涉及很大范围,应当通过增强预防与控制手段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负面因素,净化社会环境,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一味打击,会将涉罪未成年人推向社会的对立面,我们会丧失教育、感化、挽救的良机。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这个原则并不是否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刑事制裁,而是强调了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与可替代性。
“适当运用刑罚手段,并不违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惩罚也是为了教育。是否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需要进行大量论证,最高检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为妥善解决有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史卫忠说。
(小 德_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