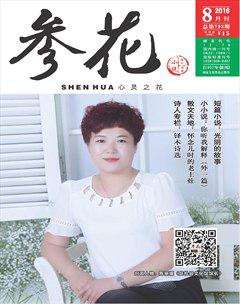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墙上的斑点》中的诗化语言
2016-08-23赵婵
◎赵婵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墙上的斑点》中的诗化语言
◎赵婵
《墙上的斑点》虽然是伍尔夫早期的作品,发表该作品时,她“诗话小说”的概念和理论尚未成型,但是在这篇短篇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诗化小说的雏形和特点。本文从弗吉尼亚·伍尔夫诗化小说的特点出发,分析《墙上的斑点》中体现的诗化语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 《墙上的斑点》诗化语言
一、引言
《墙上的斑点》是21世纪英国文学史著名女作家、批判家、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部早期作品。该作品因其与传统小说旗帜鲜明的区别被公认为当时先锋性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发表该作品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尚未形成系统诗化小说的概念和写作理论,但是在这篇短篇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诗化小说的雏形和特点。本文从弗吉尼亚·伍尔夫诗化小说的特点出发,分析《墙上的斑点》中体现的诗化语言。
二、诗化小说特点简述
伍尔夫的诗化小说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内心化”。诗化小说不以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外貌、性格为目标,而更关注人物内心思绪的变化。伍尔夫甚至简化人物内心的描写,通过突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的和谐关系,通过场景、气氛、意境的描写和渲染使小说呈现诗性。2.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伍尔夫以超然的心态,从高处斜俯视人及其生存的整个世界,思考人与人、人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复杂、微妙的关系,以从主题上凸显诗性。3.象征的运用。象征是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它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形象(象征体)和本体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引发人们大脑的联想,以表达某种概念、思想和感情的艺术手法。伍尔夫的作品大量运用诗歌常用的象征手法,从写作手法上体现其诗性。4.对传统叙事结构的解构。伍尔夫的作品摈弃了传统小说惯用的时间、地点或事件等一维线性的叙述解构,建立了当时颇具争议的多维化立体式网状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主要有两种呈现形式:一是以一个人物或事物为核心,向四周发散出网状的叙事结构;另一种则是以主次人物,主次线索交织成网,浑然一体。
三、《墙上的斑点》中的诗化语言
(一)“内心化”和“网状叙事结构”在《墙上的斑点》中的体现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文学上主张:“让我们按照原子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他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无论从表面上看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协调。”(摘自《狭窄的艺术之桥》,弗吉尼亚·伍尔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墙上的斑点》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的这一文学主张。它详细记录了从我发现墙上有一个斑点后,所引发的一连串联想和意识转换。文章中,伍尔夫完全隐退,从主人公“我”的视角描写“我”从墙上的一个斑点,联想到这个斑点可能是墙上的一颗钉子,接着想到油画——贵妇肖像——房东——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玫瑰花瓣——特洛伊城——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思考——古冢——木块的裂纹,进而联想到木质、树液、树木夜晚独自屹立在山上。最后借由别人的口,说出这个斑点是一只蜗牛。《墙上的斑点》详细地描述了“我”整个内心思绪的变化,看似散乱,实则以墙上的斑点为中心,思维向四面八方发散,构建了伍尔夫“诗化小说”独有的多维化立体式网状叙事结构,自成体系,形散神不散。
(二)《墙上的斑点》对人生和哲学的思考
《墙上的斑点》虽然创作于伍尔夫“诗化小说”理论尚未成型之时,但是也已经具备“诗化小说”的一些特点。小说中“我”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也就是伍尔夫对人生和哲学的思考。小说中的“我”以墙上的一块斑点为中心,进而联想发散,对人生、生命进行了零散的、碎片式的开放性思考。比如,小说中“我”由墙上的斑点联想到油画、房客,进而感叹人与人相识的偶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短暂。正如伍尔夫在小说中所用的比喻——“这种情形就像坐火车一样,我们在火车里看见路旁郊外别墅里有个老太太正准备倒茶,有个年轻人正举起球拍打网球,火车一晃而过,我们就和老太太以及年轻人分了手,把他们抛在火车后面。”(《墙上的斑点》,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见《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刘象愚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又进一步思考生命的神秘、思想的不准确、人类的无知、事物的不可控和生活中的偶然。为了进一步支撑自己的观点,小说中的“我”列举了装着三个订书机的浅蓝色罐子、鸟笼子、铁裙箍、钢滑冰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弹子戏球台、手摇风琴等的遗失,从而感叹快节奏的生活,生活中永无止境的消耗和修理以及生活的偶然和凑巧。接着,又从人转世投胎地点的随机性,进一步说明人生充满了偶然性。最后,通过阐述人无法定义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这些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来说明人类的渺小和无知。同时也说明了生命的同一性。“我”把人的生命和花草树木的生命做比较,以说明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哲学上,“我”想到了大自然的不可抗,想到了惠特克的哲学——“每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进而揭示了人生的本质和规律。
(三)象征手法在《墙上的斑点》中的运用
象征是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伍尔夫“诗化小说”表现诗意的重要手段。《墙上的斑点》两次运用了象征的手法。第一次,文中的“我”提到了镜子。镜子作为意象象征着“模糊”及“透明”,在小说中代表了人们的丰富、广博、多变的内心世界。文中提到:“假定镜子打碎了,形象消失了,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只有其他的人看见的那个人的外壳——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肤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墙上的斑点》,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见《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刘象愚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伍尔夫运用镜子这个意象,把现实中闷人、肤浅的世界以及无趣、呆滞的“我”和镜子中浪漫、丰富的世界以及灵动的“我”进行对比。接着,同一段出现了另一个意象“水”。它也象征着人类的内心世界。“灰暗的海水”以及“水中的闪光”分别象征着人内心晦涩不明的区域以及人内心偶尔获得的启示和真理。文中“我”的思绪最后被买报纸这个行为拉回现实之前,也提到水这个意象。“我”由斑点想到了木头,想到了树木以及树木生长的环境——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小河边”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意象。它和前面的意象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和“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则是代表人内心偶尔获得的启示的另两个意象。文章中这些意象的使用,象征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伍尔夫对传统小说的批判,表达了她“诗化小说”理念(虽然当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家不应该花费大量的笔墨、精力去刻画外在世界、人物的外貌、服饰,而应该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以及思绪的流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墙上的斑点》虽然是伍尔夫早期创作的意识流小说,伍尔夫“诗化小说”的写作思想也尚未成型,但无论是从这部小说对“我”内心的关注、独特的网状叙事结构、内容上对人生、对哲学的思考,还是意象、象征手法的运用都基本具备了“诗化小说”的特点。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伍尔夫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不满,以及对新小说形式和写作方式的探索。在那个时代,这部小说无愧于“先锋性”小说的称号。它的出现具有示范作性和开拓性。
(责任编辑象话)
(赵婵,女,博士在读,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