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城市内河的社会共治样本
2016-08-18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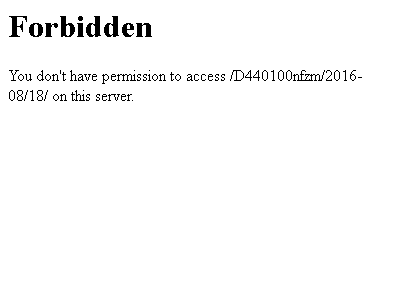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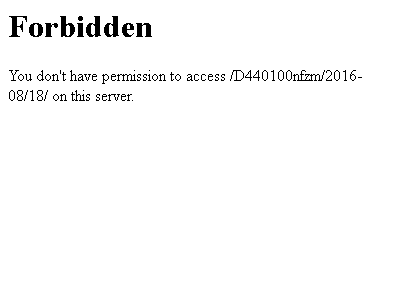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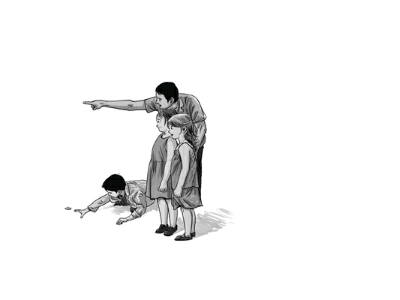
一个城市政府的殚精竭虑,一场持续两年的社会试验,一批民间组织的固执坚持,引发了广州一条重要内河的保护意识觉醒。当我们在关注政府如何优化调整供水格局时,更广阔的思考视角是,一条城市河流如何实现社会共治。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发自广州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倩
“对于老广州来说,流溪河就是母亲河。”2016年8月6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是珠江的支流,也是唯一一条全流域在广州境内的河流,老广州人喝着流溪河水长大。因水质问题,先是2010年广州将西部三大水厂的取水点搬离流溪河,2016年7月,广州市举行听证会,对全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相应进行调整。
这亦是中国城市河流的缩影,一面是城市规模扩张、人口剧增与沿河居民要求发展的现实,一面是流域生态保护、水质改善的城市梦想。
当广州市政府为这条“内河”殚精竭虑时,社会力量起而行之,以有别于官方的资源和视角切入流溪河保护,为我国河流治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样本。
两年乡村试验
2016年8月10日,广州市环保局长杨柳来到乐明村时,3户村民正尝试在农田里养殖澳洲淡水龙虾。放在两年前,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志强刚开始驻村时,当地人肯定不会接受这“异想天开”的建议。
乐明村位于流溪河上游的广州市从化区,距离广州市区车程两小时。一条溪水由此发端并汇入流溪河。在这里,一场守护流溪河水源地的乡村试验已经默默进行了两年。
2015年一整年,张志强都住在乐明村。他负责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乐明村推广生态农业,让全村179户村民不使用农药化肥。
在流溪河上游,滥用农药化肥造成的农业污染是主要污染源,这也是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面源污染。张志强做过检测,刚出山的清泉流经村庄和农田后,水质降为三类水。
长年过度施用农药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化严重,村里主要种植的砂糖橘没了收成。因为身处流溪河水源地,村民不能大规模养殖牲畜,本已为水源保护做出了牺牲。如果理由仅仅是“爱护水源、保护环境”,张志强自己都觉得开不了口。即便开口,也没有人理会——对于乐明村而言,他只是一个外来者。
“没有人天然地会为环保埋单。如果你提供的替代方法不经济,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更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张志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他入驻乐明村后,时时思考的问题。
另一个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珠江项目中心也投身于这场乡村试验,中心主席严俊经常张罗会员企业家们到村里看一看,感受乡土风光的同时,为其发展出谋划策。张志强则组织部分村民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帮助他们销售自制的青梅精、青梅酱等加工农产品。
乐明村开始慢慢接受这些外来者。2015年8月,张志强抓住每一位相熟的村民,去听一位台湾来的专家讲解生态农业。隐藏来意驻村近一年后,这场乡村试验终于破题。
20个村民来听生态农业培训,第二天跟着台湾专家走访果林的只剩6人。而专家给出建议,要用益生菌堆肥改良土壤,停止使用农药化肥,同意参与的只有1人。张志强当时感觉很迷茫。
村民赵银玲就是“吃螃蟹”的人。“大家觉得用了农药化肥才有效益,堆肥万一不成功白费力气。”赵银玲以前在城市打工时听说过“生态农业”,既然有专家指导和志愿者帮忙,她决定试一试。
还有一个本土企业广汽本田也加入到这场农村试验。2015年末,广汽本田把目光放在了流溪河水源保护上。该车企的环保公益项目负责人来到村里调研时,正看见赵银玲利用废弃的旧屋子,将杂草、树枝、牲畜粪便等堆集起来,把益生菌扩繁后,开始堆肥。看到保护水源的方法可以这样落到实处,广汽本田开始筹划扩展这场乡村试验。
到2015年末,有机堆肥开始成为合作社的一项集体活动。张志强和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们共同制定章程,逐条讨论通过。“其中一条是,如果不使用生态的方法,一旦被发现就要退出合作社。”合作社还在摸索其他生态农业方案,如稻田养殖龙虾,水稻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微生物为龙虾提供饵料,龙虾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生物肥。如果成功,每亩稻田能增收3500元-4000元。
合作社也借助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帮助村民们分担风险。有企业家出资替村民买果苗,等到收获时节,村民再回馈以等值的水果。村民们还给合作社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良源物予,寓意是在流溪河水源地做良心农产品,分享给社会,以谋求当地长远发展。
环保局长的请托
既要促进乡村发展建设,又要保住硕果仅存的流溪河水源地。面对这样的难题,试图给出答案的乐明村试验吸引了众多关注。
8月10日的一场启动仪式,成为多方共治流溪河的一个缩影。会上有广州市环保局、广汽本田、绿芽基金会及阿拉善珠江中心相关负责人,恰好代表了政府、企业、民间的三方力量。
作为广州本土企业,广汽本田执行副总经理郑衡希望为流溪河保护做点事,该公司决定参与并延续这场试验。广汽本田和绿芽共同策划了流溪河水源地保护行动,第一期项目为期3年,将建立三个生态基地——益生菌堆肥基地、生物防治基地、生态养殖基地。
“环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们推动村民自组织,在社区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实现河流保护。”除了乐明村,还有许多村庄处在流溪河水源地,严俊正在思考怎么让这个乡村试验在更多地方扎根。
而广州市环保局的现身似乎预示着官方对民间试验的认可。启动仪式前,市环保局长杨柳在留言簿上写下祝辞:“心中的流溪,梦中的河。”
27年前的一个秋夜,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的杨柳第一次来到流溪河,在上游的流溪河水库做水质监测。“当时被流溪河的水、流溪河的气质、流溪河的风光深深震撼。”
27年后的流溪河,气质不似当年。它和中国每一条流经城市的河流有着相似的命运。“由于广州城市建设的发展,流溪河下游特别是白云、花都境内河段,水质很不理想。但是上游,特别是大坝(李溪坝)以上还保持着良好的状况。”杨柳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说。
对于流溪河的生态保护,广州市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近二十年内,有四部关于流溪河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流溪河专项整治行动也进行了十多次。2013年12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市流溪河流域保护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流溪河实施全流域专门保护。2015年10月,广州在全市河涌整治的背景下公布51条河涌“河长”名单,作为唯一一条广州市内河,流溪河市级层面的“河长”由时任市长陈建华本人担任。
环保部门无疑压力很大。2013年7月,杨柳做客广州市政府纠风办主办的《行风面对面》电视栏目,主持人询问他能否理解市民们对流溪河污染严重的焦急时,杨柳回答:“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也是广州市民。”
如今,面对聚集在一起的各界人士,杨柳一再请大家多帮忙:“刚才有人说感谢我们(政府),其实相反,应该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政府感谢社会力量支持。政府只能做主导,出台政策和方案,真正有效的保护来自社会方方面面。”
听说张志强读大学时学的是社会工作,杨柳很欣慰:“你这个专业好!河流保护不只是技术问题,终归是社会管理问题。”他似有无限感慨要发,停半晌后说,等到10月假期他再来乐明村,自掏腰包买点小龙虾。
民间组织的执著
张立凡也在广州环保部门工作过,但在广州市饮用水源地区划调整及流溪河下游保护区削减一事上,张立凡有不同看法。
“我们在‘负隅顽抗。”这位流溪生态保护中心主任笑称。2015年3月,他成立了NGO广州市海珠区流溪生态保护中心。几乎同时,流溪河因广州市饮用水源地区划调整,成了本土NGO关注对象。
2010年西江引水工程建成之前,以珠江西航道和流溪河为水源的西村水厂、石门水厂、江村水厂的水源水质状况处于劣五类,而这3个水厂的所供水量占全市用水量的60%-70%。最近10年,广州市中心城区饮用水源地完成了三大远距离取水工程,形成东、南、西北三足鼎立的水源格局,同时以流溪河、珠江西航道等作为广州备用水源。
2015年上半年,广州市水务局发布《广州市城市供水水源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其中提到拟取消流溪河下游水源功能。
经过多年的治理,流溪河下游水质未见好转。当时,广州多家环保组织联合在网络上发起“1人1元为流溪河建污水处理厂”的活动,号召市民在规划公示期间用行动保护流溪河。
民间有反对调整的声音,官方有必须优化的理由。
“下游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把取水口设在那里也取不到好水。保护水资源是毫无疑问的,但不代表不考虑现实。”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水源地调整方案论证时,包括环保局在内的相关政府部门及9位评审专家最终全部表示赞成。
到2016年6月,水源地调整听证会前夕,环保组织陆续表达自己的声音。
NGO创绿中心成员官俊峰曾写过《广州市饮用水源地现状民间观察报告》,他频频向媒体投书;流溪生态保护中心征集了697位广州市民给市长留言,还起草了一封给市长的公开信。“水污染问题专家、城市规划专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为了保护流溪河,我们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做。”
听证会后,广州市环保局认为,政府不会减小对流溪河的保护力度:“尽管西村水厂、石门水厂、江村水厂等已停止从珠江西航道、流溪河下游、白坭河取水,按照有关技术规范,上述河段本可以不再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改善上述河段的水环境,调整方案仍然保留珠江西航道、流溪河李溪坝以下河段和白坭河的部分水域及其滨江带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实施比一般水污染防治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
“举报太简单了”
“政府不要嫌(民间)闹腾。有他们闹腾,大家会看清楚流溪河污染的本质和治理的难度,否则这些就被掩盖了。”陈晓宏早在2003年前后提出西江引水的设想时,就已经预见到今日流溪河污染积重难返的局面。
陈晓宏认为,流溪河污染最严重是21世纪初。这十多年,流域内人口和污染源都在增加。“水质当然本来就很糟糕,但至少没有恶化,尤其近三年处于基本稳定、略有好转的状态。对政府治水还是要有信心。”
在张立凡眼中,重要的不是信心。他更关心,当政府治理流溪河力有不逮时,社会力量能够填补多少。甚至,“流溪河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样本”。
深入调研流溪河后,他有许多新发现:
并没有一个“大国企或世界500强”在向流溪河排污,影响流溪河的,是两岸居民。在流溪河下游的太和镇,有无数做印染或食品加工的小作坊,往往是三两个外地人租房,搬几件工具进去就能开工。“居民希望流溪河变清,但也会保护租客,希望地价起来。他们构成利益共同体。”流溪河流经广州的城中村,要想将污水管道修进去,先要面对征地拆迁问题。流溪河两岸开着许多农家乐,每当政府开展整治行动时突击关停一批,风头过了,炊烟又会升起。
流溪生态保护中心成员陆志坚以前在自来水厂工作,当时,他会将这些排污的小作坊、农家乐都视作污染源,向政府举报。而现在他清楚当地环保执法人员人手不足,更重要的理由是:“举报太简单了。”
现在,他选择去和污染了流溪河的人们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史,问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每月能挣多少钱。“政府可以上工程、搞环保执法,但流域环境问题是多元的,流溪河的背后是多种社会关系。”
广汽本田在乐明村举办流溪河源环保亲子公益营,邀请父母与孩子一同在流溪河水源地起居生活、接受自然教育,在村民导师的带领下体验生态农业。他们希望以孩子带动家庭,再以家庭带动社会,不断传递环境保护的价值。
“保护流溪河不是发起一场campaign(战役),认准一个敌人,打倒它就好。你不知道你的对手在哪里,有的‘对手可能比你还小。”河流与人,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张立凡希望能解答两个问题:谁造成了流溪河污染现状?社会力量能为流溪河做什么?
趁着暑假,流溪生态保护中心组织了一场田野调查夏令营,驻地在太和镇白山村,流溪河支流边。13个昼夜,17个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流溪河,有时候,他们调研的主题甚至和环境保护没有一点关系。
8月5日,夏令营结营。仍然没有人能解答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但他们收获了同样的责任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