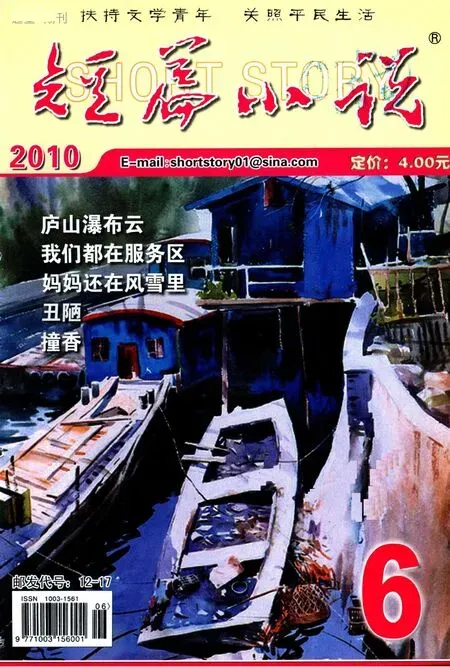皮可之死
2016-08-11吕传彬
◎吕传彬
皮可之死
◎吕传彬

01
皮可来找我的时候,正是盛夏,墙角的草长得像火焰。风低低的,卷起纸屑,在走廊上飘来荡去。宿舍楼有五层,我住在五楼,皮可费了好大劲爬上来。他在每个楼梯的拐角都闻到了刺鼻的尿骚味,他一边屏住呼吸,一边骂骂咧咧。因为这样,他吸进更多的尿骚味。
“祝元!”皮可在门口喊。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像受伤的野兽。
我正在啃西瓜,我将西瓜皮一把甩到他脚下。他跳起来,在空中停顿十分之一秒后又落下。他居然趁这个空档,用脚尖将西瓜皮踢远了。
“祝元!”他明明看到我了,但继续喊。
皮可是我的朋友,一天到晚咋咋呼呼,心理医生对此有解释:这种人情绪不稳定。可是,谁情绪稳定像定海神针呢?多半是不稳定的。只不过皮可将自己绑在钟摆的最下端,晃出去的距离比较远而已。
几分钟之后,我和皮可一块出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才再次出现,以至于我的宿友以为我失踪了,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
02
皮可死的那天已是冬天,他蜷缩在草地上,不远处有个小池塘,结着薄冰,鸭子正试图在冰上行走。他被人们发现的时候,一条野狗正在舔他的脸,他的身边有一些呕吐物,已经被野狗舔干净。呼啸而至的警车将他带走后,围观的人群开始讨论他的死因,不过,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做为皮可的朋友,少不了要回答一些警察的提问。譬如: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有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我说:那天他来找我,说失恋了,要我陪他出去走走。我们在路上拦了辆车,到了另一个城市。之后,我们在一家地下旅馆住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都得忍受隔音差的折磨。墙壁根本算不上是墙壁,一层三夹板,敲起来咚咚作响。如果仔细找,甚至能找到细缝,看到隔壁房间男人的屁股和女人的肚皮。
你们去地下旅馆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们在街上走累了,就想找个地方躺下。草地上有流浪汉拉的屎,表面上看不出来,一躺下去就知道了。相比之下,地下旅馆好多了,有床、有热水。
那么,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自杀?
不知道,真不知道。回来后,我回学校,他回家,再无联系。
你知道后来他又去找杨稣吗?
不知道。不过这事对他来说正常。他恋旧,还很爱她。他俩虽然分手了,但他回头去找她,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们吵架,他吵着跳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不过他要跳楼也正常,从小到大,他经历了无数次跳楼,跟人打赌输了跳楼、欠了债逃债跳楼。总之,他经常跳楼,他的小腿骨折过、手骨也碎过,但都没事。跳楼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这么说,你做为朋友,已经对他放弃了?
怎么可能?!我终于不耐烦了。我很不客气地说,要是放弃他,我怎么会花一个礼拜时间,陪他住地下旅馆,忍受大老鼠绿幽幽的眼神?
可是,杨稣说皮可想杀她。
我愣了愣,忍不住想骂人。
03
杨稣在成为皮可的女友前,是我的女友。那时我是个极其虚荣的浑小子 (当然现在也是),认为拥有一个女友才能高人一等。至于为什么非要高人一等,其实就是一个浑小子的混账想法。虽说杨稣是那种走入人群就找不到的女孩,但能勾到她做女友,对我来说并非易事。
杨稣的妈妈是个接生婆,做知青时跟乡间接生婆学到一手,野路子,但管用,口碑不错。她在家私设了个小产房,有时忙不过来,就叫杨稣帮忙。因此,杨稣的生理卫生知识是我班最厉害的。她颇为自得,经常在女生面前卖弄生殖系统名词,搞得没见过世面的小女生一惊一乍,半天缓不过神来。
最让杨稣得意的是,她在初中时,有个高中女生托人找到她,求她帮忙。杨稣倒也仗义,让妈妈免费为她做了流产手术。两年后,那个女生毕业了,关于她的事却突然在校园流传开了,以至于校长不得不找杨稣前去核实情况,问有没有这回事。
杨稣说:有啊!不过我妈说了,年轻人犯点小错也是正常。
校长翻翻眼睛说:杨同学,请你对那位女生的清白负责。杨稣就乐了。
跟这种女生谈朋友,就像跟生猛海鲜过家家,要很小心才不会被她的螯钳住。我这可不是瞎说,譬如有一次,她走着走着就踩住我的脚。我惊呆了,之后恼羞成怒,一把将她推开。
她坐在地上哭了半天,边哭边责问我: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被我踩一脚又怎么了?你这个混蛋,居然推我,去死吧!
04
皮可说白了,就是个贱货。他有选择恐惧症,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看到别人有的,才会觉得正是自己想要的。我们这群人中,如果有谁穿了双最新的耐克跑鞋,他一定会在太阳下山之前买到属于自己的一双。可问题是:他是个平足底,跑鞋对他来说,只是个摆设。
皮可的毛病大家有目共睹,但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种病。当青春荷尔蒙开始成倍增加,他意识到自己该有个女友了。意识一旦被唤醒,行动也就开始了。
那天我牵着杨稣的手在大街上闲逛,皮可迎面走过来。他一脸迷惑,目不转睛盯着杨稣,杨稣则用天真无邪回应了他的炽热。
虽然我和杨稣手牵手的时间并不长,但我们已有过无数次争吵,这让我们彼此深深厌倦。而我们之所以还黏在一起,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找到别的事做。
此时此刻,我对他们公然调情并不忌恨,甚至有些欣慰。我知道杨稣是那种直截了当的女孩,很快她会告诉我:我喜欢皮可,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会说:好啊。
我要是有半点挽留的意思,我就是疯了。
她肯定会很不爽,但出于自尊,她会装做喜颠颠的样子离开。临走时她一定会说:去死吧,祝元。
05
杨稣对皮可来说,当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但皮可很快适应了杨稣的各种虐待。如果杨稣喂他苍蝇,他也能当成甜点,津津有味地吞下。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并无定论,主要看其中一个人是不是够贱。
毫无疑问,皮可够贱。但这也伴随着另一个问题,杨稣若是要甩掉皮可,将会变得很困难。这是杨稣未曾预料到的。
皮可被杨稣甩的那天,正值雨季,在毛毛细雨中,他和杨稣搭了小火车一起去山上看牡丹。那里其实是个矿区,为了运输方便,修了条窄铁路。在窄铁路上行驶的自然是小火车,按照皮可的说法,小火车的速度与大卡车大致相当。但杨稣认为,大卡车的速度远远超过小火车。
从车窗向外望,紧挨着铁路的那条马路上,大卡车就像小火车的外挂,一个小时过后,它依然在那里。但因为铁路边不时出现池塘以及小树林,马路不得不绕一下再转回来,可见,马路的总长度超过铁路。相同时间内,路程走得多,速度当然快,这是常识。但皮可突然恼羞成怒,他激动地擂着车窗,冲远处的大卡车叫道:混蛋,滚远点!
车厢里只有几位昏昏欲睡的乘客,皮可的叫声惊扰了他们的清梦。但他们无动于衷,朝皮可他们看了一眼,依然昏昏欲睡。
杨稣看看皮可,不再言语。
皮可则朝杨稣尴尬地笑了笑。
上山看牡丹是皮可的提议,他大概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以为时不时搞出些浪漫举动,便能与异性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个想法当然不错,但实施对象须分清。
杨稣肯定不是那种一点小浪漫就能让她晕头转向的女孩,她要的可多了。她之所以愿意跟着皮可出来看牡丹,是因为她想分手。一路上她都在推敲措辞,她知道彻底甩掉皮可,需要一定的技巧。
小火车到站后,杨稣没下车。小火车类似公交车,挨过半小时就往回走。气氛有些尴尬。皮可说:已经到了,还是下去看看吧。
杨稣说:皮可,我们分手吧。
皮可愣了愣,问:为什么?
这种时候大概只有皮可这样的傻瓜,才会问为什么。原因当然有的,原因就是要分手。
杨稣说:不为什么。
皮可继续问:为什么?这次他凑近杨稣,表情故作轻松,他想给杨稣台阶下。
但杨稣很冷静地说:分手吧。
皮可叹了口气,问:他是谁?在皮可看来,杨稣肯定有了新男友。
杨稣鼻子哼了哼,忽然说:祝元。
皮可惊呆了,他靠在椅背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和好了?
昨天。
不可能,昨晚我们还一起喝酒,他还在说你坏话、骂你。
杨稣突然就笑起来,说:傻瓜。
06
我本来叫祝远,但去派出所报户口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成了祝元。祝元就祝元吧,反正无所谓。
我在小学五年级和皮可认识,他转学过来,大家对他爱理不理。他也懒得与人打交道,成日倦在课桌前,似睡非睡。班主任看不下去,指令班长拯救这位苦恼的同学。于是,我出马了。
不过,这种拯救却造成了局面的失衡。皮可有些依赖我,他只肯与我在一起,不肯与人主动交朋友。我的朋友则因为我有皮可这样的朋友而开始轻视我。不用说,孩子间的友谊一旦沾上成人的功利,就不好玩了。
不过,半个学期后,大家忘了之前的想法,开始接受皮可。他走在我们中间,终于不再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
尽管如此,皮可对我的依赖还是与日俱增,以至于我不得不做出老大的样子,时不时责问:皮可,你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啊。他通常这样回答我。
皮可全名孟皮可,自从父亲孟晴海死后,他就把孟姓去掉了。他说:我姓皮。
皮可父母的事在我们这个小城颇为有名,即使再过二十年,他们的故事也会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被流传。
那天天气很热,杜子美早早就下班回家了。她呆呆地坐在屋里,并不像以往那样忙着烧晚饭。
皮可嘟囔了一声:我饿了。
杜子美依然坐着没动。若是往常,她即使坐着不动,也会说一句:冰箱里有吃的,自己弄去。
如果皮可聪明点,早该看出异样。但他无知无觉,依然嘟囔:我饿了。
过了会儿,杜子美就出去了。
孟晴海正远远地从巷子口走过来。当然,若不是杜子美再三要求,孟晴海下班后是不会回家的。他通常会去多多家,给多多和她两个儿子烧晚饭、搞卫生,吃过晚饭还要陪着写作业。多多则什么也不干,她坐在孟晴海身边,计算一天的生活费。
孟晴海每月工资二千八百多,他一领工资就如数交给多多。在多多的精打细算下,杜子美每月能拿到三百多。孟晴海将钱交给杜子美时,不忘关照一声:省着点花。
放屁。杜子美的唾沫喷了孟晴海一脸。
孟晴海不再言语,赶紧走了。
皮可很少见到父亲,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条巷子里有人比他还要惨,没出世父亲就死了,根本就见不到父亲。
07
在巷子中间,孟晴海遇上了杜子美。他停下来,很不耐烦地问:什么事啊?
杜子美面无表情看着他。巷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突然,杜子美嚎叫起来:孟晴海,你个没良心的!
孟晴海铁青着脸叫道:你疯了!你叫我回来,就为了吵架啊!
是啊,你以为还有什么事?
去死吧,马上去死吧!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孟晴海咆哮着,像一头被激恼的狮子。
很快,两人的争吵引来了一些路人,他们远远地看着他俩,并不靠近。他们在分辨他俩骂架的内容,以便能捕捉住隐私。但很快他们就后悔了,竟然没及时上前劝阻,罪过啊。当他们看到杜子美猛地扑向孟晴海时,就知道情形不对。
从远处看,杜子美像兀鹫那样扑向孟晴海,而孟晴海竟然没有退让。在一瞬间,杜子美的脸紧贴着孟晴海的脸。孟晴海通过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杜子美眼中的杀气。他犹豫了下,他在想:到底怎么回事?
此时,一把刀已插入他的胸口。他的心头一紧,而杜子美脸色乌黑,比他还像将死之人。
孟晴海晃了晃,想把刀拔出来,但杜子美死死地攥着刀把,不让他拔。孟晴海又晃了晃,他的腿已经软了,血开始漫出他的胸口。杜子美抱着他,看着他的眼神开始涣散。
这个时候她突然后悔了:晴海,你不要死啊!她开始嚎啕大哭。她的哭声像尖锐的蝉鸣,在炎热的黄昏吸引了足足一百个人。
只是,大家凑近时,纷纷惊呆了,血像河流一样流向巷子深处。两个在血泊中的人,一个在哭、一个快要死了。这时,头脑灵清的去报警,心地纯良的去叫皮可:皮可、皮可,你父母出事了!
皮可正在为咕咕叫的肚子郁闷,他问:什么事啊?
大事,死人了啊!
皮可去时,警察正要将浑身是血的杜子美带走。人群自动为皮可让了一条路,但皮可缩在人群里,坚决不愿见杜子美。这让杜子美大为悲恸,哭着、喊着要见皮可一面。
有人就说:你走吧,别再吓唬皮可了。
08
皮可说:我无法原谅杜子美,她杀死了我父亲。
皮可又说:我也无法原谅孟晴海,他抛弃了我们。
09
杨稣家就住在多多家隔壁,有段时间经常见到孟晴海。做为小人精,她早就从大人异样的目光中,看出事情的端倪:他们是一对姘头。
小城对“姘头”这个字眼并不忌讳,甚至有些放纵,明里暗里的暧昧都能接受。但是,孟晴海死后,人们开始愤怒谴责,要是孟晴海懂得收敛,做得不那么露骨,也就不会死了。只是,孟晴海已死,被众人唾弃的纷扰也只能由多多承担。
多多的年龄虽然比孟晴海大,但岁月没能将这种差距鉴别出来。与同年龄的女人相比,多多简直可算得上风韵犹存。
杜子美被枪决后,所有舆论都指向多多,而挖掘出来的真相也颠覆了大部分人的想象:多多竟是杜子美的朋友,也不知她看上孟晴海什么,竟然贴上去。风韵犹存的女人用上这招,能够抗拒的男人还真不多,更何况是孟晴海那样活泛的男人。
话又说回来,这也与杜子美的傻气有关。多多来她家串门,她会特意去菜场割一斤肉,留多多吃了晚饭再走。
吃过晚饭,孟晴海说:天太黑了,一个女人走夜路不安全,多多,我送你回家吧。
多多羞羞答答,要等杜子美同意。
杜子美忙着洗碗,说:好啊,孟晴海你去送送她。
多多的丈夫是个老实男人,孟晴海送多多回来,他会很拘谨地递上一根烟。孟晴海抽着烟,在黑暗中半明半灭地走了。
没多久,老实男人就被多多打发到大庆油田开采石油去了。多多亲自去劳务公司为他签好了合同:十年。
他临走时噙着泪,但没能哭出来。多多说:到了那别想家,多赚钱,我下半辈子就指望你了。
老实男人走后,孟晴海搬去多多家住了。他什么也没说,就突然消失了。等杜子美发觉不对头,事情已不可挽回。
杜子美傻了眼,她毫无办法。当然,她也试图去多多家劝孟晴海回家,但孟晴海冷着脸,看也不看她。多多一瞥见杜子美,就像影子一样躲起来了。
杜子美与孟晴海僵持半年,毫无结果。她只好哭,孟晴海皱着眉,撵她走,她也只好回家,到了家继续哭,哭得昏天暗地。
她的哭声对挽回孟晴海毫无作用,倒是惊扰了皮可,让他莫名其妙地发烧。杜子美抱着发烧的皮可去医院挂水,刚好碰到孟晴海的同事,他很神秘地问:你们离婚啦?
杜子美呆呆地看看他,问:谁说的?
孟晴海啊!他说这事,我们都不敢相信。你们这么恩爱,竟然也走到这一步,太不可思议了。
杜子美冷冷地回应:我们没有离婚。
同事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情形看起来比离婚还可怕。
10
杨稣觉得皮可有可能会遗传他父亲的花心,这事可说不准。但她不该当皮可的面说这事,太伤人。
皮可很不高兴,他开始沉默。杨稣又想起他的母亲是杜子美,忽然有些心悸:喂,你说句话啊。
皮可说: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皮可说话的声音很怪,像走错路的过路人,不耐烦中透着怨气。
随便说点啥。
那你到底去不去看牡丹?
不去。
皮可一个人下了小火车,下车后他又绕到车窗边,敲敲玻璃。杨稣低着头,装作没看见。
皮可就喊:杨稣!杨稣!
窗玻璃密封不是特别好,杨稣显然听到了皮可的喊声。她转过身去,背对着皮可。皮可终于觉得无趣了,向车站外走去。
出了车站,就是一个小小的集市,山里人挑着各种各样的担子来卖山货。矿区的工人是他们的顾客,坐小火车前来的游客也是他们的顾客,所以,每个出站的旅客都将淹没在热情似火的叫卖声中。
皮可飞快地经过那里,他几乎被自己奔跑的姿势绊倒。山就在不远处,矿区为了美化环境,在废弃的矿山上种满了牡丹,在细雨中看起来,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但皮可甚觉遗憾,要是杨稣来了就好了。
显然,皮可爱杨稣爱得有些糊涂,这种时候,还想着能和她一起看牡丹,真是不知好歹。
11
如果不算天上的飞鸟以及地上的蚂蚁,这世上最后一个见到皮可的人,应该是巷子里的老住户毛山。他已经很老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巷子里走一圈。他起这么早是为了捡垃圾,塑料瓶是他的主要猎物,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旧电器。
他经过皮可家的时候发现他家的门开着,皮可穿戴整齐,貌似准备出门。
天真冷,毛山簌簌地经过,忘了跟皮可打招呼。他只是想,这孩子不容易。
皮可高中毕业后跟着一位亲戚,帮供电局拉电线,经常爬上电线杆,树懒一样挂着。
皮可死后,毛山忽然想起,那天早上,皮可其实是在抽泣。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