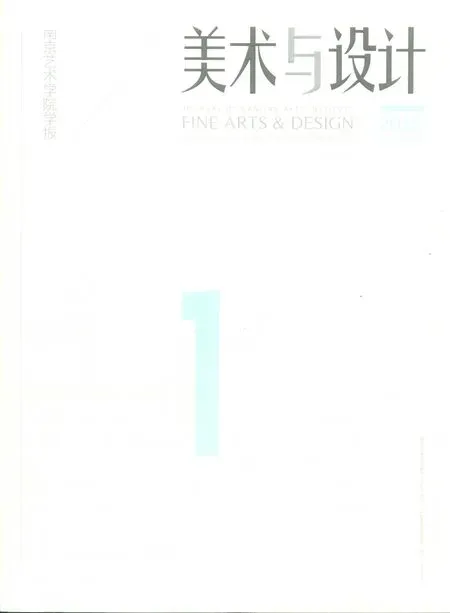从“潇湘八景图”到“纪游图”
——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关于画意转换的案例①
2016-08-08姜永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姜永帅(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从“潇湘八景图”到“纪游图”
——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关于画意转换的案例①
姜永帅(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 摘 要 ]“潇湘八景图”最初是北宋画家宋迪作为表达其政治隐情的无声诗而作,并不具有实景特征。在它流传过程中画意不断被误读,在元代吴镇眼里,它被视为描绘当地风景名胜类型的山水画,其笔下的《嘉禾八景》,成为一种表现当地风景名胜类型的“八景图”。这一类型的山水画经明代画家沈周的融合,产生出纪游图类型的山水画。八景图虽然经误读与转换发展成为纪游图,但后者并未完全取代前者。二者转换后又各自发展,不过,此后八景图已沦为一种程式,纪游图也逐渐走向更具实用性和功能性的旅游图册了。
[ 关键词 ]潇湘八景图;画意;转换;纪游图
中国山水画史在明代已被认为存在几处大的转折,这种认识最为著名的便是王世贞的论断:“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1]此言道出了明代以前中国山水画变迁之大局,这种变迁映射出山水画风格在画史上大的转变。大局之下,暗流涌动,促成大变局正是暗流的集聚。如果将一部绘画史视为其内部风格的变化史,那么每种类型绘画的流变可视为暗流,它们的兴起、演变、更替、消失、断裂或相互之间的转化构成了血肉丰满的艺术史。因此,探寻这些暗流正是艺术史学者的任务。在以往,某种绘画类型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较为引人注意,而不同类型之间的更替或转化,常被忽略,由“八景图”到“纪游图”的转化便是其中一个案例。
薛永年先生认为,纪游图起源于六朝宗炳在墙壁是所绘制的山水画。②薛永年.陆治钱谷与后期吴派纪游图.收录故宫博物院编.吴门画派研究[G].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47。宗炳仅在画论中提到自己游历后所作山水画,以便卧游。由于其画迹早已不存,在宗炳的画论以及南朝文献中未曾涉及对宗炳山水画面风格的描述,可谓迹已不再,意更难求。推测需要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更不能代替实证,故我们谈论它的起源最好以较为可靠画迹和翔实的文献为基点,从而理清它的直接来源。石守谦在题为《风格、画意与画史重建——以传董源溪岸图为例的思考》中倡导早期画史研究取风格与画意③石守谦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里提取出古人关于“画意”的观念的理解,他认为在郭若虚的观念里,“画意”还不仅仅是绘画科目的分类而已,而且还是某种特定意境的典型。人们一旦认识了这个意境典型,个别画家便可依其各自成就的倾向,溯其源流,形成历史性的理解。见石守谦,《风格、画意与画史重建——以传董源溪岸图为例的思考》,《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互证和互补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尤其在作品资料不足征信之时,容许画意的探求者跨过作品流失的断层,直接以文献为主,在文字上进行理解,这种弹性使其作为方法的魅力大为提高。中国的创作者实际上便相当依赖这个方法来进行他们与古代大师的对话。”[2]这一观察很有洞见,纪游图的产生存在着图像资料不够翔实,而文献记载较为丰富的类似情况,故我们可取画意与画迹互证之法,究其源流。
一、八景图的流传与误读
元四家之一的吴镇(1280—1354),绘有《嘉禾八景》,该作品描绘的是嘉兴周边的风景。嘉禾即嘉兴也,是吴镇的家乡。吴镇生于嘉兴魏塘,终老于魏塘。一生不求功名,半生处于贫困之中,其行踪大略不出嘉兴一带。高居翰称其为名副其实的隐士④[美]高居翰.隔江山色[M]北京:三联书店,2009:61.。《嘉禾八景》卷首题跋曰:
“胜景者,独潇湘八景得其名,广其传?惟洞庭秋月、潇湘夜雨,余六景皆出于潇湘之接壤,信乎其为真八景者矣。嘉禾吾乡,也岂独无可览可采之景欤?

图1 吴镇《嘉禾八景》局部 (36.9×850.9cm)采自高居翰《隔江山色》
吴镇所画的嘉禾八景不仅标出景点名称,并对部分景点做了介绍,例如,“武水幽涧:在县东三十六里武水,比景德教寺西廊幽涧井泉品第七也……”接下来的题跋仍旧是对嘉禾景点的描述和赞颂。值得注意的是,吴镇题跋中述及《潇湘八景图》,是宋代画家热衷绘制的潇湘名胜,其每一景都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在吴镇看来,世间不只有潇湘八景广为流传,自己家乡也有风景名胜,于是“闲阅图经,得胜景八”,并绘制出了具有一定实景感的《嘉禾八景》。这样看来,吴镇是以自己家乡的风景名胜为自豪而绘制的八景图。但《潇湘八景图》的原意并非是按照真实的景点进行描绘,而是取潇湘风景的诗意和政治隐情而绘制。显然,吴镇对《潇湘八景》的原意发生了误读,正是这种误读引发了风景名胜类型山水画的盛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纪游图类型的山水画。我们不妨先对《潇湘八景图》产生的语境做一番考察。
最早绘制《潇湘八景图》的是北宋画家宋迪(活动于11世纪),《宣和画谱》记载宋迪名下作品计31件,其中有《潇湘秋晚图》和《八景图》,二作皆已无迹可寻。宋代其他文献多称宋迪所绘为《潇湘八景图》,所以,《宣和画谱》所记《八景图》应是《潇湘八景图》。不过宋代文献对《潇湘八景图》最初的形式以及递变有相关记载。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记载: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晩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3]
苏轼《补注东坡编年诗》卷十七《宋复古画潇湘晩景图三首》有同样记载:
支员外郎宋迪,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湘山野录。长沙有八景台,宋迪度支工画有平沙落雁等名谓之八景,僧惠洪各赋诗于左。[4]

图2 王洪 潇湘八景图之一(23.6×87.5cm)水墨绢本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官网提供)
苏东坡的记载使我们大致了解到宋迪所绘这幅画的形式,宋迪画出了八景图,并未题名,是僧人惠洪后来分别在每幅画面左侧题诗。又,南宋赵希鹄著《洞天清录·古画辨》(约成书于1225-1264),载:“宋复古作潇湘八景,初未尝先命名,后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画人先命名非士夫也。”[5]由此可以看出,命名与题诗是后来“好事者”惠洪为之,这表明景点名称、诗与画本来是分开的。惠洪因画而作诗,他的题诗使画与诗结合,并产生了画、标题与诗一体的形式。
那么宋迪是否根据八景台而画八景图,宋代文献只有上述苏东坡诗文里“长沙有八景台”的一则旁证。东坡根据长沙有八景台而推测宋迪可能根据八景台看到的景点而绘八景图。明代嘉靖十二年刻本《长沙府志》有关八景台的记载:八景台,在府城西,宋嘉祐中筑。宋迪因作八景图,僧慧洪更名八境,陈付良复其旧,并建二亭与旁。清代刻本《长沙府志》也持相似说法,无疑沿袭明代。明清刻本的《长沙府志》可能均沿用了苏轼的相关记载。不过根据《长沙府志》的记载,八景台是一个建筑,可能是为观景而建。结合苏东坡的说法,至少在北宋嘉祐时期就有了八景台,问题是宋迪是否就是根据八景台所看到的风景而画八景图呢?他所作的八景是不是有实景感的作品,还是仅采用八景的名字来传达诗意?
姜斐德在其著作《宋代诗画的政治隐情》中,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诗文功底揭示出《潇湘八景图》隐藏的政治隐情。姜著认为,《潇湘八景图》最初是映射流放到潇湘地区宋迪、苏东坡这一圈子的文人。至于后来八景图发成为地方性的风景名胜,“在14世纪左右,为风景名胜命名已成为地方一种荣耀。”[6]同时指出:“从11世纪的政治性发展到后来的非政治性,并非是直线进行的,把这些主题诠释为‘美景’,在北宋结束之前就初现端倪,并与其他意义并驾齐驱。”[6]姜著的观点令人信服,宋迪的八景图在南宋代已广为人知,且“好事者多传之湘山野录”。以致祝穆在《方舆胜览》卷二十三介绍长沙郡的名胜时,将宋迪所画潇湘八景加以宣传。①[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二十三,湖南路[G].北京:中华书局,2003:410。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有王洪所绘《潇湘八景图》图2,王洪(约1131—1161)活动于南宋高宗时期,其《潇湘八景图》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潇湘的作品。王洪之作保存完整,画面仅见署名,没有其他任何题跋。姜氏认为,王洪根据惠洪的题诗而作,保持了宋迪原初的画面形式,画面不见题诗,仍保持了律诗的结构。有学者从命名与实指的角度分析,认为八景图只有“潇湘”、“洞庭”为实指,其它均为虚指。①周阅.潇湘八景的诗情画意——兼论中国绘画对日本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J].2008春之卷:170.冉毅:宋迪其人及潇湘八景图之诗画创意.文学评论2011(2):157。日本学者铃木敬指出:“完成的八景图没有必要一定与潇湘的实景有多大关系,哪怕是借云气的潇湘之地制作出八景,进而挑战水墨画的极限。”[7]本来,潇湘地区多水,常起云雾,变幻莫测,总带有一种朦胧的诗意。正是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文献中称“僧慧洪更名八境”,与其说是根据八处景点而绘,不若说画面表现了八种情境。王洪所绘八景同样很难与具体的地点相对照,若不是画面存在的暗示(如大雁),的确难以与具体的诗文进行对读。再结合八景图的名称“平沙落雁、远浦归帆……渔村落照”分析,这些名字本身就没有实指的地名,并带有时间和运动的特性,这和后来流行的表现地方名胜的八景图是不同的。结合王洪所绘《潇湘八景图》,便可明了宋迪所绘八景图也是没有实景感的组画,最初表达的是诗意的情境,其中夹杂着宋迪对政治与流放的种种隐情。正是这种没有明显实指特征的作品,再加上宋迪并非只作了一组八景图,因此,在南宋时,人们已难以区分宋迪所作画的名称,更不用说所隐含的政治隐情了。
《宣和画谱》不仅记载宋迪绘有《八景图》,同一条下还记载御府收藏有宋迪《潇湘秋晚图》,按《宣和画谱》如此记载,二者应不是同一幅作品。此画同是以潇湘晚景为创作对象。
又,苏东坡《补注东坡编年诗》、苏轼《施注苏诗》补遗,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二均收录相同的东坡作宋复古(迪)画《潇湘晚景图》三首:
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
落落君怀抱,山川自屈蟠。经营初有适,挥洒不应难。江市人家少,烟村古木攅。知君有幽意,细细为寻看。
咫尺殊非少,阴晴自不齐。径蟠趋后崦,水会赴前溪。自说非人意,曾经入马蹄。他年游官处,应话剑山西。[8]
《潇湘秋晚图》在宋代仅仅出现在宣和画谱中,而《潇湘晚景图》多次出现宋代文献,故疑二者应是同一幅画。前文所引两处东坡诗分别对应这两幅画,第一处东坡注明:“宋迪度支工画有平沙落雁等名谓之八景,僧惠洪各赋诗于左”的按语,便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东坡与宋迪二人常有诗文唱和,且宋迪之作其画意东坡大都能解。因此,东坡的诗文成了理解宋迪绘画含义的重要注脚。但到了邓椿的时代,已将八景图视为晚景了。宋代邓椿的《画继》卷六所记:
“宋复古八景皆是晩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后之庸工,学为此题,以火炬照缆孤灯映船,其鄙浅可恶至于形容不出而反嘲诮云,不过剪数尺皂绢张之堂上,始副其名也。可训之作悉无此病。”[9]
邓椿《画继》作于南宋初年,相去宋迪作《潇湘八景图》50年左右。但他所见无论是《潇湘八景图》还是《晚景图》都以为是晚景了。这也说明从画面来看,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并不具有明显的实景特征,与《潇湘晚景图》画面风格相似。但是“好事者”惠洪的题诗及其命名却使《潇湘八景图》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标题、诗与画一体的形式。
所以两百多年后,八景图当初所表达的意图和政治语境早已不复存在,在画家吴镇那里,《潇湘八景图》便成了只剩下描绘长沙八景名胜的山水画了。吴镇的误读,致使原来表达诗意和隐情的《潇湘八景图》彻底转换成为风景名胜类型的山水画。去掉了八景图最初的表现个人情感的隐喻涵义,而成为侧重于观者观赏的地方名胜山水了。使故曰:“胜景者,独潇湘八景得其名,广其传……”。但是,这种以标题、诗与画一体的形式却在吴镇《嘉禾八景》的得以继承。
元末明初也有十景图之类的画作,但这些作品也是没有实景感的作品。陈汝言所作《虎丘十景图》,未见传世,仅见收录于明代袁华辑《玉山纪游》,诗和序的作者是元末的顾德辉(顾瑛),序云:
游虎丘杂咏诗并序:至正十一年(1351)春,正月七日,余与吴兴郯九成、龙门琦元璞、匡庐陈惟允泛舟过虎丘,时积雪弥旬,旭日始出,乃登小吴轩,冯高眺远,俨然白银宫阙在三山玉树间,兴不可已,遂留宿贤上人松雨轩数日。由是得历览山中清胜,乃赋小诗十首,以纪斯游。陈匡庐且能一一写图,求诸作者题识,余先书诸诗云……。”[10]
游玩之后,顾德辉与友人共作诗十首,陈汝言(匡庐)根据诗意绘制出十幅画,并求诸作者题诗。可推测出陈氏根据每首诗的典型意象,绘制出具有象征性的作品来,应与表现诗意的《潇湘八景图》相类似。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陈汝言所绘《荆溪图》,日本学者吉田晴纪通过对该作品构图分析,认为陈氏是沿袭了元代山水典型的构图方式,由此推测出陈氏作品同样也是没有实景感的作品。②[日]吉田晴纪.关于虎丘山图之我见.故宫博物院编.吴门画派研究[G].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67.虽是一则旁证,但根据元代整个山水画表现方式,以及前代流行的八景图的特征来看,这一看法应是合理的。
从画面看,吴镇《嘉禾八景》选取有代表性的景点进行着力描绘,并且在每个景点旁边题写说明性文字,这种做法已经不同于《潇湘八景》或以及同时代《虎丘十景图》之类以诗意为表达的绘画作品,而是倾向于实景感的作品。陈汝言的《虎丘十景图》可以看作以诗意为表达对象的八景图类型的延续,画面的客观对象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心中的诗意。而吴镇《嘉禾八景》更倾向于关注景点本身的实地特征,并往往以凸显当地名胜的标志性景点作为描绘对象。然这类描写当地名胜的作品在元代并没有兴盛,而是到了明代蔚然成风。这种对原初画意背离的八景图也逐渐转换成纪游图类型的山水画。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乃吴门画派开山人物沈周。
二、沈周与纪游图的形成
明初画家王履(约1332—1391),苏州昆山人。画有《华山图册》(1383年左右),40幅,111首诗,记8帧,自题跋14帧,合66帧正页。《华山图册》画面上并没有题跋游记内容,但王履作了8篇游记附在其后。另外,《华山图册》40幅是分景点而描绘,彼此连接起来并不是一个整体,也就是空间上不具有内在连续性,这与之前流行的八景图是一致的。该图册每幅一景,且皆有名称,如《上方峰图》、《苍龙岭顶图》,这些图均制名指实,并有诗文题跋其上。王履早年师法南宋画家夏珪,因多次游历华山,被华山山川美景所吸引,在绘画上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而已”。虽然王履提出师法自然之说,但笔法仍然是南宋院体的笔法。高居翰以“他熟读经书且擅长诗文”[11]将其归纳为业余文人画家阵营。以他业余文人的身份采用南宋院体的笔法画山水,这在中国画史上是较为少见的。若就画面视觉形式来讲,王履的《华山图册》远比宋人院体画家更具视觉真实性,也不同于《潇湘八景图》较为抽象性的命名画作。这种视觉真实并不是宋人的写实,或“穷理尽性”的特点,它是具有视觉的在场性。在王履提出的忠实自然的言论里,我们仍可看出:“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者,形乎哉?”正是因为他对形的关注,才使他的画面区别以往宋、元画家以诗意来表现八景图命题的泛泛之作,使画面有了某种坚实的地貌特征。
王履的《华山图册》可视为沈周作纪游图的先声。他与沈周同是苏州地区人,但尚无文献或资料表明沈周曾看过或临摹过往王履的《华山图册》,不过与沈周关系密切的王鳌以及祝允明对该作品皆有称赞,王鳌将《书王安道登华山图》收录其《震泽集》,祝允明在《怀星堂全集》也称:“……沧州武将军家藏得其华山图子凡数十段,诗文百首,首尾灿烂整完,发卷便如携人到异境……”虽然沈周在绘画上的取法依然保持元代文人的传统,明末李日华评沈周说他中年学黄公望,晚年“醉心”吴镇。但王履的《华山图册》在苏州地区文人圈子所产生的影响,可视为沈周作纪游图的背景。《华山图册》呈现出在场性的视觉特征以及标出每个景点,并题诗的画面形式,均是沈周作纪游图的图像传统。
沈周中年时期就开始作名胜山水之类的八景图,成化九年(1473)沈周作《奚川八景图》,可惜现已不存。据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卷一记载,他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11月3日①月份为中国夏历纪年,即阴历。看到沈周的两卷《奚川八景图》作品,李日华以鉴赏家的眼光对该作品进行了简要描述,使我们大略知道作品的风格:“沈石田奚川八景,笔法仲圭、子久之间。”[12]所幸的是,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卷十载有《石田翁画奚川八景图歌》,文中谈到这幅画的主顾,“石田翁画奚川八景图歌,奚川八景图,石田翁为七世祖理平公及其兄理容公作也”。[13]沈周在卷末也做了题诗,其诗后四句道:“武肃之孙白玉双,名此八景扬芬芳。索赋绘图表清绝,吟窗阁笔怀潇湘。”并作跋云:理容理平昆玉过予有竹居,持匏庵诸公奚川八景题咏,乞予补图并系拙句,时癸巳年夏日也。”沈周为“理平、理容”两兄弟所画,故为二卷,此作乃是根据匏庵(吴宽)诸公的咏奚川八景的诗歌所补图,可知,沈周此作乃根据诗意而画,并且诗的最后一句写道“吟窗阁笔怀潇湘”,“怀潇湘”说明怀的是《潇湘八景图》,也表明,在沈周的眼里,潇湘图也是风景名胜类型的山水了。沈周作此画尚处于他艺术的早期,这些诗文显示,此画应是一般的意象山水,其笔法介于“仲圭、子久之间”,更多的是因袭前人八景的模式,而不具有实景性质的山水。
虽然王履的《华山图册》确立了纪游图画面形式和视觉特征,但是明确地使用“纪游图”这个名称并最终形成一类型的山水画始于沈周。产生纪游图的因素可能很多,若从画意来看,纪游图实则八景图之类的名胜山水发展而来。吴镇的误读可视为由表达政治隐情的八景图转换为去政治化的风景名胜。这使八景图不再充当诗言志的功能,不再隐晦地传达画家不满政治的情怀,而成为象征地方名胜的图像标志了。纪游图所表达的画意,也正是对这些景点的游历,借助绘画、游记或诗文表达自身的感受。前者着重点在于诗意的传递,后者则强调画家的感受。若从绘画的内部②绘画的内部指的是形式、风格、笔法、结构等与绘画本体有关的因素。来看,描绘出地质结构和强调视觉在场性的纪游图风格以及在景点上标出地名的做法即是从八景图之类的名胜山水演化而来。在纪游图类型的绘画风格中,保留了八景图这类名胜山水对具体景点的表现,只是不再是诗意诉求,而是近乎白描式的对具体地点的说明性描绘。并继承了八景图题写地名与诗文的传统。另一方面,描绘地质特征这个传统也可从王维、李公麟的绘画进行观察,他们皆从古代地图中得到了滋养。贝特霍尔德霍尔德·劳费尔通过分析王维《辋川图》,认为唐代山水画大师的作品“从当时高度发展的地图学中得到很强烈的动力”,又说王维的作品“目的不是表示任何山水景观,而是要表示王维珍爱和长期观察得出的辋川地形”[14],此说王维“不是表示任何山水景观”未免矫枉过正,但却观察出了中国山水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忽略从地图层面考虑山水画的面貌问题。无独有偶,李约瑟在论述古代中国地质时引用《山庄图》作为中国山水画最为生动的地形图以及再现一部分滚动的画卷理解珍贵的花山崖。他认为,该图可视为一件精妙呈现了揭露斜背拱的白描。①[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第五卷,地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258.另外,在作品上表示出景点地名也可能受到地图传统的影响,南朝王微在《叙画》里已谈到绘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镜阜、划浸流”正表明地图的特征。《辋川图》是否在每个景点标名字,仅凭唐以后的模本不足征信。但李公麟 《山庄图》最早的模本皆标示出每个景点的地名。因此,从绘画内部来看,这些视觉特征和形式皆可视为表现地质结构和标示地名相结合的传统。并非一定要说沈周就一定受到王维、李公麟或地图制作的影响,而是中国绘画也存在能够表现出地质特征的这一图像传统。在明代沈周所作纪游图那里,又呈现了出来。若从的绘画的外部看来,文人的交游与诗画唱和,虽然渊源可以追溯到“兰亭雅集”甚至更早,宋代的“西园雅集”,元代“玉山雅集”,皆负盛名。但到了明代,雅集风气尤盛。尤其在苏州地区,雅集、送别成为文人之间生活方式。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沈周画下了大量苏州附近的山水名胜。自元代之后,八景、十景等成为各地方志介绍当地风情时的荣耀,这与元代后流行绘制八景图、十景图是一致的。这些地方名胜,往往是交游、雅集的理想场所。吴门地区自古以来,人文荟萃,风景名胜不胜枚举,雅集、郊游风气之盛与这种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

图3 沈周《白云泉》局部 绢本设色37.3×936cm 采自高居翰《江岸送别》
沈周约从 1470年代开始作纪游图一类的作品,成化十一年(1475)作《纪游图卷》(20段)。成化十四年与友人吴宽、史鉴等游苏州西山,吴宽作《游西山记》,沈周作《游西山图卷》,同年又作《虞山纪游图》。1480年代后,又作《虎丘图册》、《白云泉》等根据苏州周边名胜而绘的作品,《白云泉》以写苏州近郊名胜为主题,不仅勾勒出了坚实的地质结构,而且在每个景点旁用细小的字体题写上名字,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李公麟所作的《龙眠山庄图》,除此之外,描绘出地质结构的坚实画法也可比《山庄图》。高居翰指出:“这幅构图严谨,笔法坚实的画,却是以通俗纪实的方式来呈现苏州附近的名胜……简单地说,这幅作品在处理的手法上,似乎明显地异于我们常见的沈周的大部分画作,其个人的感情成分较少,供大众欣赏的意味较浓。”[15]高居翰或许对纪游图的文献不够注意(纪游图是明代文献和作品一个专有名词),不过他对这类作品的分析十分有见地,明确指出它们的视觉特征。这种视觉特征的描绘还可以从沈周在《吴中山水全卷》题跋中得到印证:
吴地无崇山峻岭,有皆陂陀连衍,映带乎田隅。若天平、天池、虎丘为最胜地,而一日可游之遍;远而光复、邓尉,亦一宿可尽。余岁稔经熟,历无虚岁,应日寓笔,画者屡矣!此卷其一也。将涓流之他方,亦可见吴中山水之概,以视其未游者。画之工拙,不暇自计矣。②见沈周吴中山水全卷题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岁稔经熟,历无虚岁,应日寓笔,画者屡矣!”足见沈周对这些景点特征烂熟于心,但值得注意的是,沈周提到:“亦可见吴中山水之概,以视其未游者”,此语道出了这《吴中山水全卷》可以充作导游地图的作用。此时,由宋迪所开创的本以表达政治隐情和诗意的《潇湘八景图》,到了元代吴镇的笔下,俨然转化为描绘风景名胜的八景图,经过沈周对这些主题的有目的的运用,最终由风景名胜转化为描绘实景特征纪游图类型的山水画了。
三、纪游图的一个经典案例:沈周《游张公洞图卷》
除雅集盛行外,在明代,旅行也是文人重要的文化活动。沈周便是在晚年游了宜兴的张公洞,时间是在1499年3月,沈周客居宜兴吴大本家,二十一这天,在大本的倡议下,二者理舟载酒,游张公洞。游览后,根据游览所见作《游张公洞图卷》(图4)。该图可以说是成熟的纪游图作品,有很强的实景地质特征),并在卷末,沈周题写了上千字的游记和诗文,因此,此卷可视为典型的纪游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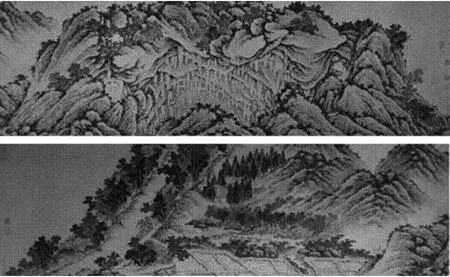
图4 沈周《游张公洞图》翁万戈藏 采自《艺苑掇英》第34期

图5 沈周《游张公洞图》卷尾题跋 翁万戈藏 采自《艺苑掇英》第34期
根据沈周的描述,(图4)张公洞在一个小山上,很隐蔽。“其山于群山最下而小,计其高不过二十仭,心甚易之,岂灵区异壤能结乎是哉。冉冉曲经田胜,间三里许乃抵,已暮,亟由林麓左行,拆而北二百步,路次临一穴,甚深晦,其唇有杂树蔽亏,人谓此洞之天窓也。转及山椒,则洞口在焉”①见图5沈周《游张公洞图》题跋文字。。这几句话的描写我们得知,张公洞有一洞口和一个天窓,二者均并不容易找到。笔者专程去张公洞实地考察了一番,张公洞的位置结构一如沈周的描述。无论是站在远处,还是近处,甚至在洞口外几米处就难以看到张公洞,甚是隐晦,只有进入溶洞才能看到内部奇怪的岩石结构。沈周游记中写道,由于天气“暝色渐翳,迨无所睹”,当天沈周并没有看到张公洞的景象,而到了次日借着日光,“日光下映,四顾了然”沈周终于看到了洞里面岩石的奇观。在沈周的画面中,张公洞被安排在首段的中间部分,占据画面的大部分面积,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在画面右边拱起的部分,有一洞口,空白处,沈周用小字标出“洞口”字样。自右向左,沈周把游览的顺序安排在一幅长卷之上。溶洞内部的钟乳石一个个倒悬着,可结合沈周游记的文字进行对读:“乳流万株,色如染靛,巨者、么者、长者、缩者、锐者,截然而平者、菡萏者、螺旋者、参差不侔,一一皆倒。悬俨乎,怒猊掀吻,亷牙利齿,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悚,乳末余膏,溜地积为石,数长躯离,立兀兀,色揉青绿可爱,西壁下,作大裂斜而衍幽,而窅内多流石。”②见图5沈周《游张公洞图》题跋文字。图文对读,确有身临其境之感。怪石结构描绘得十分清晰,有着在场般的视觉真实特征。游览的过程被沈周自右而左的安排在画面上,体现出了游记的时间性特征,这是纪游图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游记的结尾,沈周又作了首诗,进一步抒发了游览的情怀。另外,沈周笔下的纪游图有多景点也有单独表现一个景点,但无论多景点还是单个,多数情况下,沈周采用一种整体的表现手法,将诸多景点表现在一个空间连贯的整体之中,保证空间上的一体性,并在每个景点上用小字标示出其名字。这种画面形式不同于王履的《华山图册》单景点的单幅作品表现方法和形式,而更接近于李公麟《山庄图》连贯的空间处理方法。沈周所作的《白云泉》即是一幅多景点空间一体的代表作品,《游张公洞图》虽然只描绘张公洞这一个景点,但沈周以长卷的形式把周边的山势画进了画面,仍然确保了内部空间的一致性。当然沈周也有册页形式多景点单幅的纪游图,如《东庄图册》等,不过这种将多个景点整合在一起形成内部一致空间的做法可视为沈周对纪游图形式的一种创造性贡献。
纪游图仍属于绘画艺术。虽然这一类型有明确的地质特征感,但还不是纯粹的地质描绘图,当然也不同于古代的地图。郭亮通过大量的例证和比对指出,在明代以利玛窦(1582年来华)为代表的传教士将西方地图传入中国前,中国制图的传统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③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2.因此,沈周纪游图可以排除掉西方带来的地图的影响因素。地图的目的和首要特点是尽可能准确的传达地形信息,它通过观察和测量按照一定的比例绘制而成,尽可能高度符号化,减少形象与想象的空间,中国古代的舆图虽然略有变化,但同样也是以此为目的。而纪游图则不然,它仍是通过绘画、游记或诗文表达个体对游览景点的感受,虽然有强烈的实地地形感,但绝非相对客观的地图语言系统。它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传达明确而客观的信息,而是画家本人的观察与感受。因此,纪游图仍属于艺术语言的系统。
四、余论
沈周之后,纪游图在吴门地区蔚为壮观、盛极一时,深受文人追捧。明代“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尤其热衷于纪游图,王氏自身不作画,而喜旅行、善作游记,尝请陆治、钱谷为其作纪游图。陆治为王世贞画纪游图,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为止。④陆治1573年为王世贞所作的《游洞庭图册》,王氏题跋曰:
余以壬申(1572)之秋九月游洞庭,而陆丈叔平亦随诸少年往,盖七十七矣,而簪履在云气间若飞。归日始草一记及古体若干首,以贻陆丈,存故事耳。居明年(1573)之五月而陆丈来访,则出古纸十六幅,各不一景,若探余诗之景不重犯者而貌之。其秋骨秀削,浮天渺弥,的然为太湖两洞庭传神无爽也。[16]
从上述文字来看,陆治已七十七岁,仍然同王世贞等诸少游览洞庭,游后,王世贞根据游览景点作古体诗若干首,而次年五月,陆治画出来游洞庭的十六幅画,王氏睹之曰:“的然为太湖两洞庭传神无爽也”,从而促成了这次旅游后的文化交流活动。不过,陆治纪游图的绘制一方面根据自己游览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有王世贞的诗作为诱因。这种合作和元代陈汝言所作《虎丘十景图》情况相似。根据题跋可知,十六幅画是单个景点的独幅作品,王世贞热衷于多个景点的纪游图。钱谷与其弟子还为其绘制了多达八十二幅的《纪行图册》,同样也是单幅景点的作品,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纪游图流行多个景点的单幅作品。
这种多景点的纪游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导游图之类的图册了,偏离了艺术语言系统,成为较为庸俗的供大众查看旅游地点的旅游指南了。纪游图虽由八景图的画意转换而来,然八景图并非完全被纪游图所取代,而是在明代以后仍然保持美化地方风景名胜的诗意的特色。只不过明代后期的八景图类型的山水已经沦为了一种程式。纪游图虽然由王履开其端倪,沈周创造出新的视觉语言和形式,但随着多景点纪游图的兴盛以及过于往实用性方面的发展,纪游图最终偏离的艺术语言系统,成为以说明和传递信息为主要功能的导游图册了。这便是两种类型的山水画在画史上发生转换、融合,产生新类型后又各自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89.
[2]石守谦.风格、画意与画史重建——以传董源溪岸图为例的思考[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胡道静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14.
[4][宋]苏轼.补注东坡编年诗,卷十七[G]//四川大学古籍研你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5.
[5][宋]赵希鹄著.洞天清録[G].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初集,第9辑.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2013:276.
[6][美]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M].北京:中华书局,2009:218.
[7][日]铃木敬.中国绘画史[M].上卷吉川弘文馆昭和56年(1981):274.
[8][宋]苏轼.苏文忠公集[G]//宋集珍本丛刊:第二十一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755.
[9][宋]邓椿.画继[G]//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16.
[10][元]顾瑛撰,袁华编.玉山纪游[G]//游虎丘杂咏诗并序.四库全书:第13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87.
[11][美]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09:4.
[12][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M].屠友详,校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57.
[13][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十[M]. 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12.
[14]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9.
[15] [美]高居翰: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M].北京:三联书店,2009:86.
[16][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9.
(责任编辑:梁 田)
[ 中图分类号 ]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1-0047-07
收稿日期:2015-10-23
作者简介:姜永帅(1983-),男,河南南阳人,江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艺术史与考古。
基金项目:①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与研究”(项目号14JZDH039)阶段性成果之一。闲阅图经,得胜景八,亦足以梯潇湘之趣笔而成之图,拾俚语,倚钱塘潘阆仙、酒泉子、曲子寓题云,至正四年(1344),岁甲申冬十一月阳生日,画于橡林旧隐梅花道人镇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