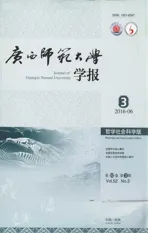写文化:侗绣服饰图案在当代绘画艺术的文化表现
2016-08-05陆丽娟
陆丽娟
(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写文化:侗绣服饰图案在当代绘画艺术的文化表现
陆丽娟
(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侗绣发展和演变中既有口传身授的传承风格,又有丰富多姿的地域风貌,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侗绣在不断地沉淀、延伸、嬗变,它在造型、色彩、构图上不断完善和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当下世人所见、侗家特有的传统民族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侗族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体现出其特有的民族艺术精神。从侗绣图案提取精髓融入当代创作,不仅是对中国绘画文化性的提升,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作出一定的文化选择,真正在人类学研究体系中体现出“写文化”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当代绘画;侗绣图案;文化表现;写文化
作为艺术人类学一直关注的民族文化传承延续问题,绘画艺术与民族传统文化间所衍生出的文化新图式和新样式,逐渐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推广延伸的重要领域,虽然不可避免地运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神话等领域的语义元素阐释绘画艺术的历史价值,但从艺术形式中寻找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对人类学研究领域来说是有极大裨益的。因而,在目前话语困境和研究困境等情形困扰之下的绘画艺术研究,其表现价值研究需要寻找既尊重民族精神又遵循艺术规律的艺术作品,还要符合艺术家创作的性情,这对挖掘民族艺术的现代性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民族性都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写文化”是美国克利福德和马库斯合作编辑出版的民族志论文集中的关键词,这些相关论文的撰写方式与视角都极其重视文化的诗性和社会学的政治性,重新反思了传统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成为人类学界极为重要的一次学术讨论和观点碰撞。本文主要援引“写文化”从语境上寻找“有意义的社会环境下汲取资源并创造有意义的社会环境”[1](序言)5,通过选择分析侗族服饰的形态,特别是其在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中的表现形式,感悟浓郁的习俗和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探寻其在绘画艺术创作中的内在规律和文化表现,从而为中国当代艺术和侗族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历史悠久,分布面广。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桂北山区,是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地,是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也是全国五个侗族自治县中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全县共有3个镇、12个乡,总人口36.7万人,其中侗族人口近20万人,占57%,侗族以外,有汉、苗、瑶、壮等民族。深入侗族地区考察就会发现,侗族的传统文化深厚而完整 ,当侗族青年男女围坐在灶堂边倾听老人“摆古”时,即是在领受做人的道理;当象征族群图腾的鼓楼响起鼓声时,即是宗族祭祀的开始;当芦笙吹响时,即是踩堂舞的热情邀约;当看到延绵街巷的百家宴时,即是族群举行红白喜事仪式之时。几乎每一位生活在侗乡的人都置身于固有的传统里,受到传统的约束和规范。世代的经验积累和文化积淀,使侗族地域俨然一个传统的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又不断演变为生动而鲜活的民俗生态场域,由此形成了侗族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
关于侗族的族源一般认为是广西土著民族,其先民或为古代的骆越人,隋唐时期称为“僚”,宋代称为“伶”,明清时称为“峒”,建国后正式定名为“侗”,包含老侗、佼侗、禅侗三个支系。各支系传统服饰的形成,不仅具有传承性,而且还有借鉴性。恰如侗族与其他民族繁衍生息的生命史一样,侗族与苗族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关系也十分紧密,并呈现了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现实状态。侗族与苗族的审美意识,共性之处在于共同崇尚群体美和女性美。侗族崇尚智慧、秀美,具有和谐美和喜剧美;而苗族崇尚冲突美和悲剧美,其中隐含着苗族迁徙中的悲壮历史。此外,侗族服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侗绣,侗族服饰的很多色彩、造型都需要通过侗绣这一载体来实现。侗绣的主要刺绣技法为挑花和织锦,色彩鲜艳,造型独特,题材广泛,涉及生活、自然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为侗族服饰的审美取向提供了可视的实物载体。
一、侗族刺绣工艺的传承与现状
侗族刺绣工艺历史悠久、古雅质朴,主要出现在侗族人民所穿戴的围裙、背带、鞋面、肚兜、手帕、衣襟、袖口、裤脚等日常物品上。侗族先民擅长用大量绚丽多彩的织绣图案来隐喻历史、装饰用物、美化生活,绣品工艺实为口口相授的一种文化传承,绣品不仅作为民族历史的见证,也具有日常实用功能,还可以作为定情信物、祭祀贡品、宗教法器等礼仪活动的重要器物。从古至今侗族刺绣一直是侗族特有的文化事项,同时也是侗族人民情感与信仰的物质寄托,更是整个侗族群落思想和审美理念的文化再现,成为集实用价值与美学体验融为一体的传统民族文化工艺。
目前,全国各县区都利用国家政策积极筹建生态博物馆,这为各地区各民族原生态的艺术和文化提供了有效的传承模式。笔者为了更好了解侗族刺绣工艺的传承情况,选择了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乡作为田野考察的区域。由于民族聚居的昌盛发展以及当地侗族人民对于传统文化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乐乡的民俗文化生活面貌保留较为完整,时至今日侗族服饰、刺绣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艺术表现手段经过历史的积淀和现代化进程,依然呈现出具有浓郁民风和地域特色的艺术面貌。
侗绣图案艺术在民间的生态现状不容忽视。笔者一行采访到了同乐乡远近闻名的刺绣世家——覃家,覃氏一门颇有家学渊源,上至耄耋老人,下至总角小孙女皆善女红针黹。德高望重的覃奶奶更是有口皆碑的剪纸能手、刺绣大师,其儿媳杨甜和韦清花两位绣娘的绣品亦是栩栩如生。传统的侗绣需要先用硬纸板剪出许多妙趣横生的动植物图样,然后依照图样运用不同的针法充分填绣,直至将图样覆盖,再把刺绣完整的图案缝制到衣物上,就算完成了一件侗绣的全部工艺。看似简单的几个步骤,却凝聚了手工艺者的巧思和匠心,他们每日精进自身技艺从而成就一件件精致久远的侗绣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覃家自主筹资修建的侗绣艺术活态展览室,整栋楼为独体仿木质吊脚楼的四层建筑,北靠乡镇主要交通要道,南朝村委会主楼以及村民文化活动广场,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其中,家庭居住与活态展览室并生在整栋楼里,除几个展厅设置为不同的独立房间外,非展示区也放置着生动而丰富的生活用品,让每一位观者行走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新侗寨浓郁的生活气息。笔者像所有外来闯入者一样,静静关注并记录图案生动、色彩冲突、做工精致、纹样繁缛的侗衣、背带盖以及绣花鞋。从各地艺术家留给展览馆的油画、国画和水彩画等作品就可以感知,此地曾有许多游人造访并留下印迹。如今,近九十高龄的覃家奶奶养成了在人多热闹时徒手剪纸和展示刀工的固有习惯,她的身上综合体现了侗族妇女的勤劳智慧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孜孜追求,生活常态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她们对民族文化生活饱含浓郁情感的物化再现。经过时间纵向对比和空间的横向比较,侗绣之美由原始朴素的古雅之美流变至当下的色彩和谐华丽含蓄之美,为其转化为艺术创作的题材和对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侗绣图案的基本艺术特征
(一)祈福吉祥的图案寓意
侗族织绣工艺的图案多取材于自然界中的花、鸟、虫、鱼以及人物故事、神话传说、风土民情等。这些图样有的直接再现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民族风貌,有的间接表达人文思想、情感祈望,还有的是对生活、生产、习俗的抽象概括。侗族刺绣中展现的花卉果实图案种类繁多,有桃花、李花、石榴花、杜鹃花、油茶花、油桐花、寿桃等。侗族人民不仅对于花卉蔬果饱含爱慕与向往,对于动植物也有着独特的崇拜情结。在侗绣中就有大量表达动植物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绣样,例如榕树纹、鸟纹、十二生肖纹等纹案。
侗族人民的宗教所秉承的生命万物的同根同源性,在绣品上可以窥见。例如,侗族人信奉“风水树”,把它看作吉祥和生命的象征,如同普照万物的太阳。因此其枝叶就以太阳的形状绣在背带上向外散发出光芒。其次,由于侗族长期逐水而居,他们热爱清澈的水,也喜爱活泼的鱼,认为鱼是最洁净的动物,所以把鱼绣在衣物上意指“人丁兴旺”。再如,对饱满的石榴和葫芦,侗族也取中原文化中“多子多福”之寓意。而侗族日用工艺图案表达的理想愿望具有较强的吉祥寓意,例如“四菜一汤”式的“五圆图案”,传说是太阳和星星,中间较大的是太阳,四角是星星,图案四周还绣以百花和鸟类,寓意太阳和星星给万物带来生机。这些图案大多绣在小孩的背篼、衣服、帽顶上,旨在期望孩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仅在绣品上的“双鱼抢宝”、“鸾凤朝阳”、“金鸡含石榴”等图案,就能说明侗族人民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图1 侗族幼儿帽子

图2 侗族女装
(二)绚丽缜密的色彩构成
侗族刺绣作为一种日用工艺,是通过在实用品的图像造型上将线条、形状、色彩加以美化、装饰,使其产生美的感观效果。绣娘们经个人的想象和经验将预设的色彩、线条、形状,主观能动地进行美化并排列组合,最终构成一幅完整、和谐的绣面,其图案的造型、色彩和纹样都具有艺术美的表现力,图案的构成也十分严整、细密且重视画面整体协调性。大部分侗绣图案都围绕一个主体图形,分别以对称或不对称的方式附加图形,构成一幅完整协调的整体图案。以背带上绣的花样为例,其画面主体都呈现太阳或突出的几何纹样,围绕这个纹样中心绣饰以花鸟、星辰、云霞等吉祥物象,具有极强的原始趣味和故事情节。
三江侗族的刺绣色彩斑斓、对比强烈、变化多端、活泼艳丽而不平庸落俗,灵秀聪慧的绣娘们巧妙地运用色彩搭配,以绚烂缤纷的强烈对比色相烘托主题的空间气氛。三江绣品的色彩典雅自然,对比之中暗含统一,是绣娘们观察自然世界的各种生态颜色后所作的艺术概括、取舍和夸张,再依据个人的视觉印象和审美习惯有意无意地进行色彩搭配的结果。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在研究文化心理学现象时,用“文化-心理结构”来解释理性和理性形式在创作中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况、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475。他的观点印证了图腾信息与文化心理的内在影响力。因此,绣娘们常常选择欢快、喜庆、跳跃的色调,如大红、桃红、橘黄等,这些温暖明亮的色彩在侗绣作品中得以大面积使用,而后将之与绿色、紫色、蓝色等色相对比配置,主观能动地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既凸显了靓丽的装饰效果又给人以欢愉、吉祥、热烈的视觉感受。侗族绣娘们在天然的生存环境和民族情感意识的影响下,善于大胆使用高纯度强对比的色彩,使其在黑色的底布上显得格外鲜艳、华丽。可见,侗族刺绣图案中的色彩构成,具有对比强烈又和谐统一的根本规律,几乎跳脱了自然界中原始事物的本来特征,使它转变为纯粹的色彩情感之信息符号,也体现出侗族人民充满了大自然一般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三)乡土情怀的审美倾向
侗绣产生于淳朴、善良的民族土壤中,它既精致饱满、明艳热烈又极富原始野趣,具有质朴、细腻、和谐、俊丽的艺术特征,体现了侗族人民特有的审美意识和必然的乡土情怀。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侗绣图案表达了侗族先民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审美理念,并构成了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艺术都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只有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且真实地、艺术地表现生活的作品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侗绣图案就是这样根植于民族生活的土壤,用艺术再现了侗民的生活情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
侗绣艺术是主观个体对客观对象的一种主观反映形式下审美意识之集中体现,它表现了侗族人民丰富的社会生活、心理特征、思想感情等。当今侗族地区流行的刺绣图案都极富民族特色,鲜明地反映了侗族传统审美意识中的群体意识、平和理念和多神崇拜性。例如,构图的设置、色彩的搭配都依照美的法则形成一个完整的纹样图案,即是侗族民族群体意识的反映;侗绣图案的含义并没有很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大都表达绣娘们沿袭下来的审美意愿,画面整体基调都是和谐温暖、吉祥如意的,凸显其古朴优雅、温情脉脉的平和理念;侗绣图案还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意识,例如鱼的抽象图案和手牵手且歌且舞的花边图案都表示了对祖先的敬仰和纪念;侗族刺绣艺术在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都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特质,丰满地展示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意识以及民族性格的精神面貌,巧妙体现了农耕文化中的乡土情怀与现代社会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不谋而合的文化精神。英国学者莱顿就如此解释文化在形式审美意识下发挥的作用,“文化常常决定什么是一个对象的‘特征’,而且人们可以假设艺术风格是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有形的形式来揭示与展现这些特征。”[3]197不难看出,侗族艺术的审美取向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宗教意识,同时还蕴含着浓郁的艺术文化情怀。
侗族与自然、与神灵相处如此和谐,得益于侗族在社会群体的规模较小,社会存在于部落村社中,其组织行政系统还未分化独立出来,村社头人像家长一样;也得益于本民族的习俗和自然法则管理村社各种事物,这种社会关系和结构具有高度的群体一致性和原始集体主义性质,同时又包含着严肃的约束性。而侗族服饰一如既往地沿用族群长期传承下来的神灵形象和自然风物,以特有的集体力量共同生活以维持和延续民族的生命,其中,集体族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侗绣图案在当代绘画中的应用及文化表现
(一)侗绣图案的文化转换特质
中国民族文化为现代绘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民族元素对当代中国绘画的发展具有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我国部分学者和艺术创作者都意识到,绘画艺术可以从民族图案中汲取养料,融入民族地域文化元素以获得文化人文价值的延续和艺术图式上的突破。只有把握当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性、区域性、文化性和个性特色的作品。正如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指出:“艺术的关键并不在于艺术家们所表现的物品,而是通过他的艺术表现所再创造出来的那个对象,因为真实的物品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只是希望凭借种种的艺术表现手段,表达出他们更想表达的文化意义。”[3]130
民族图案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当代画家及设计师研究中国艺术文化的一个突破点;而将传统图案融入现代绘画中,不能直接生搬硬套,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的思维对传统图案进行重构。这种重构是在深入认识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图案中的基本元素加以归纳提炼,使其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观念,或把图案的造型方法和色彩搭配应用到现代绘画中来,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和指向。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创意突出、构图完整、色彩华美的图案设计运用于绘画之中,必然会增添中国民族题材绘画的附加价值,绘画语言和表现力由此更加丰富,同时更具乡土情怀的审美趣味。
艺术创作场域的影响和关照,对于艺术家艺术语言的形成都会具有孕育和影响的独特功能,而这种信息将会在艺术家的各种状态中悄然显现,这就是文化的自律性。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在西方艺术价值观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传统艺术正面临着自身发展的瓶颈和审美危机,在讨论传统艺术是否需要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侗绣图样以其特有的文化价值具有民族艺术传承者的身份,因此侗绣图案应用于当代绘画创作中已然成为一些艺术家独到而执着的审美选择和文化取向。
(二)侗绣图案的绘画创作理念
相对稳定的艺术创作方式和心理定势,使得传统侗绣图案先入为主地在本土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中潜移默化地显现出来,即艺术家需要尊重自身的直觉感受。直觉主义美学家克罗齐从他的直觉概念出发,认为艺术作品就是在心灵活动中完成的直觉,他认为:“用艺术作品做直觉的知识的实例,把直觉的特殊性都付与艺术作品,也把艺术作品的特性都付与哲学”。[4]20
因此,民族服饰纹样如何转换为有效的绘画语言,直接体现艺术家在民俗题材、民族元素中的创作思维,其中带有个人趣味的取舍与再现,成为很多艺术家共同努力的实践方向。侗绣图样具有民族文化延绵不绝的生命力、稳定性、典型性,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和西方现代审美观碰撞融合下,成为当代画家表达本土情怀的真实体验。侗绣图样通过一批中青年画家的艺术创作,积极实践于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插画等绘画领域中,在了解并挖掘刺绣艺术的绘画价值方面有了一些经验。
虽然侗绣图案运用在绘画中的实践经验不够成熟,但纵观艺术发展史,民族图案都是艺术家们可以借鉴的绘画资源。从清代郎世宁中西融合的风俗绘画到当代顾黎明的油画——门神系列,不难看出那些传统图样的民族元素依旧被当今的画家巧妙运用于绘画之中。丁绍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灿烂,艺术道路十分宽广,每种艺术皆可有人创新,走出一条新路”。[5]3如中国的彩陶、青铜器、玉雕、漆器、剪纸、木版画、皮影等,都有不同的艺术造型,绘画艺术可以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西方当代绘画虽然以突破传统、打破规则为发展的根本原则,形成各种流派和各种风格,但就艺术语言而言,中西方艺术都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语言符号,从而能在新突破中寻找到各自的绘画面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从现代装饰绘画的角度出发,汲取西方图式构成的基本原理,再立足于本民族的审美基础上,将侗绣图案的形式与内容,结合艺术家本体的创作风格与情感体验,将可创作出民族风情和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绘画作品。
近现代中国著名的艺术家都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态度,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本体语言、图式构成、哲学依据等因素都表现出独立的思辨能力和强大的表现能力,不管是中国第一批留洋回国的李毅士、李铁夫和李叔同,还是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亦或是当代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包括陈丹青、陈逸飞、张光宇、丁绍光等人,他们大胆采用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构图方法,再转化为独具个人特色的装饰性构图,与全球艺术创作理念相接轨,与世界艺术气息相共鸣,将中国传统民族元素融合在艺术作品中,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展现中国民族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此来弘扬中国传统民族艺术,体现中国艺术家的当代文化自觉与自信。

图3 陈丹青油画《西藏组画》

图4 陈逸飞油画《浔阳遗韵》
(三)侗绣图案的创作转化方式
侗绣传统图案并不是一般简单普遍的图像形式,而是某些特定的关于细节、局部、再现自然的形式,把这种具有中国绘画的游戏性、写意性、个性化特征的图案形式提炼归纳为具有艺术性的程式化语言。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将营造出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并在中国当代中国画、油画、插画等绘画形式中展现出新的风貌,而把侗绣传统图样为代表的图式符号,以简单有效的实用特征应用于画面之中,也体现了民族自信与认同感。
传统装饰元素在古今绘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表现元素,更是装饰绘画的灵魂。侗绣图案的装饰元素可以作为审美载体的视觉语言,通过具体的、大众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视觉符号组合的方式来呈现美的状态。侗族传统装饰元素可以通过现象学的视角解读,获得在绘画中所隐含的真实意图。在研究其转换方式时,恰如日本现象学家伊集院令子所言:“对图像的解明,构筑新的解读方式,他要求人们回到事物本身,关注对结构的理解来解读艺术作品。”[6]11他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证了服饰元素不仅装饰美化生活和传递宗教信息,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通过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解读不同民族背景下的心理性质和文化取向,从而达到民族间情感的沟通桥梁作用。
所谓“侗锦之绣在彩丝,侗水之美在魂魄”,富有情感的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家们从西方绘画和民族民间文化中寻找到契合点,以田园般的诗意、戏剧性的构图、天籁般的色彩和跳跃式的明暗等手法,合理取舍民族元素,凸显侗族文化在艺术创作中的语言样式和深邃情感,彰显侗族特有山水灵性中的艺术灵魂。
(四)侗族服饰在创作中的文化表现
艺术家从可感知的线条、色彩、体积、明暗、颜料、肌理等方面思考创作的手段,通过主观的审美意识对艺术对象作取舍与夸张,不仅将自然的物理属性发挥到极致,还将情感的化学共鸣引发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因此,著名艺术批评家梁玖先生认为:“这些物质一旦经过艺术家之手的改变,按照艺术原理和审艺观重新组合出新的结构和样式,并传达了一定的意图或目的,它就构成了艺术形式。”[7]189从绘画形式的角度观察,虽然侗绣图案目前还很少被作为主要内容用于当代知名民族艺术家的绘画当中,但是也有不少画家通过传统民族服饰着装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侗族风情。例如写实派画家吴极的作品《侗曲悠悠》,生动地塑造了一位身着侗族传统服饰、手执侗族古琵琶的少女形象,她眉眼婉转、面含微笑,正用侗族琵琶弹出一串串欢快清脆、质朴悠扬的小调。栩栩如生的画面,使观者仿佛听到了那历经千年文化沉淀的民族乐曲。黑褐色背景是侗族故土的赤色山石,两千年的光阴洗礼使养育侗族儿女的土壤显得格外沉郁厚重,但身在其中的少女却又是那么青春明亮,这二者便如少女传统服饰中的侗绣一样,虽对比强烈却又有着奇异的和谐统一。明与暗、新与旧,它们本就不是完全对立的两面,若以画笔将之调和创造使作品更有文化深度。

图5 吴极油画《侗曲悠悠》

图6 卢平中国画《侗家又逢丰收年》
民族画家卢平的《侗家又逢丰收年》参展于北京画院主办的“疆域行歌——北京画院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展”,描绘了现代社会侗族妇女辛勤劳作的场景,呈现出一幅侗民其乐融融、生活气息浓郁的场面。这是画家到当地实地考察、写生创作而成的作品。当他面对淳朴热情的侗族村民,触动他内心的不再是侗族独特的样貌与服饰,而是那份纯粹的、没有经过打磨或污染的生命力以及那些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淳朴风情。少数民族所展现的贴近自然、流露天性的文化引力,感召着一代代艺术创作者不辞辛劳、不厌往返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亲身感受、吸收,并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表征的美术作品。

图7 龙飞江油画《侗族少女》

图8 佚名插画《幸福》
由于对侗族风情和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情感体验,所以侗族的风土人情成为了湖南著名侗族画家龙飞江绘画创作的灵感源泉和作品主题。他的创作往往以丰满、细腻的造型去寻求侗族姑娘自然动人的美,汲取她们的民族精神,描绘她们内在纯洁的情感世界。《侗族少女》是他经典的作品,画面以深色的花纹和凤纹为背景营造了一种意境深幽、装束素雅的气氛。色彩上,大面积的黑色运用,使画面显得更加沉稳,从而突出侗族少女气质的娴静与典雅。对于精美的侗族服装及银饰的描绘,也是作者绘画作品的一大亮点。在民族服饰的内容形式上,画家折衷选择了他们的民族传统节日礼服作为创作的主题,这样的绘画主题使他的作品在现代多元文化的交叉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样式。侗族服饰色彩及造型在龙飞江先生绘画中的成功运用,证明了侗绣图案在当代绘画中的可行性及有待开发的艺术潜能。侗绣中明艳动人的图案需要当代画家以具有自己个人特色的思维方式和绘画风格,加以归纳提炼,再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代手绘插画作品也关照侗绣中的图像和色彩元素,作品《幸福》的背景以背带盖刺绣为主,侗族妇女的衣袖上绣有二方连续的植物花卉纹样,小孩的背兜上也有鲜艳的动植物和几何纹样。可见作者善于把民族传统图案与现代绘画元素相结合,创作出展现侗族艺术美特征的现代插画作品。
四、侗族文化表征力的诗性传承
在侗族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发现,他们那种对异族的聪明、勇猛和刚烈远远在自己之上的生命感觉早就转化为神话传说,这为侗族人民的生活处境找到了某种合理化的解释,从而得到一定的心理补偿和感情平衡。这在过往的岁月里尤其明显。而今侗族社会已蓬勃发展,由原来长期封闭的深山地理环境中走出来,基本上打破了族群自我心理处于弱势的境遇和认知。从他们的生活事项中可以观察到,丰富的节庆仪式、庄严的宗教礼节和坚守的图腾崇拜,都深深地镌刻在这些有意味的侗族服饰图案中,表现出对神灵和上苍的敬畏态度,使生命的存在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通过随处可见的服饰纹样,随时随地开展具有人性化和平等性的对话与交流,让侗族古老的神话与传说得以有生命地延续。
但倘若在当代服饰样式与现代日常服饰的冲击下,侗族服饰图案设计得不到有效凝练和适时应用,则难以通达古老民族原始的宗教信仰,难以与时俱进地将族群审美意识生生不息地繁衍创新。因而,研究侗族服饰图案在当代绘画艺术的表现过程,应着重挖掘族群文化的核心价值,直击侗族特有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使民族志研究的路径经由“寻找”到“再现”,最后抵达“唤起”,努力摆脱习惯性模仿,突破艺术固有样式的束缚和羁绊,积极主动地借用修辞学中的模式,认真审视“客体”、“真相”、“描写”、“归纳”、“概括”、“证明”、“实践”、“真理”以及“创新”等类似的概念进行研究,在民族志的田野考察中探寻在现实艺术创作中可支撑的理性愿望。
绘画艺术的发展已然来到了现代与后现代时期,符号学与图像志在现代主义中徜徉并发挥了非常炙热的作用,图像艺术与图像记录的学术话语权牢固地钉在现代艺术的评价与批评体系中,而当后现代艺术观念真正渗透在每一种视觉艺术时,“主动”与“被动”同时不假思索地一拥而进,形成了对峙而互动的特殊关系。它超越了纯粹感性的嫁接和超乎理性的创造,使民族文化中持之以恒的审美定律一如既往地融汇在当代绘画与服饰表现中,有时体现在色彩的沿袭,有时体现在纹样的统一,有时呈现出基因的变异,有时展现出生命的逆袭。凡此种种都充分反映出侗族文化滋养后现代艺术语境,后现代文化汲取侗族传统文化丰盈养料的互动关系,从而生发出自然、平等、独立和尊严等特征的文化发展趋势,使民族常有的自卑感在无政府主义的文化观照中得以平和安详地延续。这种非强势、非强权、非性别的文化态度,使调研的样本不再是某一个个体,或是某一个对象,实则是一种手段,一种超越时空的深思工具,亦或不仅仅是超越,极有可能是超越性的回归时空。
综上所述,反思原有人类学的研究体系反思而获得新的认知,对声音的忽视已经开始得到一一修正,尤其在人类学家斯德勒的作品中,强调感官系统给予不同寻常的关注,使人类学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具有了极为细微而更为精准的一线素材,实则是在本学科的话语体系中为民众个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同时,也为所谓“东方主义”的民族志猎奇美学掷下重重一击,那种东方被“本土化”之后,产生出多层次和蔓生状态的生活环境显然不适合本民族的阅读和研究。为此,在艺术领域清醒冷静而肃穆地关照民族文化的传承工程,除了积极构建符合民族心理的评价体系外,其艺术表现形式不仅要摒弃简单的移植、嫁接民族服饰元素的拙劣手段,也要主动放弃盲目的“高级”模仿,而应该感同身受地领悟民族性格和民族历史,深刻体悟蕴含在民族基因中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从而使当代绘画艺术在描述民族文化立场时,将接地气的民族声音和学术界的审美立场相结合,表达出具有相互影响的文化诗学画面,使艺术形式既具有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叙述,又不失艺术特有的诗性魅力。
结语
中国民族图案元素是东方文化中的宝贵艺术结晶,它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流传悠久,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具魅力。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今天,不同形态的民族艺术也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它们构成了今天艺术多元化的全新面貌。侗族刺绣作为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侗民用图形来传达思想、沟通感情,它表达了侗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是中国最早的图形艺术之一。而如何认识这一传统民族艺术,使其在现代绘画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对发扬民族精神和提高大众审美情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世界是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世界,各民族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侗民族图案元素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英]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 李东晔,王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意]克罗齐.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5]丁绍光.巨匠与中国名画-丁绍光[M].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1997.
[6][日]伊集院令子.图像发生的现象与21世纪绘画[C]//倪梁康,等.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六辑(艺术现象学 时间意识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梁玖.艺术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白云]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3.005
[收稿日期]2016-01-10
[基金项目]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人文强桂’优青特色研究团队”“珠江—西江经济带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团队”(YQTD2015005);广西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一般资助项目“区域文化建设广西当代油画艺术风格研究”(201203YB031)
[作者简介]陆丽娟(1975—),女,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术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958;J2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3-0024-08
Writing Culture:Culture Manifestation of Kam’s Embroidery Patterns in Contemporary Art of Painting
LU Li-juan
(College of Fine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Culture” in the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this essay takes the life of Kam’s folklore cultur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 in the inheriting of Kam’s culture and art, and by analyzing the inherent law and culture connotation such as subject matter, pattern composition, color-matching rule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Kam’s embroidery pattern, discovers the painting principle when Kam people applies and expresses the patterns in contemporary art of painting. The essay aims at inspiring the creation of artworks with indigenous features and native senti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folklore culture, excavating good cultural genes in designs of traditional folklore costumes, and making it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folklore ecological system.
Key words:anthropology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of painting; Kam’s embroidery patterns; cultural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