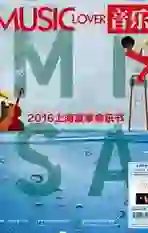敢有歌吟动地哀
2016-08-04曹利群
曹利群
为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而作的四重奏世间稀少,我只知道前有二战期间梅西安的《时间终结四重奏》,后有王西麟的《四重奏》(Op. 41)。前者表达了身处集中营的作曲家在绝望中的信靠,后者是一生困顿、在黑暗中不断投射出光芒的作曲家的真实写照。
这部只有十几分钟的单乐章作品作于2002年初,同年4月13日首演于德国科隆,2005年5月演出于美国旧金山国际艺术节,2007年5月13日于科隆再度上演。虽然它在国内偶有演出,但听过的人少之又少。王西麟在交响曲方面的创作世人瞩目,但在国内同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够。加上有时还会有艺术之外的干扰,使得王西麟新作品的传播屡屡受挫。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西麟结识了来北京工作的德国单簧管演奏家奥利弗·施瓦茨(Oliver Schwarz)。在认真地听了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的录音之后,奥利弗郑重地邀请王西麟为他的科隆四重奏团写作一首新作品,还要赶上2002年4月的演出。首次应邀为欧洲的四重奏团创作,机会难得,兴奋之余,王西麟感到这也是他改变困境的契机。奥利弗回去后,很快给王西麟寄来一批室内乐作品,包括梅西安的《时间终结四重奏》,这之前他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为了开阔视野,王西麟还研究了波兰作曲家古雷斯基的《安魂波尔卡》《晚安》等一批管弦乐队作品。压力自然很大,因为这不是标准的四重奏作品,除了梅西安的《时间终结四重奏》以外,这种类型的作品世所罕有。我们难以得知科隆四重奏团为什么要邀约王西麟写这样的作品,但王西麟的内心非常坚决:“我必须做好它!”
首演如期在科隆举行,举座皆惊,掌声不断。2002年4月16日的《科隆文化报》评论说,“王西麟的新作《四重奏》中震荡着巴托克式的激情,然而个性已完全改变。”“人们可以听到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完美地融合其中。”奥利弗深情地致函王西麟说:“你的音乐对这场音乐会十分重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诉,它的哀悼,它的悲伤,它的充满希望和爱:经过中间的恶魔之舞,而最后却是和平的结尾。不仅如此,你的音乐还表达了,在悲伤和痛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人一定要信任自己,相信能击败邪恶,并最终将感受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纯净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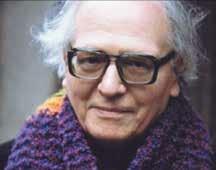
时隔五年后,即 2007年5月13日,这首《四重奏》再次演出于德国科隆Music Triennalekoln现代音乐节。科隆音乐学院教授约克·霍勒尔(York Holler)在听后说:“昨天的音乐会上,《四重奏》是最好的作品……在曲式上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很有个性。大提琴开始的独奏很有力量,很原始,很个人化,作品并没有让人联想到像韦伯恩等任何现代作曲家的影响。我还能记得开始的动机,也记得作品的结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发展都很有逻辑。”他认为,这部作品比他听到的日本、韩国的作品都要好。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四重奏》还很清新,其中透射出的精神状态像三十多岁的作曲家写的。当然,三十多岁的作曲家不可能有这样成熟的曲式。
如果说行家的看法和王西麟心有灵犀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德国观众的不谋而合则让王西麟颇感兴奋。2002年音乐会首演后,有心的奥利弗给王西麟寄来了两封普通听众的来信。一封信中说:“我必须告诉您,我和我太太深为您的作品所感动。您的《四重奏》是智慧的结晶,散发了无穷的表现力。我和其他室内乐界的同行们都一致认为,您的《四重奏》是通过紧凑而密集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音色来感动听众的。”另一封信说:“我们十分幸运地亲历了您的《四重奏》首演,可惜您没能亲自来现场收下那排山倒海般的掌声。我不是音乐家,但我想肯定地告诉您,您的《四重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很想再次听到您的这部作品,从而更好地理解它。”
这部作品没有录制唱片,而且版权在科隆四重奏团那里,因此平日里很难听到。多亏科隆方面给王西麟复制了一张首演的唱片,我才得以在他家里听到这部作品。一个犀利的和弦拖着长音,大提琴以宣叙调式开启了幽怨的独白,另外三件乐器仿佛是看客,任由大提琴自言自语。听的出来,这是作曲家多年积累的地方戏的散板音调,但在这里却变成了强烈的控诉。一声声,一句句,欲说还休,老泪纵横。大提琴还在继续,有中音区的悲愤与哀诉,也有高音区的呼喊、嚎叫和凄厉的痛哭。短短三分钟不到,八个长大的乐句层层展开,须知有什么样的大苦大难才能有如此的哭嚎与痛不欲生。那一刻你的心是紧的,是痛的,挺拔的音型和有力的附点节奏,凸显了作品的悲剧性。
在达到紧张激烈的顶点时,钢琴强横粗暴地介入进来。那是残酷的斥骂和鞭打,突兀而起的对抗性立刻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我一下子想到那个不公平的年月对王西麟残酷的围攻与批斗。在不断增长的尖锐的对抗中,音乐进入快板的第二部分。王西麟说,这是粗暴的撒旦之舞,是魔鬼的肆虐。这个长大的快板,其动机来自秦腔的一个曲牌,间或有波兰作曲家古雷斯基《安魂波尔卡》的戏仿。两者结合在一起成为邪恶横暴、色厉内荏的形象。惊悚的单簧管穿过僵硬冷酷的节奏,充满了激烈的抗争和痛苦的呻吟。单簧管丰富的表现力和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共同组成了富于交响性的织体。从作品开始的冤诉、鞭打到此时的鬼魂之舞,三条线索密集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有旋律和节奏的对抗,也暗示了压迫与抗争对峙。音乐一步步紧逼,张力不断增强,在推进到高潮之后,突然坠入无底的深渊。

进入第三部分的广板,喑哑而断续的钢琴以小二度的低音持续着,单簧管长长的独奏既是凄凉的悲声,又是低吟的叹息,让人想到鲁迅“万家墨面没蒿莱”的诗句所呈现的破碎凋敝的民生境况。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怀(我一直在作品中感受到他的存在)从伤己转而伤众,一己之凄苦已经饱含着民生的悲凉。到了作品的最后一段,单簧管转为亮色,钢琴也奏出明亮流动的音型,仿佛是一种释怀。虽然作曲家自己解释说“这里并不是光明的预示,而是无奈”,但它却在结构和四件乐器的声部音响色彩上有着奇特的对比。
这首四重奏得以在国内演出时,恰巧被作曲家古拜杜丽娜听到。2005年10月13日,古拜杜丽娜来中国讲学,在中央音乐学院小演奏厅的学术交流和讲座中,她听到王西麟的《四重奏》和《铸剑二章》(《黑衣人歌》和《三头釜中舞》)。这一听,让大师震惊不已。她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大师的作品,给我留下很强烈的印象。第一部作品《四重奏》的感情非常强烈,形象非常鲜明。开始的大提琴独奏,好像是有力的抗议……后面出现的四度、五度的和声,很安静,很抒情,给人感觉非常美。这些音调的变化、戏剧性的对比和构思特点,是大师的手笔。”耐人寻味的是,古拜杜丽娜还从这部十六分钟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交响性思维:“虽然这只是个四重奏,但不只是普通的室内乐,而是交响性思维很强的作品。它不仅有情节的感觉,而且音调上有强烈的戏剧性,这不是外在的戏剧性形象对比,而是具有内在的戏剧性。它的旋律进行以及顿音都很独特, 并且形成前后的极大对比。”王西麟听后深感遇到了知音,而在我看来,这是大师对大师的惺惺相惜。
当被问到这部作品的构思时,王西麟打开了他特有的“话匣子”。“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的地方戏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这里的地方戏主要是秦腔、蒲剧和上党梆子,这些戏里的许多故事都是奸佞当道忠良受害的苦戏、悲情剧,像《杨家将》《过韶关》《走雪山》等。那些人物有许多诉说冤情的悲怆的唱腔,很早就深深地感动了我。”与王西麟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首《四重奏》的音乐元素自然少不了地方戏的影响和创造性的运用、改造和提升。国外评论家感受到结尾的安静平和,却和王西麟的理念并不相同。王西麟说他非常欣赏郑板桥当年的挂冠而去,营造类似毛驴碎蹄的拟声,表达了一种面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民间疾苦声。”这种社会学意义的解析古拜杜丽娜自然无从辨析,但“内在的戏剧性”的评论已经证明了两位作曲家在审美取向上的暗合。了解王西麟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就是一出起承转合的悲苦戏,后期作品里,哪部没有他困顿人生隐匿的影像?《四重奏》化用了大量的中国地方戏,却让无数国外观众悠然心会,充分显示了王西麟音乐的穿透力和超越性。

和王西麟话别之时,古拜杜丽娜特别强调说,这样的音乐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上也是很少有、很独特、很新鲜的,希望在全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听到,这对当今世界的现代音乐是很大的补充。也许古拜杜丽娜还不知晓王西麟的音乐在国内的尴尬处境,但她的高度评价让王西麟有绝处逢生之感。我突然想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权且用来作为本文的结语:“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凌晨五点醒来,躺在床上再听王西麟的四重奏。十六分钟,大开大合,大悲大苦,泪沾衣衫……推开窗,见天光微明。好吧,让我们坐等王西麟音乐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