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宇宙与中国字
2016-08-02刘磊
刘磊
在意外成为“汉字叔叔”之前,理查德·西尔斯曾是一心逃离闭塞的家乡小城的叛逆少年,花30万美元扫描古汉字字形的怪人,租住在10平方米简陋房间里的失业老人。他说自己是一个要用一生了解宇宙秘密的嬉皮士,汉字不过是他的众多兴趣之一。
61岁,汉字叔叔,突然红了
理查德·西尔斯(Richard Sears)先生晚年的生活是被中国网友的一条微博改变的。2011年1月15日早上,他发现了一些蹊跷的事情。那时他正在硅谷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位叫吴安的中国女人曾经是他的助手,他创办的汉字字源网上的96000个字形就是她花了8年的时间从《说文解字》《六书通》《金文编》和《甲骨文编》四本书里一页页地扫描并录入的。为此他前后花了大约30万美元。
“我坐在那边,来了一封信,又来另外一封信。那天到晚上是好几百个。”这些来自陌生网友的邮件无一例外地都与他的汉字字源网有关,而平时这样的邮件每个月也就三两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的网站,我都不理解是发生什么事情。”

理查德·西尔斯,花了近10年时间建立汉字字源网,因此在中国社交媒体走红,人称“汉字叔叔”。
Paypal账户里的捐款也是。一个10美元的入账提醒,再过几分钟,又一个10美元的入账提醒……一小时之内的捐款已经超过了100美元,此前的捐款一年不过几十美元。不断涌来的邮件里甚至有网友给他起了昵称,Uncle Hanzi(汉字叔叔)。他喜欢这个新名字。
2011年1月13日,一个无意中发现汉字字源网的中国网民发了这么一条微博:“这个人叫Richard Sears。他用20年功夫,手工将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形数字化处理,上传网络供所有人免费使用。这就是外国人的‘傻吧,这种国家工程,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弄呢?而且这是以自己五千年传统历史为荣,标榜举国体制,人多力量大的文明古国文字。国家都没着急,您一外国人操的什么心?”
至今理查德说不清他红的原因,只知道与中国的微博有关。但当他接到中国媒体的越洋电话时,他态度谨慎,说话小心,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他红的原因与他的“外国人”身份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说,这个外国人做了那么好的一个网站,为什么我们政府拿了我们的钱,然后没有做出事了。我慢慢了解他们一边说我的故事,一边批评政府。我想我不要说话。”他狡黠地笑了笑。

理查德·西尔斯在兴趣上的一大花销是买书,汉字的、物理的、数学的、医学的、生物的……
做过理查德助理、同样热衷与汉字研究的姜礼惠子有时会和他开玩笑说,你幸运就幸运在是个外国人。“中国人做同样的事,不会有人关注的。”她举了一个例子,创办象形字典网的海恩,一个中学语文老师,2003年辞职专心搞汉字研究,如今在厦门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一生的积蓄啊,都花在他那个网站上。”姜礼惠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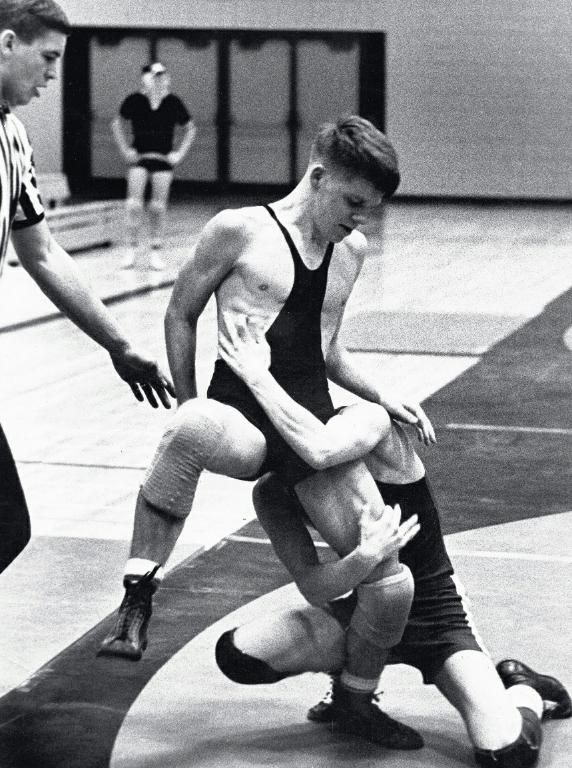
中学时期的理查德·西尔斯。父亲从小对他严格管束,摔跤是父亲允许并鼓励他做的少数事情之一
天真的孩子、偏激的愤青、严肃的学者、洞察人情世故的老人几个不同的角色会在理查德与你聊天的不同情境下显露出来。他长着一张酷似肯德基爷爷的脸,平日最爱吃的也是肯德基。与很多老外不同,他对中国的美食毫无兴趣,超过60元的一顿饭他都觉得浪费,他喜欢便宜又不用等的快餐。
突然红了,得到了认可,理查德开心—“我花了十几年做我的网站,99%的人觉得我的网站没有价值,我自己的朋友说你为什么浪费你的时间,你为什么浪费你的钱做这个奇怪的事情。”
却也不敢开心—“我今天红了,说不定下个星期大家都会忘记了。”
他的网站点击量,从每天1.5万突然蹿升至每天60万,然后下滑到20万,一个月后恢复到了每天1.5万—红了,不红了,又红了,又不红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点击量曲线震荡着,直到2011年10月,中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让他意识到,缘分到了。
天津卫视一档讲述外国人在中国的专题节目在飞往他所在的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乡下采访拍摄几天后,邀请他到中国继续补录一些镜头。在这个不到30分钟的专题片里,理查德是一个略显落魄的形象,已经失业3年多的他租住在一幢简易的二层小楼的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每月500美元的租金。房间里没有床,他打地铺睡,书架上全是一本本大部头的关于汉字的书。

理查德·西尔斯在公司(左图为教儿童学汉字的“汉字乐园”,右图为办公室)。同事们平时都叫他汉字叔叔
拍完专题片回到美国之后,理查德和92岁的母亲商量,他要搬到中国长期居住。19岁离家出走,偷偷转学到离家更远的另一个城市,20岁做背包客,搭便车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22岁时飞往台湾学汉语,他18岁之后的人生里从来都是自作主张。母亲是教了65年中学数学的传统女人,一辈子都在担心自己的儿子,“强迫性地担心”。弟弟乔恩·西尔斯安慰母亲:“飞往中国不过比田纳西远几个小时而已”。之后的几年里,乔恩反复拿一个中国朋友的话安慰母亲:“中国会照顾他的。”
“我在美国就是一个老人,我想我在中国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生活。”
“中国的生活怎么就有意思呢?”
“我不是在美国,这个就有意思。”
19岁,嬉皮士,逃离
1972年7月,22岁的理查德用自己在餐馆洗盘子挣下的钱买了飞往台湾的机票,他要去那里学汉语。几个月前,他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非常生气,骂他“嗑药嗑成了神经病”。

理查德在拍摄中主动摆出亲吻癞蛤蟆的pose,年轻时他曾用癞蛤蟆制作过致幻剂
理查德想学汉语的念头的确来自一次“嗑药”的经历。1971年,他刚刚结束了一年的搭便车旅行。1969年之后的几年里,美国青年学生的反越战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生“闹革命”、做背包客外出旅行,都是常有的事情。旅行途中钱用完的时候,理查德在波士顿黑人区停留了几个月。一天从餐馆打工回来之后,他尝试了LSD。LSD是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流行的嬉皮文化密切相联的一个词,这是一种由著名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在1938年合成的半人工致幻剂(可以“扩张你的灵魂”,理查德说)。
“你吃迷魂药之后,你会了解你完全不了解你自己。然后你会问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讲英文,如果我讲一个外国的语言怎么样。我是一个美国人,如果我在中国长大什么样。我是一个男的,我跟那个女的有什么分别。你突然会有一个感觉,你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理查德回忆LSD对他的影响,“这个会完全改变你对宇宙的观点。你会了解宇宙不是你想到的那样子。”就在那天晚上,他冒出了去中国学汉语的念头。
出发那天,全家人一起到机场为他送行,刚刚查出癌症的父亲勉力支撑自己说话,对儿子接下来在台湾的生活一再叮嘱。弟弟乔恩记得,在机场时,父亲流泪了。
理查德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美国俄勒冈州一个叫梅德福的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在他的观念里,家乡的一切都“很无聊”—“全部是白种人,全部是讲英文,然后全部是基督徒”。生于1950年的理查德是在嬉皮时代长大的一代,他以嬉皮士自诩:“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埋头工作,对世界不感兴趣;另一种人希望能理解全世界。一种人的世界是停滞的,一种人一直想探索前方的可能性。嬉皮士就是后一种。所以,很多嬉皮士最后变得很成功,比如史蒂夫·乔布斯。那些不是嬉皮士的人,最后都是普通人。”
比理查德小4岁的乔恩过的正是哥哥所说的“普通人”的人生,按部就班地读大学、工作、退休。他对嬉皮士的理解与哥哥不大一样。“我觉得嬉皮士都是加入了回归土地运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项社会运动,和以嬉皮士为主的反文化运动重合,一些嬉皮士从城市回到乡村,建设嬉皮公社,实践一种开展民主实验的另类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毒品,对不同宗教持开放态度,喜欢不同风格的音乐。我哥哥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我不认为其他人会认为他是个嬉皮士。”乔恩说。
但在理查德看来,不修边幅的外表或参加某个嬉皮运动并不是嬉皮士的标志,嬉皮士的真正标志是自由、开放的思想,不愿继续过和父母一样的生活,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越战?
乔恩讲述哥哥的故事时主动讲起了历史。“他1968年从高中毕业,那时(越南)战争正急剧升级。也是在这一年,他最好的朋友(在战争中)死掉。战争和民权的抗议声势越来越大。几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被暗杀。骚乱在每一个城市发生,有人引爆了手榴弹,就在离我家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镇上。”他强调,“成长总是处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之中。”
在弟弟眼中,理查德非常聪明,但“他没有一些人们普遍拥有的社交技能,人们觉得他很特别”。理查德自己说得更直接,“可能很多的人认为我是怪人”。
19岁之前,理查德一直在梅德福与父母一起生活。父亲的教育方式有些特别,一方面对他管得很严,禁止的事情很多:开车,去外面看电影,与同学约会,参加party,晚归,等等。另一方面父亲却又允许他做一些别人家的孩子不能做的事,比如,用邻居从实验室带回家的化学品在后花园和街道上制作“炸弹”,以及刻意培养他的勇气—“我4岁的时候,他让我从一条狂吠的恶狗旁走到街尽头。”
“如果我能子承父业找到一份卖人寿保险的工作,那样父亲一定很满意。”已经成为“汉字叔叔”的理查德多年后在脸书上写道,可是他要看看梅德福之外的“外面的世界”。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理查德一直想逃离,逃离那个“控制”他的家,逃离那个无聊的“小城市”。严厉的管束提供了反叛的动机,勇气的培养又正好提供了反叛的力量。大学的第一年他住在家里,就读的南俄勒冈州大学与梅德福只有15分钟的车程。大一结束时,他分批一点点将行李带到了朋友家,然后在学期课程刚一结束就从学校直接去了波特兰,俄勒冈州的一个“大城市”。两周后父亲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在波特兰大学注册了。
“我的爸爸很生气。我的妈妈很难过。”这是理查德的记忆中,每次自作主张时父亲和母亲的不同反应。“在他离开之前,父母每天都会和他争吵。几乎所有事都会吵。”乔恩回忆。
多数人在经历短暂的躁动和喧闹之后,人生终回到平淡的庸常和循规蹈矩的生活。理查德例外。自从19岁的这次“逃离”之后,他再也没有停止一次次的“远行”。这一度给母亲造成压力,朋友们在她的身边炫耀自己的儿子拿了博士学位,赚很多的钱,有好的工作。“我的妈妈可能有一点难过,因为她的孩子不是那个普通的孩子。”理查德说。
44岁,斯睿德,濒死体验
这几年理查德先后在天津、北京工作生活,2016年1月底到了上海。新东家是一家为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开发动漫教程和汉语教材的公司。
2012年在天津时,有一天理查德做了一个梦。在一间教室里,下面坐满了对古汉字感兴趣的孩子们和一些想听他讲些“有趣的事儿”的人。这时,一个小男孩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个红色的盒子:“您父亲的留言。”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部红色的智能手机,手机下面压了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着:“要记得你在台湾时,我给你买的电视。”
梦醒了,他注意到电脑上的日期,这一天正是父亲去世39周年忌日。当年到台湾之后,理查德在信中告诉父亲,他如果有台电视的话,学习汉语会更快些。父亲给他寄来了买电视的钱,并在回信中说,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之后不久,父亲便去世了。
1972年到台湾不久,他有了一个中文名:斯睿德。他住在台北两所大学附近,每天出门找人聊天学汉语,有时搭便车到山里,与山地人一起爬山、捕鱼、打猎。他还遇到了一个台湾女孩,结了婚。但饮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肠胃不适,几乎每天拉肚子。而且,各种异国文化的新奇并不能缓解他强烈的孤独感。与家人的联系只能靠每月缓慢的书信,跨国长途话费太贵,每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3分钟的电话。乔恩记得第一年的圣诞节,全家人一起录了一盘磁带,所有人都对哥哥说了祝愿,给他寄去,“让他知道我们都在想着他”。
在台湾待了两年之后,他因无法忍受孤独回到了美国,继续在波特兰大学读本科。
妻子排行老三,小名三毛。回美国之后,理查德从妻子那儿知道了作家三毛。他对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作家三毛很感兴趣,给她写了信,翻译了她的两本书,还在台湾见了一次面,在路边吃槟榔、聊天。“我喜欢她开放的(思想),她在非洲,她对世界有兴趣。”理查德觉得作家三毛与自己很像。
1994年,44岁的理查德想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美国了,第三次去了台湾。有一天他突然感到像是被人抓紧了气管,呼吸困难。到台湾的一家小医院住了几天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走路只能走十几米。一个月后,他回美国做了血管成形手术,身体恢复了七成。
在台湾的这一个月里,他体验了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天想的唯一一件事是,明天还能不能活着。21岁时吃LSD让他重新认识自我,44岁这次突如其来的心脏病让他思考什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除了家人之外,他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电脑化《说文解字》”。
这源自他40岁时的一个想法。他意识到自己学汉语已经近20年,但只能进行基本的口语交流,读和写都很成问题。他想,如果我不死记硬背,科学地分析每个汉字的来龙去脉的话,可以更好地学汉语。当时他有一本英文版的《说文解字》,但他“慢慢发现这个有很多的矛盾”,比如篆体的“女”字,《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女人的手,而他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手不是一个女人的特殊”,而象形文字“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特殊”。
做了多年IT工程师的他想到了建立汉字字形数据库,这样“这个字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目了然,而且如果发现已有的解释不合理的话,可以随时更新。乔恩记得,哥哥在创办汉字字源网之前,尝试了很多可以“让自己学得更好的方式”。“他有几百张自己制作的中文卡片,结果被人偷了。这些对偷的人没有任何价值,但对他来说太伤心了。所以后来他弄了电子版,这样没人可以偷走。”乔恩回忆。
28岁,毕业生,无底洞
在理查德真正决定做汉字字源网以前的那些年,他的生活分成两条线。
“明线”是1978年28岁的他终于读完了波特兰大学物理专业的本科,然后与三毛离婚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叶淑荣,1985年拿到了田纳西大学计算机专业图形识别方向的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做着IT工程师一类的短期项目制的工作。
“暗线”是他广泛且持续变化的兴趣:本科读了10年,除了因为中途到台湾学汉语以及一年的背包客经历之外,还因为他修了很多与专业无关的学分:音乐、俄语、西班牙语、化学、生物学、历史、心理学;1980年在台湾生活的两年里,“拼命学数学”,从基本的计算到高等数学,思考其中所有的“为什么”;1985年有段时间买了大厨的全套用具,每天在家做印度菜、阿拉伯菜或者中国菜;摆弄无线电,用短波收音机和自制天线偷听美国警察或苏联人与父母之间的通话……
“花了10年才毕业,毕业时候的场景还记得吗?”
“那个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事,我毕业了就是毕业了。”
“为什么30岁时突然想到重新学数学了呢?”
“因为我要了解宇宙。每一个问题,我不要相信科学说的,我要看这个科学的背景是什么样,然后自己(思考)。数学是上帝的语言,要解决我的问题,我需要学数学的历史。因为你学现在的数学,很多的他们没有告诉你它的来源,没有告诉你它的逻辑,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的逻辑,你必须要了解历史。”
理查德对未知的世界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兴趣,得了心脏病之后,他还把医学专业的课本大部分都买来读了一遍。
关于兴趣,他的解释通常只有一个:“因为我要了解宇宙。”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每天下午放学后在学校多待一个小时,到科学老师的办公室问各种问题: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正电子和负电子有什么分别?耶稣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什么?
张蕾是汉字叔叔现在的助理,她眼中的汉字叔叔“挺神奇”,比如他看到一个同事泛黄的牙齿之后能够说出她“体内缺了一个什么什么素”,有次她手上破了一个伤口,他从包里随手拿出一种药,“他说这个(药)就不留疤”。汉字叔叔的“神奇”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在《人物》拍摄的过程中,他在路边发现了一只癞蛤蟆,蹲下将它捉在手里,一边和它玩一边随口说了句:“这个可以做迷魂药。”后来他解释,癞蛤蟆身上有某种可以做致幻剂的化学品,他制作过。
现在轮到了汉字。每个汉字的历史是什么?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让他着迷的“无底洞”。
1994年,他的工作换到了硅谷,接下来的这几年做的都是软件国际化方面的工作,服务对象包括台湾《中央日报》、Sun等。这是他薪水最高的几年。“可是我都花光了,都花在这古代汉字。”他笑着补充。中国女人吴安受雇于他,帮他扫描字形,他每年要从5万美元的薪水中拿出两万给吴安。买各种有关古汉字的书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一次他专程到中国买书,因为刷卡数额太大,妻子叶淑荣误以为遭盗刷让银行将账户锁定了。直到2002年汉字字源网上线的这8年时间里,汉字成了他生活的主角,工作之外的时间以及挣来的钱很多都被他用在了汉字上。“我一边读汉字来源(相关的书),我一边考虑怎么电脑化,我考虑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怎么电脑化。”做网站的这几年里,光写程序的语言和数据库系统软件就换了好几次。
叶淑荣理解丈夫的方式更多的是从“我们”(台湾人、华人、东方人)看“他们”(美国人、西方人):“我知道现在中国都是要读书,就是要赚钱啊,在美国比较不会这样子,尤其像Richard,他是对(科学)那个东西有兴趣。他都自己买很多数学的书啊,物理的书啊,生物的书一大堆。”每次有新的无线电设备上市,他都会第一时间买回家;他会花几百美元买一本“很大很厚”的医学辞典;家附近的实验室里淘汰了仪器,他也会成堆地买回家。叶淑荣总是叮嘱他“不要乱花钱了,钱不要都花光了,有钱要留住”。为此他们总是吵架。“她管我,我不听,我们分开了(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婚姻关系)。”理查德说。
66岁,漂泊者,不汗颜
“他们有的嬉皮士慢慢变成像我一样,是变成科学家,有的嬉皮慢慢是变成酒鬼。可是嬉皮时代我们都是有自由的,我们不在意父母的观点,也思考为什么我们存在。”理查德自称“科学家”,他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怀疑政治,怀疑宗教,怀疑偶像。只有科学是他的信仰。
到了2000年,硅谷的经济形势变差,找工作变得困难。在美国“没有人会请一个60多岁的人做电脑”。2007年,57岁的他失业了。2011年理查德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意外走红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在研究物理的失业老人。自从2002年建成了汉字字源网后,他已经好多年没有研究汉字了。50岁那年,他的兴趣回到了物理上。他把初中、高中、大学各个阶段的课本都找来,就像40岁时研究数学那样,这次他开始对物理系统地问一遍为什么。
意外走红让理查德看到了与中国的缘分,并重拾了对汉字的兴趣。这几年,汉字叔叔的故事总是隔段时间就会被网友翻出来并成为一个小小的热点。最近一次是6月7日一个有1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号用拼凑的素材,冠以“这个外国嬉皮士花了20年,做了一件令中国人汗颜的事”的标题,添油加醋“加工”了他的故事—“他常常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完全不知道时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获得了2000多条转发和5000多个点赞。
不过,理查德觉得中国人没必要感到汗颜,而且这种“汗颜”也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就会开始研究汉字了:“我觉得汗颜的人,都是很团体主义的。大部分人会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为什么你要考虑‘我们呢?如果你想做,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今年5月乔恩到上海看了哥哥,很满意他在中国的境况:“在美国没有这些围绕他的人,因为很多美国人对古汉字不感兴趣。”
但理查德明白,中国人同样对汉字缺乏兴趣。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总是对他窘迫的生活更感兴趣,电视节目则刻意挖掘他的娱乐性。他至今仍对某档节目耿耿于怀。在播出版本中,主持人让他分析的简单的“马”保留了,而他自己要求分析的复杂的“艺”,切掉了。“每一个幼稚园的人知道‘马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知道‘马字,你太笨,你是白痴。”理查德笑着说,“他们是故意的,故意做笨的。所有的聪明的话,他们都切掉了。”这让他“没有面子”。
2015年7月,牵挂了儿子一辈子的96岁的母亲去世了。在中国生活的这几年里,理查德每天都准时和母亲通过Skype说话。“我妈妈在最后几年里几乎瞎了,也丧失了大部分听力。从某个时候起,她认不出哥哥的脸了,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是她知道他‘在电脑里,每个早上都在等着他的电话。”弟弟乔恩回忆。
理查德越来越不喜欢美国。母亲去世时他回美国发现,“所有的女人都超级胖,所有的男人都凸起肚子,所有的孩子都病态肥胖”。美国的政治、警察、法律、媒体,他能说出一堆让他厌恶的问题。他经常和弟弟聊起美国,他们都对保守的现状很不满。在理查德看来,美国有一半的人是保守的,他称他们为“恶心的人”,这些人在嬉皮时代的表现是赞同越战,如今的表现是反对奥巴马,“因为他是黑人”。
“我觉得中国比美国是我的家。”他想永远地留在中国,尽管在中国面临的烦恼也不少。签证始终是个问题,“我现在危险,我有两个月,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离开中国”。经济也不宽裕,从美国来时带了1万美元,这几年不仅没有存下什么钱,反而因为请助理花掉了一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容易,上海的这份新工作他很喜欢,只要专心研究汉字就好,无关任何公司业务至于公司“无私”地雇他的原因,他也感到困惑。
汉字字源网的更新工作仍在继续,他已经建了一个分析8000个简体和繁体汉字部件的数据库,计划几个月内添进网站里。但他现在每天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另一件事上。他在写一本关于汉语语言的书,每天脑子里都在思考无数个关于语言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客气”用的三个字是“不”、“客”和“气”?为什么“染色体”用的三个字是“染”、“色”和“体”……
偶尔理查德也会想起那些在美国选择做“普通人”的同龄人,他们退了休,有儿孙,银行存了足够养老的钱,而他还过着要考虑“明年我住在哪里”的生活。“他们有钱,有一个家,比我舒服。”追问他是否有些羡慕他们的生活时,他话锋一转,“我不会后悔,我有很多的故事,他们没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