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香镇传奇
2016-08-01陈东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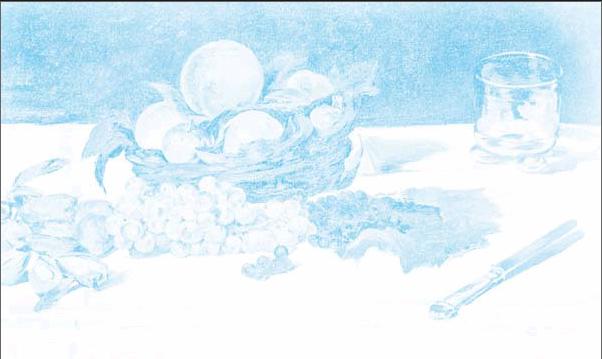

1
你相信吗?某种声音可以勾起隐秘,又将这些隐秘放大。
那个春天,槐香镇常来些奇怪的人。有挨家敲门,不要吃食,只下跪讨钱的“四疤瘌”;有拎着裤裆中间的那个脏东西,鸭子般扯着嗓子、哀唱情歌的失恋学生“阿斗”……“神算子”是揪着春天的尾巴来的。他右眼瞎,睁开是白眼珠,吓得小孩子乱躲;左眼却总眯成一条缝。神算子似乎在用这条缝儿,鬼鬼祟祟打量着世界。他板寸头、发花白,三道深纹刻在四方黑脸的上端。早开的槐花,似乎落到了他的头上。常看到神算子抱着把二胡,在镇上的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因此显得有些生动,似乎把春天揣着身上。更多的时候,神算子戴着方形黑墨镜,把自己悄悄藏在镜片后面,似乎又跟整个春天隔开了些距离。
几天后,神算子在我们二层小楼对过的街边,开始摆摊。一个小马扎。马扎前面是纸片。上面写着“神算子,六爻、算命”,字是颜体,敦实、庄重。没想到一个破算卦的,能把字写这么好。神算子穿着还算整洁的藏蓝西服,外面却套着个油渍麻花的军大衣。眼神里似乎透着某种渴望和贪婪。没顾客算卦时,他就开始拉二胡,重复演奏着我没听过的某个曲子。开始还算新鲜,后来就感觉那声音悲悲戚戚,像人在哭。
我很后悔招惹了神算子。这是个讨人厌的家伙。特别是“大善人”四奶奶,更不该让我给他送吃送喝。他来镇子一周后,似乎就赖上了我们。哪天如果吃不上饭,他会让我们这儿“兜底”。他站在楼下,似乎要把二胡晃散了。安六和阿斗他们,孩童般围着他。神算子的二胡声,似乎有种魔力。只要他开始演奏,他们就都马上消停了。
但是,我却开始心烦了。
我是个保姆,每天都想骂人。四奶奶得了那种看不好的病,是淋巴出了问题。病毒已在她身上,随着血液疯狗般乱窜。她儿子是这里的镇长。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拗不过俺爹俺娘,竟干了伺候人的破活儿。每天心里堵得慌。我承认是为了钱,或者未来可能的工作,镇长大人已拐弯抹角,把某种好消息,通过别人提前告诉了我。没办法,咱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等于半个文盲。我只有忍耐,再忍耐。我甚至天天祈祷,四奶奶早点死。
伺候人先要适应人。四奶奶信耶稣,饭前都要闭眼说句“感谢主”。我刚来的时候,她像个老修女,穿衣黑白搭配,常静在院内的椅子上,手里捧着本破旧的黑皮《圣经》,目视前方。她并不读,却不停翻动,手指在字里行间抓来挠去。
表面上,我喊她四奶奶,心里却骂她“老不死”。
她喜欢絮叨着说话,跟我说这讲那。有次竟神秘地趴到我耳边说:“在南方时,有个知青竟然把毛巾弄成长条,塞入那里面!”她是笑着说的,说得很慢。但在我脑子里像炸雷。我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差点就用双手去堵她的嘴。她常常“南方这”,“南方那”地说,很多话我听不懂,也懒得理她嘴里冒出的这些稀奇古怪……她说完还笑,对着院里的槐树笑,对着二楼的那盆吊兰笑。这多少有些瘆人。她咯咯咯咯笑一会儿,又开始说了。
说吧,说吧,丰富下自己的遗言罢了。我常暗中诅咒她。
奇妙的是,有次二胡声想起时,四奶奶马上立住上身,眼珠斜看右上方,似乎开始配合着唱,但听不太清唱的什么。我常趴在二楼的窗户前,把推拉窗弄个小缝儿,让带着寒气的春风,撩我的脸。那阵子,槐树开花了。奇异的香气填满我们的卧室。我瞥瞥床上的四奶奶,再瞧瞧楼下的神算子,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神算子摇头晃脑,全力摇晃那个叫二胡的东西。那架势,像摁住一个撒欢的猪仔。神算子蹲在树下,嘴里叼着个槐花枝,使劲扭着脖子和二胡较劲。拉一阵子二胡,他就品尝点槐花。
好事的风吹过,槐树悄悄抖落些黄白色的花片。
二胡声在大街上流淌。神算子晃得更带劲了。
我发现,突然出现的二胡声,似乎把四奶奶拉回到某种隐秘中。她脸上呈现出幸福或者害羞的状态。四奶奶或许想起了四爷,或许想起了曾经的某个人。我有些好奇,开始想法探着什么。我正看她时,四奶奶突然对我说:
“闺女,我要做回让人吃惊的事儿。”
不等我问,四奶奶不再搭理我,她开始唱“圣经赞美诗”——
让我拥有最后的开始
让我拥有最后一次的结束
当你不再犹豫
也不再执著
请走入我最后的开始
让所有思念留在过去
让满程旅途不再孤独
……
我头一次发现赞美诗如此动听,简直像流行歌曲,直入人心。
2
槐香镇近年开发后,干什么的都有。路两侧的医院、饭店、旅馆、理发馆、宠物店等全是仿宋建筑,一股脑的聚到这个街上。开店的人,大多穿着宋代服装。游人来到这里,有穿越时空的恍惚感。镇上还有天主教堂。四奶奶去那儿祷告的时候,阳光穿过玻璃,打在她的黑发和侧脸上,似乎感觉,她脸上很细很短的绒毛,都显得特别安静和虔诚。教堂的钟声,缓慢且悠扬,春雨般飘洒在镇上的旮旮旯旯。教堂回来的路上,四奶奶颇有大家闺秀的样子,走路慢且优雅。有时却蹑手蹑脚,显得小心翼翼。中央大街是泛白的水泥路,四奶奶的鞋磨着路面。日子似乎被她无限拖长,拖得让人心焦。她不许我近身搀扶,时常用力甩开我靠近她的胳膊。这让我有些尴尬,只能咬牙切齿地跟着。
四奶奶通常直接从教堂踱到水边。
我们镇子四周全是水,靠着南北两个石拱桥,连接外面的路。镇子多槐树,夏至前后槐花开放,一夜之间像下了场雪。四奶奶说,她当年投亲靠友,一路向北,误入槐香镇,闻到这魅惑人的香气,才决定留在这儿的。四奶奶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是坐在水边,或者去水边的路上。“槐香亭”靠着水边那棵最大的槐树。几百年了,槐树依然枝繁叶茂。大多的时间,四奶奶似乎是亭子里面的一尊铜像。镇上投资建造的凉亭,似乎是专门为四奶奶盖的。四奶奶脸上虽多皱纹,但皮肤白皙,能看出来,她年轻的时候,定是个大美人。曾经的两个酒窝,已经变成两小撮密集的皱纹儿。她最近染了黑头发,这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我常以为,四奶奶一直在想四爷。她一直在凉亭边等,拱桥并不远。四奶奶用和自己说话的方式,消解着日子沉淀的某种东西。四爷是土生土长的槐香镇人,已消失多年,据老人们说,四爷曾干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后来杀人逃亡。我见过四爷的照片,墙上挂着,很魁梧的一个人。只要看到魁梧的人,四奶奶的眼珠会亮一下。这总让人感到心酸。等待中的四奶奶,脖子并不怎么动,眼神会在水面和拱桥间游弋。
神算子那天出现时,是夏至前。
春天有些调皮捣蛋,冷一阵热一阵。傍晚的气息有些神秘。魁梧的神算子,孩童般跑步穿过石拱桥,却立刻放慢了脚步。桥北侧的两只大石狮,似乎在冲他龇牙咧嘴。阳光在他的脸上,镀了层浅金。神算子撸了把脸,立在那里,打着眼罩四处看了看。他的头上下抖动,眼神似乎有重量,剧烈拍打在街上。街上行人并不多。神算子踮着脚尖,猫般走了几步,却接着返回石拱桥上。他的眼神射过来。水边的石子路,倚着镇子的形状而建,走向并不规则,像唱戏花旦的飘袖,顺着水边抛了出去。桥栏儿的顶端,间隔雕刻着槐花和飞马,样子都有些夸张。他扶着桥杆喘息,身体哆嗦了几下,接着拍了几下前胸。
四奶奶眼神迅速爬过水面,跃上石桥。她眼皮迅速合上,睁开;睁开,合上。空气酒精擦洗过似的,四奶奶眼睛里似乎出现了魁梧的影子。四奶奶“唉”了一声。或许神算子那天并没有看到我们,转眼他就消失了。但四奶奶却说:
“我吹口仙气儿,来了个人!”
她接着“咯咯咯咯”笑起来,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我被迷茫笼罩,忽然感觉有些难受。
阳光打在抖动的水面上,不规则的刀片在水面上漂着。
大堆的槐叶隐在另一些槐叶里。大朵的槐花隐在另一些槐花里。
四奶奶又开始自言自语。她对着槐树不停地说,嘟嘟囔囔的。我感觉,槐树也和她说话。树皮里、树叶里包裹着槐树的声音和香气。我劝四奶奶回家。她看了看河面,接着扭头冲着我说:“河水会说话的。水下藏着的鱼和水草,都会说话的。我要听它们说完。”
3
神算子是河南口音。一周后,四奶奶让我把吃的喝的送他时,他一直“中中”的。
但是,接着发生些事情,让人恐惧。突然有天下午,我们居住的楼顶,滑落了一条蛇。我碰巧看到蛇从窗户外掉下去。蛇头好像还冲着我看了看……那些天,我经常做噩梦,感觉有事情要发生。我在梦中竟然认为,蛇或许坠落前就是死的。不久后,有两个人因为在街上争夺“练摊”的地方,互相大打出手。其中,有个竟然是神算子。他浑身是血……后来,神算子成功了,他从腰里掏出条死蛇,吓走了对方。我没有看清,这条蛇是不是楼顶上跌落的那条。
他们争夺的地方,有个石头台子,正对着我们的小楼。
四奶奶经常送给乞讨者、外乡人一些吃的喝的。可以这么说,除了给四奶奶做饭,我还负责给他们做饭。只是,他们用自己的破碗而已。这些人似乎都很尊重四奶奶。后来,她从他们身边经过,神算子会带头站起来,几乎站成一排,冲四奶奶和我打敬礼。四奶奶会冲他们微笑,扬扬手,颇有电视上阅兵的感觉。
神算子和几个流浪人,住在四奶奶曾经的老院里。四奶奶说:“好人做到底!”
有人说,神算子还常跟着响器班,去周围十里八村的喜事丧事上,耍些玩意儿,讨些钱财。他有个小手机,打电话的时候仍然“中中”的。
但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这里面好像有事儿。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我说不清楚,常骂自己胡猜乱想。
有一段时间,四奶奶喊着神算子和另一个乞丐去教堂。他们并排坐在椅子上,一起诵唱着。阳光透过玻璃窗,耀在他们虔诚的脸上。他们的声音飞出来,有种惊人的和谐。出了教堂,四奶奶就听神算子拉二胡。四奶奶说:“这小子还怪能哩。他拉的叫‘赛马。‘看见你们格外亲他也会!”神算子拉的时候,四奶奶甩开架势,双手比划着,还配合着唱——
小河的水清悠悠
庄稼盖满沟
解放军进山来
帮助咱们闹秋收
……
四奶奶很有些专业味儿,让人有些吃惊。她常常仰着头唱。槐花落了,槐叶绿了黄。槐叶哗啦啦响,像是在鼓掌。但是,有次我忽然发现,四奶奶满脸是泪——
四奶奶到死都很清醒,行动自如。
接下来的几个月,四奶奶似乎玩得更有戏剧感了。
——四奶奶常捯饬个枕头。抱起来,放下;放下,抱起来。她放下的时候,非常缓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枕头一寸寸地脱离她的怀抱,但还未等脱离开,又冲上去抱起。她喜欢玩这种无聊的游戏。这么说吧,她抱起的时候,非常用力,似乎要把枕头嵌进身体里。她抱着枕头,左右摇晃,像拍打婴儿那样。有时候,还乌拉乌拉地哭。她哭声不大,嘤嘤嗡嗡。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四奶奶有时会伸出一个手指,放到嘴唇前面,发出“嘘”的声音……四奶奶重复着这些动作,有些执拗,像分别,又像见面。她能玩几个小时。后来,她去河边也带着枕头,继续重复着她的游戏……有次,我故意藏起了她的枕头。她竟然出现了蛮力,翻箱倒柜地找。四奶奶在大街上奔跑,到处看,遇到街上停放的电动三轮车,也不躲避,她抬腿上去,蹦下来。这样的动作,让人怀疑四奶奶以前练过体育。或者说,病患者身上,有种让人唏嘘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会爆发。后来,我把这种情况汇报给四奶奶的镇长儿子。他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有一次,我出去买东西,回来后发现她不见了……终于在河边找到了她。她抱着槐树,壁虎一样贴在上面。神算子在旁边扯着她的衣服。我分明看到,四奶奶和神算子头上都有些草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神算子表现出一种惊恐,脸上黑里透红,甚至有些发怒地冲我说:“姑娘啊,别让她掉进河里,你要天天跟着她,要看紧了,中不?” ……那天晚上,发生了更诧异的事情。四奶奶竟然爬到沙发上,摘下一楼那个镜框,掏出了合影照片。她拿出菜刀,朝着照片上的四爷一顿猛砍。她甚至割下了四爷的“头”,歇斯底里地大骂:“强奸犯!不要脸!”四奶奶喷着唾沫,她的嘴角拉着白色细丝。我的后背阵阵发凉——
好奇心拿捏人。四奶奶到底有何让人吃惊的事儿?我开始变着法儿,想从四奶奶嘴里掏点秘密。面对我的问题,四奶奶有时回答,有时不理。总感觉,她在和我捉迷藏。
4
第一场小雪的时候,四奶奶死了。镇长请了响器,槐香镇出现了嘈杂的喧闹。雪花不大,很多地方现出毛茸茸的白。四奶奶终于睡在了灵床上。她的身体是条硬邦邦的线。这条线把我和四奶奶,似乎隔离了。我们好像从此再没有半点关系。大门上的“丧”字,盖不住新鲜糨糊的香味儿。我看着白纸黑字的挽联发呆:“良操美德千秋花,高洁良风万古存。”四奶奶这辈子,似乎在保护着什么。我说不清楚。四奶奶闭眼前那几个小时,嘴唇起了层白皮儿,仍然缓慢张合着。她的儿子儿媳,无论谁问什么,她都那样说,但是没有声音。其实我知道,她一直说着“南方”两个字,从口型我能猜出来。但他们不知道,四奶奶在说什么。
但是,四奶奶口中“南方”的具体指向,我闹不懂。
我看着咽气的四奶奶,心里不知道是何种滋味。
四奶奶去世前几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天,她让我叫来神算子。又把我支开。
我去了趟楼下的厕所,回来时,透过窗户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四奶奶盖着个红盖头,正在和神算子拜堂。
神算子胸前系着个大红花……
他有些羞怯,看到我迅速离开了。
接着,四奶奶拿出个纸包对我说:“把这些钱交给他,让他走吧!”
“奶奶,把你心中的秘密告诉我吧。” 我说。
“其实没什么秘密”,四奶奶说:“其实,是我双胞胎妹妹的事情。我替她完成心愿。我们同是知青。40年前,我们下乡到南方——浙江的一个镇子,妹妹爱上了神算子这个有妇之夫。神算子老家是河南的,当时也在浙江那个镇子工作。1971年,我妹妹给他生了个男孩……神算子的老婆因为这件事情,自杀了。后来,我们的父母,以自杀相威胁,让妹妹离开了神算子。可是,我苦命的妹妹,在投亲的路上,在北方小镇的桥边,被人强奸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不去找孩子,找男人?”我问。
“真想去找,想啊,想孩子啊。但妹妹后来结婚有孩子了,事儿如果捅开了,让这里的孩子怎么做人呢?”四奶奶揪着胸脯说,“我妹妹一辈子都在赎罪。她和男人分手时说好了,互不打扰。”
“心痛啊,妹妹隐姓埋名很多年。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对,叫骆依然,多洋气啊!”四奶奶冲我笑了笑。
“她在哪?”我接着问。
“死了,早就死了”,四奶奶摇着头说。
“是我把神算子喊来的,当年他就会胡算八算,”四奶奶微笑着说,“我妹妹死前抓着我的手说,最遗憾的事儿,就是和他没有拜过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妹妹孤独的眼睛。似乎,她在某个孤岛上生活了一辈子……”
我冲到大门外,心里感觉很空,忽然泪水滂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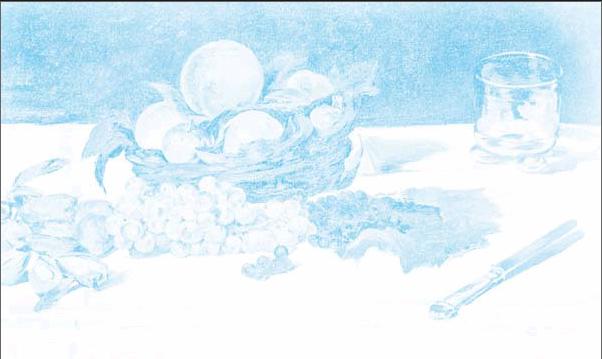
大门上挂着个鼓,吊唁者一到,报信鼓手便会敲几下。我们镇上的风俗,男客来男人哭,女客来女人哭。击鼓次数有别,鼓声一响,男人或女人的哭声,便瞬间冲出院子。高中时,我写过关于死亡的散文。四奶奶正在进入死亡程序。悲哀搅动着我的心。
我正抹眼泪时,神算子出现了。
他推着摩托车进了院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算子有了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他穿着宽大的道袍。灵棚桌上放着四奶奶的照片。她笑得很甜,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神算子看着照片,口中念念有词,表现出一种让人感动的虔诚。他双手舞动,做着些奇怪的动作。后来,他绕过灵棚,去堂屋门口看了看四奶奶。
四奶奶躺在的灵床上,似乎是睡着了。神算子又开始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有人递过来五十元钱,示意他抓紧离开。他说:“招魂,让四奶奶走得不受罪,中不?她是个大好人呢!”有管事的说:“你一个破算卦的,没人请你,你瞎乱什么?”后来,神算子几乎是被人连推带攘,出了院子。接着,却唱了起来。响器班愣住了。他们说,神算子在唱豫剧《大祭庄》:
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
听儿把内情事细说根由
老爹爹诬相公黑心雪口
把李朗当强盗送往苏州
……
神算子唱腔流畅、节奏鲜明,声音乍着翅膀在往天上飞。他唱反串花旦,声音飘飘忽忽的,又尖又高,让人称奇。接着,他又唱《秦雪梅吊孝》,声音悲悲戚戚。四疤瘌、阿斗他们,围在旁边。有人说:“四奶奶多年来行好,感动了神算子。瞧瞧,这家伙还哭呢。”
后来,神算子拉起了二胡,节奏欢快,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地上的薄雪被踩出了脚印。黑色的脚印,凌乱地抱在一起……神算子有只脚踏在摩托车的踏板上。他歪着脖子,扭着身子疯狂拉着二胡,好像和世界比赛着什么。琴杆和弓子,仿佛是他兴奋作响的骨头。
5
当天,又下了场大雪。那场雪是下午突然下起来的。太阳挂在天上,槐香镇出现了罕见的“太阳雪”。四奶奶是土葬的,坟地在镇子的东北方向。送别四奶奶回来后不久,那雪就飘起来了。
雪下了一晚上。第二天,槐香镇像覆了层厚实的天鹅绒。屋顶的积雪很厚实,压得屋子矮下来。很多槐树枝上,恭敬地托着半寸积雪,充满了基督教堂的虔诚气息。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心情糟到了极点。有种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太阳让人感觉像月亮,在天上发着干冷的光。高中时我参加过文学社,忽然有写诗的冲动。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常蹦出些怪词儿,总会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站在大街上疯狂转圈儿,心里的热通过嘴传递到空气里。我脑子里,甚至突然出现了“阉割”这个词儿。雪片阉割了阳光。白色阉割了黑色。现在阉割了过去。现实阉割了梦想。生理的阉割和心理的阉割,都是他妈的阉割。空气中,似乎有什么正在被阉割。这世界,阉割了太多的东西。空气,食物,水……都被另外一些东西阉割了。我放声大哭,但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善良阉割了坚硬。每时每刻,一些情感正在阉割另外的情感。
地球如此之小。这个世界,感情是在流淌的。从北方流向南方。又从南方流向北方。总有一种感情,在追着另一种感情奔跑。一种感情消失,另种感情却开始存在着。情感的总量是恒定的,但世界没有消停的时候。海洋和陆地的纷争,就像人和人之间感情的争斗。看不见的,并不是不存在的。感觉到的就是存在的。感情的暗物质在空气里肆意地飘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日子就这么向前奔跑。
又过了近十天,有则新闻在网上引起了轰动。有个男人,在路口被交警同志扣下。他摩托车上驮着的木箱,突然跌落下来。木箱里竟然装着具女人的尸体。网上刊登了几幅照片,运尸者竟然是神算子。记者采访时,他开始一句话也不说,蹲在那里。后来终于说话了:“领着女人回家。我叫胡永前。她是我的女人,叫骆依然。”从他身上还搜出些照片。竟是他和“四奶奶”年轻时间的合影照。照片的背后,都写着两个小字:结婚。另外,还有些一摞信,外面用塑料纸裹起来。好事者拍照传到网上:
“亲爱的,你让我从女孩变成了女人,又从女人变成水做的女人……月亮像一个懵懂少年,在我们的头顶飞奔。我们的影子或短或长,在田野里兔子般飞奔。我撒着欢、绕着圈跑,你喘着粗气追不上我,就索性蹲在地上,装着很生气的样儿。月亮笑了,弯成了天上的月牙洞,似乎不断有热风和凉风从洞里吹过来,让人做梦心跳。你用力抱紧了我,我用力捶打着你。你轻轻亲了亲我的唇,就一下。你嘴唇里的热传到我的脸上。鼻尖左侧的那一小片皮肤,迅速把这些热放大,在我全身蔓延,痒且酥麻。我睁开眼睛,你的眼珠里有月光。你说,我要对你负责任。我浑身抽搐了一下,又一下。你霍霍霍地笑了几声,声音很浅,但迅速填满了我身体的旮旮旯旯……”
我默默读着四奶奶的信,或者是她双胞胎妹妹的信,泪流满面。
我心里空空的。四奶奶的双胞胎妹妹存在吗?我不知道。
但我坚信:仍有人,在爱着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陈东亮,山东省作协会员,70后。在《中国作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山花》《当代小说》《西南军事文学》《飞天》《文学港》《伊犁河》《小说月刊》等文学杂志,发表(转载)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被《时代文学》“文坛新势力”重点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