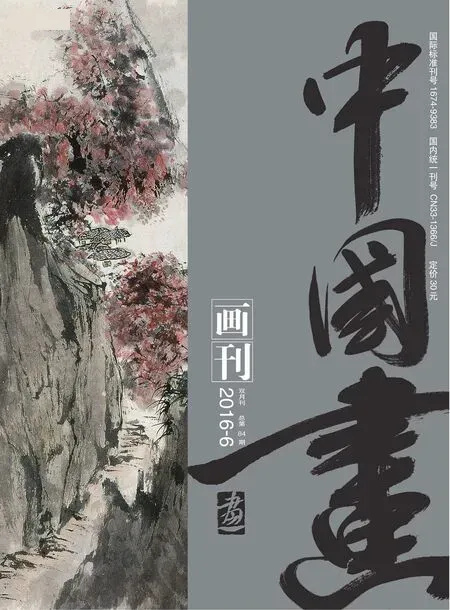当下民间中堂画考略(节选)
2016-07-31赵健雄罗小珊赵犇
赵健雄 罗小珊 赵犇
当下民间中堂画考略(节选)
赵健雄 罗小珊 赵犇
历史源流
中堂,又称大轴或堂幅,是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传统样式。其尺幅限定于2∶1的长宽比,而不得小于三尺,常用以创作气势宏大的山水、人物或花鸟作品。一般悬挂于厅堂或居室正面墙壁正中,两边配有对联,俗称“堂联”或者“挑山”。自明代晚期以来,中堂是中国书画一般陈设中的主要样式之一。
两汉以降,直至明中叶,中国绘画在居室中的主要陈设形式始终为屏风。作为周礼“天子当屏而立”的演化,汉以后,屏风在贵族和士族家庭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器物。屏风绘画的最早记录见于东汉:《后汉书》载,桓帝时有《烈女屏风》。他的兴起肇始于南北朝,在《贞观公私画史》的记载中可见北齐画家杨子华画“杂宫苑人物屏风本”一卷。
屏风双面均可作画的特性决定了他在分隔空间的同时,可以为不同空间提供相应的图像背景。这种特性,也促使屏风绘画在唐的风行。《历代名画记》载:“自隋以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障,多以屏风为准也。”《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载:“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名家作品的炙手可热,至两宋不衰。宋代嗜好书画屏风的时尚可从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极尽详细的记载里得以充分感知。
宋以后,屏风绘画突然沉寂下来,元明清三代,少有画家画屏的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居室格局的改变,使得屏风的应用不及前代广泛;宫廷画院在元明清三代的没落与文人画家的主流化,也决定了专业色彩浓重的屏风绘画不受推重的现实。总之,屏风作品在两宋时期盛极一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公共展示的屏风绘画渐渐让位、蜕变为厅堂挂轴、条屏等形式。而取屏风而代之的卷轴绘画形制的确立与盛行,是在明清之后。
所谓卷轴绘画,一般指绘制于纸绢之上,进而为了便于保存,装裱成可以卷曲收纳的形式。横长竖短的画幅多裱成手卷,可以边舒卷边欣赏;竖长形、方形或矩形画幅裱成挂轴,舒展后可供张挂;成组的竖长形画幅裱成屏条,合之为屏,分之为轴。
手卷式的绘画在《历代名画记•述古之秘画珍图》即有《汉明帝画官图五十卷》的记录。其注曰:“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遴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这种“左图右史”的形式,奠立了绘画手卷的最早雏形。它盛行于隋唐,延续至宋元明清。
挂轴与条屏,初成于唐代,完备于北宋,南宋以后成为手卷之外的主要形制。按薛永年先生的说法,其渊源有三:
一为屏风绘画,即间隔室内空间所用屏风裱装之绢本作品,亦即前述的屏风绘画。
二曰佛教帧画。帧画是佛教画的一种,作于单幅绢上,贴于墙壁,以后揭下,镶装边框,后加衬布,上置挂带,成为可以移挂、折叠的画幅。帧画为壁画发展到卷轴画的过渡形式。
三曰绢本壁画,即张彦远所载,兴唐寺中西院“有吴生(道子)、周昉绢画”。这种绢画或裱于墙,或挂于壁,因绢幅的门面有一定尺度,制作壁画如不拼接缝合,便需由数幅组成一铺。
上述屏风绘画、帧画与绢本壁画,最终都随着装裱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挂轴与屏条画的出现。挂轴的出现,无疑受到了手卷的影响。而一铺数轴的陈设形式,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壁画的衰落。这种形制在北宋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与经济发展所促进的需求繁荣,成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两宋与明中后期,都是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商业繁荣的时代。因应这种时势,商人阶层由此登上舞台。在儒教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审美需求的实现。于是,卷轴绘画在两宋的繁荣与中堂在明中叶的崛起,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必然。
明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的发展,封建礼法的等级限制开始松弛,商人阶层得以享受他们原本不能享受的生活。在衣、食、住、行、用以及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正如时人所言,“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这种礼制的松弛与苏州地区制砖业技术进步相结合,促进了建筑技术的发展。不同于明前期遵循《明史•舆服志四•室屋制度》:“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饰彩色。”单调而简单的方式,后期,尤其在苏、皖地区,砖墙结构的导入,使得扶墙柱加密,柱身变得细长,屋顶出檐减少,民间建筑中开始出现高大、敞亮的厅堂。原有用于分隔堂内空间的屏风由于过于低矮而无法适应,于是堂中平置的通顶落地的屏门逐渐流行,长条的卷轴字画由于直接悬挂而便于更换,一跃成为主流。

浧坡别墅 耕读第

浧坡别墅 临书别院
同时代技术的发展,也为大幅生纸抄制提供了可能。虽然宋代已经可以制作出六尺或者更大的纸张,但限于工艺的局限性,其生产并不稳定,且造价高昂,无法普及。明清时期造纸术的进步,最大的体现即在于供应的稳定与价格的合理化。这为文人画写意精神的发挥、中堂绘画的普及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而徽商对书画的重视也发挥了惊人影响。徽州作为朱熹故里,有着极为浓厚的儒学传统,朱子学的纲常伦理渗透到宗族结构的方方面面,也强烈影响了审美和伦理。富有的徽州商人阶级在积聚财富的同时,试图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们学习和仿效士族在文化和陈设上的品位,以竞相购买名人字画为潮流。与此同时,其原有背景的影响,导致了有异于文人的陈设习惯。他们并不满足于收集作品以自娱,而更倾向于展示于他人。这种使用方式的改变,促进了适合悬挂于堂屋—待客之地—的卷轴作品的繁荣:在收纳便利与赏玩效果上,都没有比这更加适合展示主人的品位与财富。
其后在金石学盛行和收藏由厚古转向“不薄今人”的时代背景下,堂联作为更加直接、通俗地表现当事人态度、立场的方法,逐渐进入中堂的展示之中。清初之后,渐渐固定为中堂画格式的一部分。从此,这种相较于条屏、立轴在题材与内容上更加世俗的展示方式,就自然成为我们记忆里中国画最习见的形态。具体的绘画形式与特定的观赏场合在这里巧妙而无法分割地结合为一体,中堂所承载的审美趣味、文化习俗,乃至家族态度与社会认同都藉由画面与堂联展示于眼前。
当下民间的状况
一、浙江
郑义门:旧日的光荣与当下的守持
由南宋至明中叶的340余年间,郑氏一族在婺州(现金华)藉由儒家文化理论的指导,共财聚食,累世同居达十五世—故而世称“郑义门”:这不仅仅是时间跨度惊人,由他们留下的《郑氏规范》条文所见,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几乎穷尽儒家伦理,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惊人的道德高度。
时至今日,虽然历经战火与动荡,郑氏一族的收藏几乎都已散佚,古建筑群中最主要的郑氏宗祠在经历元明清三代与新中国成立后屡次修葺,依然在寝室(寝殿)中保留了祖宗容相。作为中堂在祠堂建筑中的表现方式,与“三圣岩西峙,三朝旌表,三子发祥,孝义家风三代上;九曲水东流,九世同居,九贤崇祀,巍峨庙貌九楹间”的楹联一起,记录着旧日的光荣。而唯有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义门郑氏的后人会再聚集于此,按着《家仪》的记录,于拜厅设牲礼、点烛、焚香,对着列祖列宗的容相,行跪拜之礼—这已然持续百年,虽或有中断,却终究又回正轨。
礼张:名家与民间的互动
随便推开一家大门,或从窗子望进去,中堂是习以为常的布置——这其实并不能算平常,因为村里宅子大多也是20世纪80年代或者更晚些修造的,格局已然不是过去几进几进的式样,自然也没有了天井和堂屋。但画和字依然放在进门那间屋子正对的墙上,还是随了古制。
村民家里中堂的内容与式样,多是花鸟或者山水—福禄寿三星之类更加俗气的题材反倒不多见;或者说,内容与趣味更近于文人的口味,对于这个世代务农的地方来说,无论如何都值得强调。
二、山东
高密:吕氏传人
吕氏一家三代都以扑灰年画为业,吕清溪老人已九十高龄了,身子仍硬朗,偶尔还作画,只是有点孤僻,不大喜欢与生人说话。他一生历尽坎坷。其子吕蓁立也六十多了,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高密扑灰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孙女吕红霞亦承此道。
据文化学者伊红梅多年探寻和考察,祭祀供奉的家堂、财神,才是扑灰年画的核心产品。
也因此,这里以年画为主体的中堂,通常要到旧历新年才布置起来。
董庄中堂画:申请非遗成功
董庄中堂画,反映了当年文人画随着经济日渐衰落而失去上层市场后,为了谋生,只得转向民间,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受众。这个过程中,董立元起到了引领和推广的作用,董庄中堂画成为清末文人画向民俗画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标本。
三、甘肃
通渭:家家挂中堂,书画几乎是一切
通渭有“五多”,一是收藏家多;二是书画家多;三是字画商多;四是装裱店多;五是字画店多。整个县城人口四十几万,10万户人家,几乎家家有字画,这里的人可以吃不好、穿不好,可以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却不能不收藏字画。
天水:传统中堂集锦
吴氏民居现在辟为天水民俗博物馆,收集与展示的民俗用品中就有若干中堂,都是有些年头的物件,与老宅的气氛极为契合。和普遍意义的中堂设置不同,此地中堂布置中间也是书法,而不放画作。至于这儿收集的中堂,甚至也不是书法,而是某种强调义理,宣扬传统价值观的文字。
四、陕西
阿拉伯文中堂:异文化结晶
中堂本来属于汉文化范畴,而书法艺术却不止汉文化独有。阿拉伯文中堂作为一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到西安时,虽然在有名的清真大寺寻得,却未能得拍摄之便。
回族的阿文中堂一般为有饰库法体,以线条为主,饰以各种植物的枝、叶、茎、花于一体,有的以字组画,做到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给人一种整体的造型美。
五、江西
渼陂中堂:后革命时代的叙事
渼陂曾经在清中叶之前,已然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后因为革命与内战的缘故,最终成为红四军军部的驻地。
北京的雷子人先生以渼陂村为例,重点考察现有民居中堂规制,得出中堂样式在事实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结论。我们步雷先生后尘来到渼陂时,眼前景象比他当年考察时要萧条得多,更多老屋主人出走了,但村民家中多半仍有中堂设置,什么样式与内容都有,却很少与当年革命有密切关联的。
六、福建
福州:三坊七巷觅中堂
时过境迁,三坊七巷也不复旧时模样,在经历了城市现代化开发的浪潮后,现在这里更接近于杭州河坊街或者成都新街坊这样的旅游点。中堂绘画作为旧时官宦和富有人家中较为普遍的堂屋布置之一,在三坊七巷的考察中所见不多。
而福建作为在传统文化保持上极富特色的省份,似乎不应该如此。某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建筑用途的改变,促使现在的使用者倾向于改变布置的方式。因为由我们在福建的亲友家中所见,无论莆田还是泉州,大量现代住宅中仍维持了传统的布置方式:从条案、主座到中堂、堂联,尽管房屋本身的规制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传统犹在。
七、安徽
绩溪与歙县:作为传统的坚守
漫步在歙县,已经没有太多过去的感觉。无论格局或者构造方式,都不再遵循徽派建筑的传统,只是保留了某些符号而已。但即便如此,在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窗后,还是可以见到原本出现在白墙黑瓦里的中堂布局。我们称之为堂屋的结构并不存在,也没有作为一种外部条件的建筑本身的气氛。在经历过上个世纪纷繁的变革之后,依然有人选择这种最能够代表传统文化的方式来陈设美术品,我们所录得的照片里,“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堂联配上不知谁人手笔的青绿山水,多少也有点文人味道。如此,便不得不承认传统所具有的顽强:在习惯和潮流等诸种因素都随着上个世纪不断的运动而消灭的此刻,恐怕除掉真心的欢喜,便没有什么可以驱动主人去如此这般布置的力量。

浧坡别墅 南屏读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