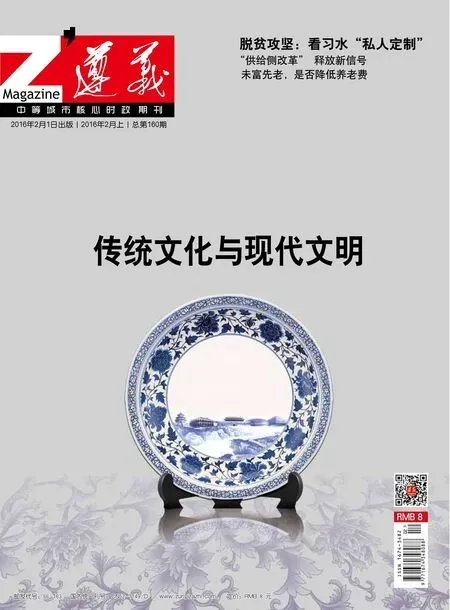双城万国
2016-07-31文丨
文丨 汪 溪
双城万国
文丨 汪 溪
雕栏玉砌犹在,洋大人们也朱颜不改,只是那一腔行走在殖民地上的高贵与得意,早已随着一江春水,东流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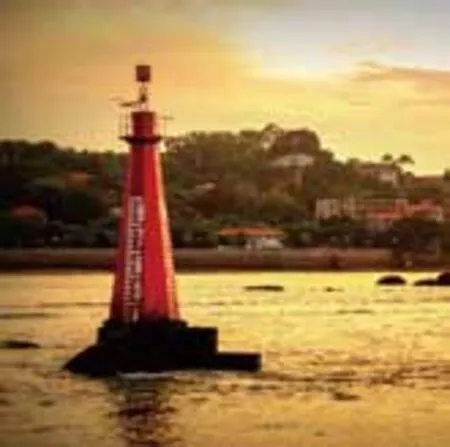
从一百多年的前半殖民地社会走来,中国不少城市都留下了或大或小的异国风格建筑群,天津的五大道、上海的外滩、青岛的八大关、厦门的鼓浪屿还有广州的沙面更是因为建筑群出自不同大师之手,风格迥异而又轮廓协调,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也是游客必游之处。
也是我的运气,因为求学、访友、出差等缘故,厦门、广州都曾去过,也都在八月最澄净的阳光下欣赏过双城两地的万国建筑之美。百年之后,人事俱杳,而建筑仍然坦然站立。虽然已模糊了英美德法或者俄意日奥的属性,但鼓浪屿的清新,沙面的古旧,带给了她们新的性格。
鼓浪屿:我是你不曾远行的心
厦门本岛被称为鹭岛,因古时为白鹭栖息之地。鼓浪屿被称为琴岛,因为这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只有两万多人口,却有着100多个音乐世家,拥有600多架钢琴,人均钢琴拥有率为全国第一。浅浅的鹭江将琴岛与鹭岛拆散,二者不足千米,坐渡轮也只需8分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厦门本已是文艺小清新们的圣地,而鼓浪屿简直就是帕特农神庙,小清新们必来朝拜。
鸦片战争以前,这座神庙曾长期是一座人烟稀少的荒岛。在厦门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殖民者和华侨纷纷来鼓浪屿定居或暂居,许多华侨也回乡创业,未经开发的鼓浪屿成了他们的首选。数十年间,上千座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中外建筑出现在鼓浪屿的各处,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闽南风格的院落平房,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有江南古典园林,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除了跟团必看的海天堂构、八卦楼、黄荣远堂等建筑,在鼓浪屿上,哪怕自己信马由缰地乱逛,走到游人罕至的巷道,也会时不时与一幢有着罗马式的圆柱或中式屋顶的别墅相遇,有的还以院庭中摆放整齐的盆花或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告诉你,这里仍有人居住。
每次上岛,我都是亲友同学的伴游和苦力,有时懒得逛太远,就跟在旅行团后面蹭讲解,半程全程地蹭。厦门人性格温和,从未见过导游因为学生和散客蹭讲解而不爽,鼓浪屿上的各色建筑前,讨论最热烈的常常是导游和并未跟团的学生。
鼓浪屿上有八座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教堂,也修建于不同年代,毕业前,一位教徒同学带我参观了其中颜值最高的一座。我们从轮渡出发,渐渐远离了鼓浪屿上常年沸腾的人群,同学一边带着我在迷宫似的小路上左转右转,一边告诉我,鼓浪屿天主堂是哥特式建筑,也是厦门仅存的一座哥特式天主堂。
记不得走过多少小路,经过多少有着不同风韵的别墅,直到错杂的视野上方出现了典型哥特式的塔尖,才知道到了。大概由于不是礼拜日且已到下午,天主堂并没有开放,连铁闸也紧紧闭锁,只能欣赏外部,目之所及,拱、门、窗、塔以及女儿墙的镂空装饰均呈尖形。
同学告诉我,教堂由西班牙建筑师设计,室内天花是彩蓝色珠网结构,她曾参观过一次,华丽非常。同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轻易不会去天主堂,能专门进到堂内,我想一定是极度欣羡此堂之美。
只要天气晴好,天主堂前一定会有新人在拍婚纱照,摆出活泼甜蜜的POSE,与庄严的教堂一起凝固在照片中,大概会成为让人不时忆起的最幸福的时光。就像鼓浪屿上随处可闻的《鼓浪屿之波》,即使离开厦门五年,也常常在脑海中响起。
厦门从未被割让,也不曾是租界,但也许因为是侨乡,这里总带给我一种去国怀乡的离人的凄清,鼓浪屿上中西合璧的多样建筑,多是当时华侨归国置家所建,解放后,这些华侨和他们的后人多数也再次离家远渡海外,但就如《鼓浪屿之波》里唱的“思乡思乡啊思乡,鼓浪鼓浪啊鼓浪”,即使身在千里之外,只要鼓浪屿还在这里,她就依然是游子们那颗不曾远行的心。
外滩:雕栏玉砌犹在
初到上海,最大的感觉就是“长”,路太长。
在手机上查到外滩万国建筑群“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后,就坐着公交车到了金陵东路附近的一个公交车站,想着自己慢慢走过去,也顺便逛一逛两旁的支路,谁知这条路比学海还无涯,在八月的烈日之下,我整个人越走越绝望,一整瓶矿泉水都喝完了,正想着要不我还是打车过去吧,就发现黄浦江近在眼前了。
沿黄浦江逆流而上,左岸是浦东,右岸外滩,左手挽着新上海蓬勃的现在和未来,右臂拥着老上海从未褪色的辉煌。作为上海的重要象征,万国建筑群全长约4公里,外白渡桥与金陵东路之间并非其全貌而是其精华所在,大多具有100到120年的历史,都是上海的优秀典型建筑。
她们见证了上海沦于殖民者之手的屈辱岁月,也见证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风华绝代,百年沧桑之后,她们仍然矗立在黄浦江畔,她们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上海的荣光。
早期的外滩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这里洋行林立、贸易繁荣。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外滩成了一块风水宝地。商行、金融企业在外滩占有一席之地后,即大兴土木,营建公司大楼。外滩的建筑大多经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重建,各国建筑师在这里大显身手。
52幢大厦鳞次栉比,有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顶、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走在路边,即使不懂建筑如我也从来没能把目光从那精致的建筑细节上挪开过。虽然都是当初各国殖民者各自建造的,风格迥异,但却非常协调地聚集在黄浦江沿岸,与江对岸浦东的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
这些已有百岁的老建筑,在精心的维护下,如今依然光彩依旧,各大银行入驻于这些往日的金融中心,越来越多的时尚酒吧国际品牌也来外滩,让她平添了几多时尚的味道。特别是那些楼与楼之间的街道,印证着新与旧,历史与现代的变迁,别有风味。
站在和平饭店老式的大门旁边遥望江对面高耸的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时,能闻到历史与现代混合的奇妙味道。
尽管各有风格,但要我说,最吸引人的还是海关大楼,就因为8层大楼顶端33米高的钟楼。这座1891年翻建成哥特式的红砖建筑,于1925年再次重建,终成了现在的模样,总体上属于古典主义,正立面是典型的多立克柱式。钟楼仿照英国议会大厦的大钟(大本钟)制造,在美国造好后运到上海组装,是亚洲第一大钟,也是全球现存唯有的三座威斯敏斯特大钟之一,每逢整点奏威斯敏斯特报时曲。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报时曲也顺应潮流改为了《东方红》。然而游览时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不知是现在不再报时,还是报时声被嘈杂的街道人群淹没了。
作为中国最“洋气”的城市,在外滩,随时可见三五成群的金发碧眼的洋人在万国建筑群之间穿行。与百年前一样,洋楼和洋人,仍然是外滩的一道常景。雕栏玉砌犹在,洋大人们也朱颜不改,只是那一腔行走在殖民地上的高贵与得意,早已随着一江春水,东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