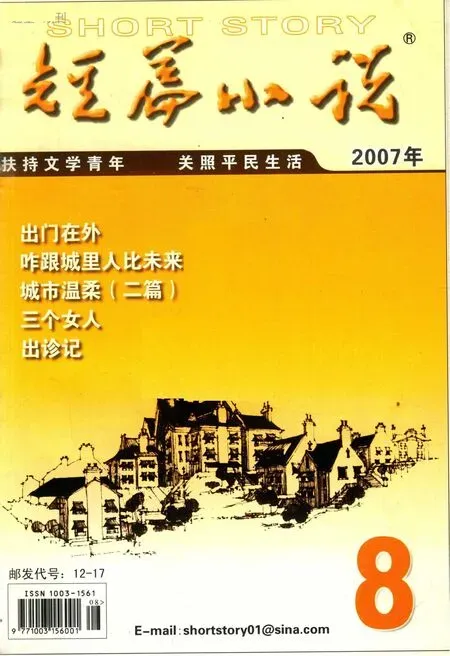旧人旧事
2016-07-19◎孙荔
◎孙 荔
旧人旧事
◎孙荔
孙丽丽,笔名孙荔、晓荔,电视台编辑、记者,专栏作家,发表作品百余万字。作品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试卷大阅读题,随笔 《晓荔谈女人》,中篇小说《谁可相依》,《你的脸上流着我的泪水》等。
青衣阿伶
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阿伶,阿伶是戏班里的名角,她唱得字正腔圆,悠扬婉转,云遮雾绕,再加一副好嗓音好身段,声情并茂的表演,常常让人们醉酒般沉醉戏间。
阿伶生长的小村庄四周环水,小小村子像一个岛屿,阿伶不喜欢下地割草种稻,偏偏喜欢越剧,连走路的姿态也一唱三叹,袅娜成村上一处风景,不由让人感觉时空错乱,怀疑她前世可能是一个戏子。十六岁的阿伶偷偷背着奶奶报了名,在草台班子里走街串巷登台演出。固执而倔强的奶奶知道后手持着小棍,一定要阿伶退出鱼龙混杂的戏班子,满脸皱纹头发像蓑草似的奶奶说,就是在家种田,也比做戏子强,我要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体面地做人,将来好嫁个好人家。
但是阿伶却很叛逆,背着奶奶又去投奔别的戏班,奶奶气得头发梢都是愤怒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仿佛孙女下了火坑。村里人都来劝老太太,各人都有各人的造化,唱戏也好卖艺也罢,这年头有饭吃就好,阿伶聪明伶俐,过够了戏瘾,说不定哪天意念一转就回来了。奶奶望着老屋的一角天空发呆,好像天空上悬着戏台子。
阿伶不久回来看奶奶了,带来奶奶喜欢吃的一些糕点、红枣,还有为奶奶买的新衣服,但是又匆匆地走了,像一个刚刚落下的树叶,瞬间又被旋风刮走。奶奶幽怨的眼神渐渐变得听天由命,长长的叹气声,似乎拿孙女没辙了,孙女也拿自己没辙了,接近神经一样入迷地唱戏。
阿伶渐渐成了戏班里的名角,她入戏深,表演起来惟妙惟肖。爱听戏的沙河镇第三旅旅长赵奎,很喜欢听阿伶唱戏,戏台下常常出现赵奎门板一样的身影,他常沉醉在阿伶碧水蓝天一样的唱腔里,那长袖舞出的身影娇柔动人,是定格在他心里的一副水墨画。有时赵奎听得不过瘾,就去后台探望阿伶,一来二去,两人感情渐渐起波澜,后来赵奎想把阿伶娶到家中,就可以随时随地听戏了,后来阿伶就真的成了赵奎的姨太太。
赵奎生有一张粗线条的脸庞,坚毅的下巴,薄薄的嘴唇常高傲地紧抿着,黝黑的眼睛里有着淡淡的忧郁。在一次抗日战争中,队伍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赵奎心里早明白此次战役必败,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人退缩,也没有一人临阵脱逃,战士们以赴死的决心为失败而战,为悲壮而战,为战而战。
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天,赵奎穿着一身伪军将服,和手下人在酒馆里饮酒,与其说饮酒,不如说饮恨,日军以各种方式诱降他,甚至威胁要掘他母亲的坟墓。是孤苦的母亲一点点讨百家饭将他拉扯大,有一次两天没能吃到一点东西,小小的赵奎饿得快要昏过去,只觉得头重脚轻,眼泛黑花。母亲到一家看管很严的大户人家,要了一碗米饭,一只硕大的狼狗撕扯着母亲的裤腿,瘦弱的母亲吓得脸色苍白,几乎瘫倒在地……往事啃食着赵奎的心。赵奎决定诈降,以假投降的方式来对付日军。一个月夜,马粪的气味,血腥,干草香,在清澄的夜的空气中飘荡,赵奎对着母亲的坟墓连叩了三个头,他在心里说,母亲是知道我的心的,他低下了头,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地掐到肉里去,他坚硬的脸上流下了两行热泪,残月下的树叶在风中微微颤抖着。
日本人占领了沙河镇,其中日军里最大的长官虹野,人长得粗糙像上帝未睡醒时捏的半成品,但是虹野却文雅得很,爱听戏,他听起戏来,僵硬的表情顺间柔和多了,所有的凶神恶煞都像一个变脸,变戏法似的溜走了,他变作了一个温和斯文的人,他请戏班到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为他演出,偶尔虹野还会穿一下龙袍,客串一下角色,也许在中国待得久了,唱腔居然咬字清晰圆润。
虹野喜欢听阿伶唱戏,但他不知阿伶是赵奎的姨太太,他只知道阿伶是这个戏台的名角。一日虹野正摇头晃脑地和着韵律一唱三叹,眼神柔和成一汪水,在台上正唱得渐入佳境的阿伶,朝台上扮演武将军的小秋木使了个眼色,忽然两人腾空而起扑到台下,阿伶将冰冷闪着寒光的刀子架在虹野脖子上,对着持枪的宪兵大喊放下枪,统统放下枪,否则你们司令虹野的小命就没了,随后阿伶小秋木和长官虹野在芦苇掩映的沙河里,一条树叶似的小船上消失了。
这日旅长正带着戎装待发的士兵准备夜间出发,这时身穿戏服的阿伶出现在他身边,从腰间拔出长剑,一边舞一边唱起了“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赢秦无道把山河破,英雄四路起干戈。”她舞得一脸泪水。风呼啦啦撕扯着军旗,“我以宝剑自刎于君前,以免挂念妾身。”唱完真的以利剑自刎,赵奎以军人的速度前去夺剑,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他的眼睛涌出了泪水。阿伶仍凄凄惨惨地唱,唱得将士们都红了眼。
赵奎知道自己这一去凶多吉少,归来的希望几乎为零,为了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也安排好了三位夫人,让她们各自寻找自己的前程,免得受托累。后来赵奎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他被抬回来时像是睡梦中的人,粗眉毛微微皱着,高傲的嘴唇略微下垂,仿佛是为了发命令而生的。
后来,赵奎的一位夫人为了生计,投奔了做纺织生意的亲眷,阿伶因受了刺激而变得精神失常,她常常一个人迷迷糊糊中去沙河芦苇荡里唱戏,说不出的苍凉,那风声把声音刮得很远很远,像一个遥远的梦境。
裁缝冯小七
裁缝冯小七是在程记客店认识香云的。
那是一个雾气很重的秋天的早晨,冯小七正在裁缝店里忙碌,裁缝店在临河路南段,钱庄、典当、盐商,米商、绸缎商等商铺林立,一棵香樟树遮住半边街,店外稀稀疏疏走着各色行人,他也无暇抬头顾及一眼。冯小七的裁缝店在凤阳城开得很出名,冯小七年龄不大,但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裁缝,他也常背着包走街串巷,接来布料由妹妹帮忙缝制。
这天程妈请冯小七来程记客店,给十几个烟花女子做旗袍。冯小七清瘦的影子在程记客店的西厢房内,轻轻落座,掏出剪尺划粉放在古铜色的清式雕花桌上,这时窗外一场小雨迷迷糊糊降临了。冯小七依次给几位粉脂香味很浓的女子量身,她们叽叽喳喳,笑声里有着风尘的味道。冯小七三笔两笔就勾勒出一个妖娆的旗袍,有着完美的曲线,这时冯小七的剪刀像一尾游走的鱼,在平静的水面上游动,瞬间一块完整的布料,被裁剪得七零八落。
最后,走来的一位女子,人年轻得像山毛桃一样青涩。她自我介绍说叫香云,明眸皓齿,山清水秀,这样女孩多出自乡野。冯小七量她瘦削的肩,两人面对面,他能感觉到她轻微的呼吸,濡湿的唇,白皙纤长的颈项,转身,那长长的辫子轻轻晃动着,让冯小七的心颤颤的,香云像一道光芒出现小七面前。
程妈问冯小七可喜欢香云,冯小七脸红了,程妈把眼神瞟向雕花的屏风,说,三百骋礼就可以领走,香云是新来。程妈声音有些阴冷。冯小七没敢作声,没敢作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银两,也就没有了底气。
冯小七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香云这旗袍他做得很用心,紧袖、封领、底衩、嵌花,黄昏时他借着窗前的微光,一针一线用他那灵巧的手缝制得针线格外匀称。两天后,冯小七提着小包袱为香云试身,晨光中,窗棂前,香云羞涩如一朵云,她像桃花一朵开在小七面前,脱得只剩下麻夹儿,让冯小七本来突突的心,跳至喉咙咽儿,他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气声,他为香云牵衣拽袖,看香云袅娜地在自己面前转来转去,冯小七醉了。女人一穿上旗袍立马像换了一个人,普通女子也变作了艳阳花。香云喊一声,冯哥,阳光像碎银一样洒进房间里,冯小七却有些微醺的感觉,他想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挣够三百元。
冯小七没日没夜地忙碌,大约七七四十九天了。这天冯小七在店里埋头缝制衣服,面容有些憔悴。这时一大户人家做寿,送来一整匹布料,要他尽快做成衣衫,这让冯小七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这匹布完工后,那三百元聘金就有些眉目了。
冯小七有一双女人的手,十指纤尖而灵活,他端坐如木,引线飞针,比得上古代的江南绣女。那月光下香云转身回眸瞬间曼妙的风情,一直在他心里回旋着。
大半年的辰光,再加上冯小七以往的积蓄,他终于攒足了三百元钱。终于有那么一天,冯小七风尘仆仆地踏进程记客店,怀里揣着聘金小心翼翼,像揣着他的后半生。冯小七谨慎而恭敬地来到程妈面前,程妈厚厚的粉底,让人感觉一说话会扑簌簌落下来,她缓缓地吐着烟雾,让冯小七以为到了虚幻的仙境,冯小七低低问程妈,香云在哪里?
程妈看了看冯小七,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宽大的金戒指,漫不经心地说,香云不能为了你我一直供养着,香云早已被人聘走。这时冯小七的心咯噔一下掉在地上,甩得尘埃飞扬。程妈说香云走了,我们还有别的女人,程记客店就是不缺女人。冯小七落寞地走了,程妈说什么他都没有听见,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像养了一窝蜂。
这天一瓜皮小帽,长礼马褂的刘老四,请冯小七去给开中药铺的赵老爷府中为太太做旗袍。冯小七的旗袍做得越来越有名气,让女人曲线玲珑,摇曳生姿,盘扣的高贵与优雅,衩口妩媚与香艳拿捏得恰到好处。
冯小七在幽雅庭院内刚刚坐定,太太款款地走来了,不,是姨太太,目光相逢的刹那,两人的眼光又落了下来,那姨太太是香云,粉扑扑的脸儿圆了,温润如珠,高高拢起的发髻多了一份府中的贵气。香云走过来,环顾一下丫环不在,她走到小七面前,鼻尖似乎相撞,说,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声音里有着湿湿漉漉的幽怨。
冯小七搓着手,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刚要说什么,这时一股烟味先跑来了,接着是老爷沉沉的脚步声。赵老爷有些苍老,嘶哑着声音说,你看这旗袍料子如何,不行我更换一下。冯小七摩挲着布料,说是上等料,颜色只要太太喜欢就是了,老爷满意地晃悠着走了。冯小七在房间里,围着太太量身,肩宽、臀宽、胸宽……冯小七忍不住把温香软玉的香云拥入怀中,他温热的唇抵住她柔软的发。丫环蹬蹬跑来送茶水,香云赶忙推开冯小七,冷着脸对丫环说,给先生放张唱片。唱片响起,咿咿呀呀唱起来:“一弯清泉清且浅,水也甘甜,花也正艳;秋雨绵绵,心亦绵绵……”
赵老爷闲得无聊时爱赌牌,且一赌就是一个通宵。香云便秘密私会冯小七,春宵一刻,梦也想求,黑夜潮水般一波一波涌起,香云和冯小七在密谋两人私奔的计划。
一天赵老爷喝了很多酒又去赌牌,这一赌又是一个通宵,虫儿也眠了。香云趁着月黑风高,日月无光,装作去寻老爷,然后打起包袱,让冯小七在墙外的老柳树下等着,两人一起做船去昆城过神仙眷侣的日子。
两人逃到渡口处,不料西瓜流水坏了事,不知何时家丁竟跟了上来。紧跟着赵老爷也跟上来了。老爷说,我看得出你俩平日里眉来眼去,我已让下人防备你们了,果然上演了一场私奔的戏,给我打!给我打!老爷愤怒得声音在发抖。两个壮丁,你一掌我一拳,十几个回合,让冯小七难以招架,脸上流下了血,一家丁,勇猛地拿起棍子直奔小七的大腿挥去,于是冯小七的后半生就成了瘸子裁缝。
香云被关在了府中,冯小七私奔未成还差点搭了半条性命。从此冯小七一拐一拐地远走他乡,瘸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裁缝,外地人很喜欢这个远方的裁缝,做工精细,针脚匀称,且工钱少。只是冯小七以后见多了小蛮腰,丰乳肥臀曼妙风情的女子,不再生造次之心。约一年后香云给老爷生下了一个儿子,云再无心出岫,小男孩满庭院地耍玩,眉眼间很像冯小七。
玉匠茂子
茂子重新站在家乡的一个土埂上时,已是晚秋了。
茂子的胡子很长很乱,让人觉得好久没有修理了,仿佛日子过得很慌乱。茂子的破军装穿得东扭西歪,已失去了军人的英武姿色,倒像火车站上的流浪汉。战争过去了,茂子有幸活了下来,虽然看上去四肢健全,但他某部分神经受了伤,看上去滞呆,很少言语了,这场战争也让他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他身上斜挎着的包里,有一本重度残疾症。
这时,村上的老臣公公坐在老屋前一把破旧的椅子上,抖着为数不多的山羊胡子,颤颤地说,茂子你回来了,你爹已为你找好媳妇,她可是十里八乡的俊妞儿,笑起像牡丹花一样好看。茂子的神经已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有了媳妇,参军前好像有人提亲,他见过一群姑娘,在集市上对着他叽叽喳喳地像一群麻雀,其中一个姑娘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那时他帮爹在集市上卖山芋。之后他就参军了,一走就是好几年,那时虽然他穿得寒酸,但也掩不住是一个英俊的小伙。
茂子回到家,看见一个穿着花褂的女人,在往两棵榆树之间的粗绳子上挂玉米。那是英子,英子是她的未婚妻,肤色微黑,眼睛像黑葡萄,笑起来有一排洁白牙齿。茂子走后,家里只有老爹种地了,娘一直卧病在床,英子就常来他家帮着干农活。老爹常笑着说,英子真是好姑娘,现在连用牛耕地,也快跟我学会吆喝了。
英子同茂子说话,茂子呆呆地望着她,没有表情,英子的心沉了沉,又沉了沉,快落在地上了。茂子默默跟在英子后面给牛添草加料,爹望着面前有些呆痴的儿子,想着往日爱笑又机灵的儿子,一转眼就能爬到枣树上,一晌就能从河里捉回几条鱼,而如今……爹的眼里含满泪水,心酸如夜里的冻露。
一天,早饭是红薯稀饭,和着红腌菜。饭后,茂子忽然拿起英子的包袱,嘴里听不清说的什么,像含着什么东西,指指村口的大路,意思是让她回去。英子一边用袖口擦拭着泪水,一边挎着包袱回了自己的娘家。她做梦也没想到,茂子会如此这般,她常想像茂子打了胜仗,英气轩昂地回到她身边,然后耕地种田生儿育女,直至天荒地老,但是此情此状,让她伤心,没有回头路可走。
让人惊奇的是,茂子经常出现在邻村的莲子家。莲子带着女儿孤苦无依地生活着,莲子的丈夫金贵是和茂子一起去当兵的,金贵牺牲在战场上,成了光荣的烈士,留下无依无靠的莲子,莲子很瘦弱,她的笑容也很瘦弱,像冬天稀薄的太阳。
茂子常常出现在莲子家的田里,茂子总是沉默着,即便说话也让人听不太清,茂子索性不言语了。他有时牵着莲子的女儿小燕的手,呆呆地笑,和小燕一起快乐地逮蚂蚱,串成串,茂子笑容显得很单纯,他把金贵家的庄稼侍弄得很滋润,他想金贵一定在天上对着他笑。有一晚他在梦里见到了金贵,对着他说谢谢,眼神很悲戚。茂子喜欢买烧饼夹肉给莲子吃,于是莲子的笑容丰满了许多,茂子爱吃莲子给他做的面条,茂子一气能吃上两碗。晚上,他喜欢静静坐在院子里看月亮,背后莲子在教小燕识字,日子如水安静地流着。
后来,茂子和莲子领了结婚证,虽然茂子已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农活干得很好。后来村上的人议论说,茂子并不全傻,茂子可能在完成战友金贵的遗愿,帮着照顾好他的老婆和女儿。但是茂子总是沉默的。
想不到半年后他们离婚了,为什么离婚谁也猜不清。茂子也从此在家乡消失了,像天上的一朵云从此无踪影。只不过莲子每月都收到一笔汇款,说那是茂子寄给女儿的抚养费,离婚时签下的协议,但是汇款下并无地址。
多年后,有人在江南一座小城遇到茂子,茂子因雕刻玉在当地小有名气。茂子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间干净的老房子里,每天陶醉地雕刻着玉器,他的头发有些斑白了,他说话嗡嗡的,但仔细听是能听得清楚:此款玉古朴大气,色彩过度柔和;另一款玉像一段栩栩如生的树枝,纹理清晰,舒卷成如意状……此时,一场春天的雨开始飘落。
茂子微笑着,他微笑里有一种安于平淡生活的味道。茂子回忆着往事,说,战争让我不再是一个健全的人,当时觉得天地都是灰的,前方的路不知道在哪里,想到了死,我不想连累还未结婚的英子,她还年轻,她还漂亮,她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
但当我看到金贵走了,留下可怜的莲子和小燕时,似乎有束光照在我心上,那束光叫勇气,我要帮她们,我不想让她们一辈子再为衣食担忧,但为了让她能正常接受,我给她们生活费,我同她结了婚,又离了婚,我知道自己不能给她带来一生的幸福,选择离开是迟早的事。
茂子笑着,笑得有点沧桑。这时,江南笼在一场绵密的细雨里。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