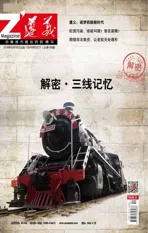徐志摩:公子驾到
2016-07-18■丨晓荷
■丨 晓 荷
徐志摩:公子驾到
■丨 晓 荷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徐志摩,以其诗,以其情,点亮了那个灰蒙蒙的时代。正是那一首首清新隽永、迤逦纯净、飘逸灵动的诗,伴随青葱岁月,在心田播下文学的种子,慰藉年少的忧伤、装点青涩的年华、丰盈年轻的梦想,开启一段灵魂的诗意栖息之旅。
青年才俊
或许每个中文系的女生,都曾有个关于爱情的玫瑰梦:在最好的年华遇见那个人的浪漫爱情;邂逅一份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唯美爱情;演绎一段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经典爱情……梦幻中的男主角,就像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写得好、爱得好的“五好青年”徐志摩。上世纪还没有“男神”一词,好吧,他就是中文系那群爱花痴的女生们“梦中情人”的最佳诠释。
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首富之家的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优渥的生活。沈钧儒是他的表叔,金庸是他的姑表弟,琼瑶是他的表外甥女。
从小在家塾读书,1908年进入硖石开智学堂,师从张树森,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郁达夫、厉麟似同班。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也注入了新的因素,并大量涉猎中外文学。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很大,二人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
1918年,徐志摩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经济系。在美国待了两年,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诱惑,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未能实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觉苦闷想“换路”走的时候,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1921年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1岁到25岁,从私塾到现代大学,他读了无数学校,无论喜不喜欢,在每一所学校的表现都出类拔萃,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可是典型的学霸。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与英国名士交往,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理想主义。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如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赣第德》。同时他写了许多诗,其中《康桥再会吧》最为经典。他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换路”成功,走入诗人的行列。
在剑桥的两年,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成为新诗的代表人物。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年仅28岁。作家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大概指的就是徐志摩这类天才吧。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首初载于1928年《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号,署名志摩的诗,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诗作问世后,文坛上只要听到这一声诵号,便知是公子驾到了。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能把“偶然”这样一个极为抽象的时间副词,使之形象化,置入象征性的结构,充满情趣哲理,不但珠润玉圆,朗朗上口而且余味无穷,恐怕也只有徐志摩了。诗歌史上,一部洋洋洒洒上千行长诗可以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的历史沉积中,而某些玲珑之短诗,却能够经历史年代之久而独放异彩。这首《偶然》,只有两段十行的小诗,在现代诗歌长廊中,堪称别备一格之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特立独行、谜一般的传奇人物:想作诗便作得一手好诗,为新诗创立新格;想写散文便把散文写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想恋爱便爱得昏天黑地无所顾忌……一个深信人生必须有爱、自由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诗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他的心永远是人间四月的天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没有他的诗坛是寂寞的。
爱与哀愁
传世的不仅是他的诗作,还有绵延深远的爱情。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15岁的张幼仪娶进了门。张幼仪出身江苏名门,受过新式教育,性情温和善良,长相明眸清丽,知书达理又遵传统守孝道。婚后不久,长子徐积锴出生,徐志摩便赴英国读书。其时,徐志摩一心追求林徽因,提出离婚。虽然身怀有孕,张幼仪还是慨然应允徐志摩,结束了他们七年的婚姻。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获成功。难能可贵的是,她仍照样孝敬徐志摩的双亲,精心抚育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
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写道:“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她对徐志摩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诗人最著名的情感经历,莫过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徐林”世纪之恋。1921年秋天,与林徽因的初次邂逅,是在与狄更生的会见中。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好,一个是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恋爱,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写了《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诸多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起接待,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共同担任翻译。但冰雪聪明的林徽因始终清楚,徐志摩只是她生命中的惊鸿一瞥,只是一次漂亮的过错。“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这一句是林徽因发自肺腑的对徐志摩的真情告白。林徽因用她女人特有的心智,结束了和徐志摩一段无望的爱恋。
1931年,徐志摩为了去听她的报告,在碧海蓝天中,把他35岁的生命回报给了至爱的林徽因。后来,林徽因把他飞机出事的那块残骸永恒地寄存在她的卧室里,林徽因知道,她是最懂他的女人。
1922年,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认识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开启了诗人的另一段浪漫而热烈的恋情。陆小曼是北京的社交名媛,才貌双全、机智活泼、人见犹怜。这一时期写下的《爱眉小札》,浓烈炽热的文字,吐露着爱人的缠绵深情。
然而这一段不被世俗包容、不被世人看好的婚姻,或许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在刚结婚的前段日子里,虽然徐父徐母对陆小曼依然心有不满,但是两人也算过得浪漫惬意。由于陆小曼从小过惯了奢逸的生活,为了使妻子心喜,他一味迁就她。后来,徐父出于对陆小曼的极度不满,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他不得不同时在不同的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补贴家用,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家庭的花销。
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嘘,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

天妒英才
1931年11月19日,为了赶到北京参加林徽因给外国使节讲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讲座,徐志摩搭乘的航班失事,不幸罹难,时年35岁。
听到噩耗的那一刹那,林徽因一下晕倒过去,醒来后,感到一根针刺触到心底,天地如墨一般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她的嗓子,良久没有说话。直到半个月以后,才蘸满泪水给《北京晨报》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文章——《悼志摩》。长歌当哭、锥心泣血、不胜哀痛!
英年早逝,消息传来,北京、上海文艺界沉浸在一片悲伤中。徐志摩的灵柩运到上海万国殡仪馆,上海文艺界在静安寺设奠,举行追悼仪式,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许多青年学生排着队来瞻仰这位中国的拜伦。
北平的公祭设在北大二院大礼堂,由林徽因主持安排,胡适、周作人、杨振声等到会致哀,京都的社会贤达和故友纷纷题写挽联、挽诗和祭文。
蔡元培的挽联是: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梅兰芳的挽联一唱三叹:
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着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笑貌;
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黄炎培的诗长歌当哭:
天纵奇才死亦奇,云车风马想威仪。
卅年哀乐春婆梦,留与人间一卷诗。
白门哀柳锁斜烟,黑水寒鼙动九边。
料得神州无死所,故飞吟蜕入寥天。
新月娟娟笔一支,是清非薄不凡姿。
光华十里联秋驾,哭到交情意已私。
……
徐志摩去世后,其墓地也是一波三折,一共经过了三次变迁。第一次是在东山玛瑙谷万石窝,由胡适之题写“诗人徐志摩之墓”碑文,在动乱中荡然无存。第二次,徐父对于胡适先生题字的墓碑感觉过于简短,又请到徐志摩生前红颜知己,被称为闺秀派才女的凌叔华,请她为徐志摩再题一块碑文。凌叔华欣然应允,她所题碑文取自曹雪芹“冷月葬花魂”的寓意,转化为“冷月照诗魂”。此块墓碑也在动乱中丧失。第三次,徐志摩的墓地因动乱坟陵早已损毁,故乡百姓为了表示纪念,由政府拨款把墓地迁葬到西山北麓白水泉边。徐志摩的外亲、著名建筑学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设计并撰写墓记。西山墓地古典雅致,白石铺地,青石为阶,半圆的墓台恰似一弯新月,有诗坛“新月派”的寓意。墓碑沧桑厚朴,海宁籍书法大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先生根据胡适之原文补题碑文。墓碑两侧各有一方白石做就的书形雕塑,刻着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名诗名句。
徐志摩之死,陆小曼便成了众矢之的,但她默默忍受着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正如她在致志摩挽联中说:“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志摩走了,她的心也死了,怀念志摩的方式,便是致力于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其中的苦辣酸甜岂是常人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