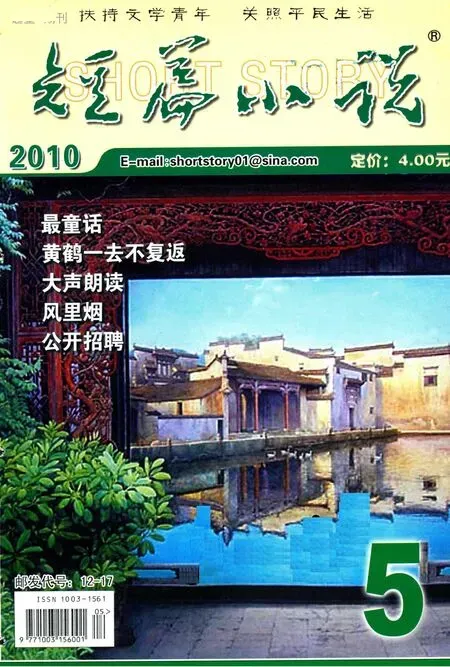年
2016-07-12碎红如绣
◎碎红如绣
一、严关
年是一种凶猛的动物,老婆也是。
前者出自传说,后者源于严关的亲身体验。老婆大人腰圆臂宽,环眉豹眼,堪比莽汉李逵。严关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被李逵拿捏在手,引发得旁人啧啧慨叹。
但是老婆有她的妙处。比如逢年。老婆大人横刀立马地往前一跨,讨债的都会抖三抖,老婆大人再咆哮两声,债主不是两腿抽筋就是两脚抹油。老婆是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存折数字后面画出六个圈七个圈,她还是建筑师,把屋子的面积从五十平米变到一百平米再变到三百平米。总而言之,老婆就像满室的红木古董家具,不耐看却很实用。
严关时常感慨造物主的神奇安排,它为雄壮的老婆安配了一颗比针眼还小的心脏。前些天翁康来借钱,老婆挡在门坎,睥睨四周口生莲花:“这年难过呀,去年的尾款还没收回来今年又垫进去几十万再下去我一家老小就要喝西北风了还是你们打工的好每月定时领薪不愁吃不愁穿乡下有房也不用还贷别看我们表面光鲜实际上苦不堪言哇。”
老婆大人的第二项专长是说话不断句,噼哩啪啦叽叽呱呱,比讲加多宝的那个四眼男生还能不歇气。严关曾试想过老婆当上主持人会是什么形象,才闪念就打了个激灵。
相比马小花,老婆实在太伟岸了。
二、马小花
严关以为会和马小花终成眷属。
马小花娇小玲珑,眼睛横过来就是一湾泉,泉水咕嘟嘟地冒着欢快的泡泡儿。严关和翁康都喜欢她。严关能言善道,幽默风趣,常把马小花逗得乐不可支。翁康站在一旁编草环,一顶两顶三顶,扣着马小花脑门大小箍,严关曾半开玩笑地说:
“翁康,等以后我娶老婆,你也给她编一顶花环吧。”
严关的眼睛向马小花溜一溜,她抿着嘴低着头,严关不禁想起有一首诗,诗句是这么写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好似一朵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发展势态必须是水到渠成。谁料想进城后马小花会和木讷的翁康配成对,苍天无眼哪。噢,苍天瞎了两次眼,第一次错把老婆肥厚的手塞进他的掌心,第二次就是现在,瘦成一枝竹的翁康安静听完老婆大人的宏篇伟论,他的目光准确在自己面上定位:
“严关,顺便通知你,我和小花这趟回家过年顺便摆酒,你如果回来过年,记得来喝酒。”
三、年
世界上唯一痛恨“年”的当属老婆大人。
老婆大人姓胡,单名一个玫字。胡玫痛恨过年,它意味着会有大大小小的讨债鬼不约而同地排在门口唱起颂歌:过年啦,老板娘心善发红包啦!这些字句像一柄柄小李飞刀,嗖嗖嗖地扎在老婆大人针眼大的心坎上。严关耳朵软,懵懵懂懂被灌了迷魂汤,来跟她商量:
过年了,大家都不容易,把款子给结了吧。
工程完工了,让他们过个欢喜年吧。
胡玫眼一瞪嘴一翘,吓得严关绊一跤。
“工程虽然结束了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留下尾巴现在还没有验收就让我付款我又不是傻X由着他们说说戏弄得了的。”
严关不吱声,垂头耷脑接受批判:哪有你这样的笨蛋白痴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有没有大脑有没有辨析力难怪一辈子都这么窝囊。
补充交待:那年北风猎猎,严关揣着口袋的最后五毛钱,跌倒在老婆家门前,是老婆甩出一只大肉包救了他的胃。后来严关想那会儿他一定饿得够呛,才会感觉老婆的一张大饼脸入眼入心,又暖又香。
严关轻声问:“今年,又不回?”
老婆不假思索:“那个破地方回它干啥你要么让两个老家伙来城里过年要么就随他们去我话事先申明要替你二弟盖房子那是门都没有我的钱也是一点一滴节衣缩食存起来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严关嚅嚅地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只能无语。
四、翁康
计划之中,意料之外。
严关惧妻不算新鲜事。若非那可恶的蝥贼偷走大半年的血汗钱,翁康是不会想到找严关救急的。扳指计算,严关离得最近,家境最好。胡玫二话不说,抡起板斧劈开了他与严关的那点情份,马小花就有些愤慨不平:
“当年若不是你——”
“不提当年。”翁康说,当年是什么?是根鸡毛不值一提。无非严关走投无路,问他借过三百元钱。那时候都一穷二白。
但是严关记得,三百元,重于泰山。严关声情并茂,向老婆大人叙述了一幅感人至深情同手足的故事,老婆闭上双眼抽了抽鼻子,然后拿出计算器噼噼啪啪按一阵,甩到严关眼前:
“七百三十二块两毛六分。三百块,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
严关只好小心翼翼贡献出私房钱,连同老婆的同期利息,一共五千七百三十二块二毛六,严关把它交给翁康的时候眼眶濡湿,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并不卑小。临走前他回望了一眼马小花,她站在那枚大红窗花下,依旧美艳。
严关说:“麻烦你们将这里的一千块交给我爸妈,转告他们我忙,不能回家过节,其他的,算是给你们的贺礼。”
五、新桃旧符
严关小时候喜欢听戏,每逢年节,晒谷场上临时搭建了戏台,请剧团的人来唱。《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歌者豪气冲天,听者如痴似醉。等唱戏的离开,台子还来不及拆解,严关会跑上戏台学着哼一两嗓子。父亲坐在台下,明晃晃的月光盛开在他的膝上,像一团团炸开的蒲公英。
月色里,两个摇头晃脑的影子,一只父亲,一只严关。
自从有了老婆大人,严关不得不遵守侍妇从妇之道,胡玫是从不听戏的。
胡玫爱听那些咿咿歪歪的歌,你是我的蝴蝶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严关牵挂不起来,猫进书房,想念戏台、父亲、白月光。
年前,母亲说父亲身体抱恙,不知好些了没有。
翁康快到家了吧。
严关能看见母亲黯然的目光。
这是连续第三年没有回乡过年了。严关鼻酸目赤,厅里的歌声宛转一折,忽然转为尖锐高亢: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严关猛地再打一个激灵。
六、横祸
老婆大人也有她的死穴,譬如你当她面夸别的姑娘好看,譬如批评她不会烧饭(也只能是其他人,严关怎么胆敢批评呢),譬如严小宝。
眼下,严小宝出了状况。严小宝哇哇的哭声隔着听筒传来,老婆急得脸色煞白,庞大的身躯摇摇欲坠。你们有什么要求不要伤害我家小宝我统统想办法满足你小宝胆子小又怕黑你们千万别吓着他——
“闭嘴!”对方说,“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老婆颤颤巍巍回答:“我还,我一定还。”
严关家的香火九代单传,严小宝可不能有所闪失。外面大雪如麻,严关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雪地上,若干年前,父亲也曾在雪花如此纷繁的天气踉跄行进,背着他去医院就诊,严关记得那天是初一,雪地上还残留着赤红的鞭炮碎屑,父亲的脖子窝缠了一条“白围巾”,随他急促的脚步颠簸,簌簌落下。
严关又想到刚才收钱那个胡子拉茬一脸憔悴的男人,他的眼睛写满伤心绝望。他抚摸着严小宝的脑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我来不及回家过除夕了。”男人说,“我们整队人都等着这份工钱。”
严小宝忽然仰起脸,亮晶晶的黑瞳仁似一只雀:“我好久没见爷爷啦。”
七、年
严关不是原来那个严关了。
他竟然胆敢在接完翁康电话后即刻包车,要去那个鸟不拉屎的破村落。这一次,老婆大人的威胁恐吓毫不起作用,严关一把钳住她粗短的手臂,瓮声瓮气地说:
“挡我者死。”
严关拿出了戏台武将的胆色,震得胡玫一愣一愣。趁她还在发怔的间隙,严关跳上计程车,车子绝尘驰去。
老婆大人的毛病会传染,翁康结结巴巴说不清楚话。最后还是马小花夺过手机:严关你快回来你父亲跌了一跤摔得很严重现在卧倒在床他很想见你。
严关的眼圈潮湿,奇怪,马小花的话却让人感觉到温暖。
八、新桃旧符
旧门联,破院落。音乐刚刚响起,烛火在风中摇曳。
翁康捎回来一笔钱,说严关赶不及回乡过年。老父亲不相信,天天拄着拐杖到南山俯瞰,天降大雪,南山穿上一层白袄,老父亲眼睛花,滑一跤,骨碌碌滚下山坡。幸好翁康及时请来医生,老父亲的脚才没有残废。
然而翁康为治老父亲的腿脚花掉了五千块钱。
母亲说:严关年中告诉我们今年会回来过年。
又强调:小宝也说会回来看爷爷奶奶。
严关忘记把新更换的手机号告诉老父亲了。他一拍脑门,握着翁康的手讲不出话来。翁康胸前别着大红花,只是木讷地笑,马小花灰着脸,言语淡淡地:比起老人的健康,什么都是次要的。
严关说:“今天年三十,你们就在我家屋里过除夕吧。我送给你们一份特殊的礼物。”
严关的礼物是一出戏剧,他唱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唱得气冲宵汉。唱着唱着,严关感觉自己飞了起来,在半空中旋转,远远眺见奔来一个宽臂厚背的身影,像人,又像传说中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