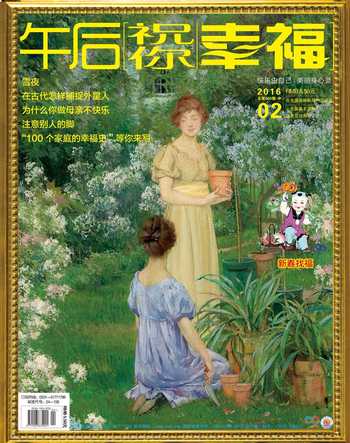过年菜
2016-07-04白峰
白峰,当过警察,做过书店,至今还当着某杂志编辑。无学历、无专业、无职称,属于三无人员。好读杂书,对蟋蟀文化情有独钟,曾出版《中华蛩家斗蟋精要》《蟋蟀古谱评注》等偏门杂书。
中国人过年是个天大的事,出门在外的都要回家,百行百业全都歇了,走亲戚、串门子,凑了一块吃饭聊天。在歌剧《白毛女》里,黄世仁大年三十上门讨债,不让人家过年,特别招人恨。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是韩复榘执政时期,国民政府曾一度改行西元,过元旦,不过春节,春节也就不放假,老百姓该过年还得过年,苦了公务人员,大过年的还得坐班,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感觉活得没滋啦味的,没过几年也就不了了之了。再就是知青下乡那几年,上级号召要过“扎根年”,不许知青回城过年,据说有的知青点哭声一片,社员听得心里直泛酸,再说也不吉祥啊,有的知青点第二年就早早的让知青们回家过年去了。
文化的东西,形成不易,一旦形成,去除和改变也不易。
过年少不了吃,吃还要讲究吃的吉祥。年夜饭,鱼是少不了的,“年年有余”嘛。我小时候社会物资那么困难,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凭购物本可以买到定量的鱼票,这是政府体恤民俗的少数事例之一。
好多小脚老太太,大过年的见了孩子们,还要问吃了这没有?吃了那没有?总之要答出鱼啊什么的,这才算完,就是为了讨个好口彩,然后给每个孩子一颗糖,孩子们也欢喜而去。
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黄土地》里,结婚的喜宴上,没有鱼也要上一道鱼,是用木头雕刻的木鱼,当然不能吃了,这是道看菜,取的就是吉祥有余之意,意思到了,大家也就舒坦了,并不在乎是不是真的有鱼。
即便是在贫困年代,过年的时候,各家各户也都是铆足了劲凑东西,但是年夜饭,豆腐依然名列其间,取“都有福”的意思。豆腐实在是普通的食材,过年了,就不好再做白菜炖豆腐之类了,但是还要有,就衍生出许多复杂的做法,比较典型的要算博山菜里的“豆腐箱子”,大约是将豆腐先过了油,让它成型不易碎,然后挖出空心,填上馅,再盖上盖儿,如此折腾一番,再下锅炖,吃嘛也还是好吃,就是太麻烦。还有一种蹊跷的做法,叫做“富贵有余”,提前将泥鳅用淘米水养上几天,每日换淘米水,吐净肚里的杂物,活鱼下凉水锅,文火煮着,待水温起来,再将嫩豆腐下锅,泥鳅在水中已然热得受不了,遇着凉豆腐,就都钻进去了,进去可就出不来了,加胡椒粉调味,出锅,看着是一块清水豆腐,划开,却有小鱼身在其间,而且不着痕迹。这种做法听上去过于残酷,我从没试过,但也能折射出国人在吃上不知动了多少脑筋。
我没考证过用谐音的办法来注释饮食究竟是起于何时,但是我疑心这种吉祥语大约主要来源于清代。
从瓷器的装饰纹饰上可以看到,宋代崇尚单色釉,没这些讲究,元代有了青花瓷,虽纹饰繁复,但也很少这种隐喻,倒是“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子下山”来得更知名。明代瓷器有文人气,松竹梅常见,云山雾罩的也不少,但是利用谐音作吉祥图案的却不多见。清初瓷器还是刀马人物呢,很快就有了一种图案:一个孩子欢快地指着天上的太阳,这叫“指日高升”,多是康熙朝的东西,这会儿康熙皇帝江山基本坐稳了,反清的力量日渐削弱,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表达的气节,斯时也已不成气候,做清朝的官,也没人指为汉奸了,毕竟大明朝已然远去,可是日子还得过,再说了,谁坐江山和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税照拿。李自成起事的时候有歌谣:“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那是闯王没坐稳江山,真坐稳了江山,该纳粮还得纳粮,朱元璋不就是例子吗?何况大清朝的赋税还比前朝轻许多。人们也就认命了。
又许多年之后,戏剧变成了电视剧,康雍乾全成了盛世。人们也就不大想起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些事儿了。
清初瓷器,器形里有一种桶瓶,取“大清一统”之义,官窑器里常见,可知这种利用谐音说事是有官方背景的。这种习俗的形成我个人揣度大约和女真人的语言有关,满语是一种注音文字,拼出来的是读音,读音后面才连着意思。而汉字是多音字,一字多音,一音多字,入主中原不久的满人在汉化的过程中,一定曾一度充满着困惑。这两种语言方式一对接,弄出这么一种办法,严格说起来是一种半文盲的手段,相当于读白字,实在是俗得很。这倒是和当日里百姓普遍的文化水平偏低能对接,竟然流布开来。
明代的年画里“天官赐福”是常见图案,另有一种时代感极强的年画,是一个老汉撒网打鱼的情景,本以为是勤劳致富、年年有余的意思,读了上面的题记才知道画的是明初的金陵首富沈万三,题曰:“从前有个沈万三,天天打渔在江边,一打打了千千万。”这个题材、这个意思就和今日的福利彩票有着同样的吸引力,人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从此过上不劳而获、为所欲为的好日子。从正面的意义理解,也可以理解為勤劳致富,但是坦率地说有点牵强。打渔的多了,沈万三却只有一个。这个年画大约从明一直穿越大清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在沂蒙山区的大集上见到过,依然卖得不错,不知道这几年还有没有,别看就那么张小小的年画,用的可是明代的板子,数百年的反复拓印,字口明显磨损不复当初的硬朗,但是依然刺激、爽朗、喜庆,当初忘了收藏几张了,今日想来很是后悔。
清代的年画里,谐音吉祥图案就非常多了,多到已经无须举例,大家随便想想就能想起一大堆来。映射在饮食文化上,过年菜也就多和吉祥有了牵扯。比如平日里的乱炖,这会儿就叫“全家福”。
对于俺这种儿童时期正赶上物资贫乏时代的人来说,过年菜里最有好感的还是“炸松肉”,赶年下,炸上一大盆,蘸椒盐,香;炖菜,也香。尤其是在外面无事忙地瞎跑一气,跑饿了,回家摸一块炸松肉,又赶上是块肥的,一咬满嘴流油,别提多香了。今天的人已经没多少人敢吃这个了,吃一块,就得喝半天的铁观音或是老班章,成本大了去了。要不然就得吃药了,为了香那一口,费这劲,不值得,所以多数人家都改了炸里脊。炸藕合也是不可少的,有“百年好合”之义,吉祥。
吉祥菜细数下来怕是超过百种不止,大家茶余饭后倘若闲来无事,不妨数数,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显得俺没觉悟。俺小时候可是听着《国际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过年了,吉祥话该说还得说,吃好喝好,养好了膘开了春接着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