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风云(十五)
2016-07-02内尔森德米勒
内尔森?德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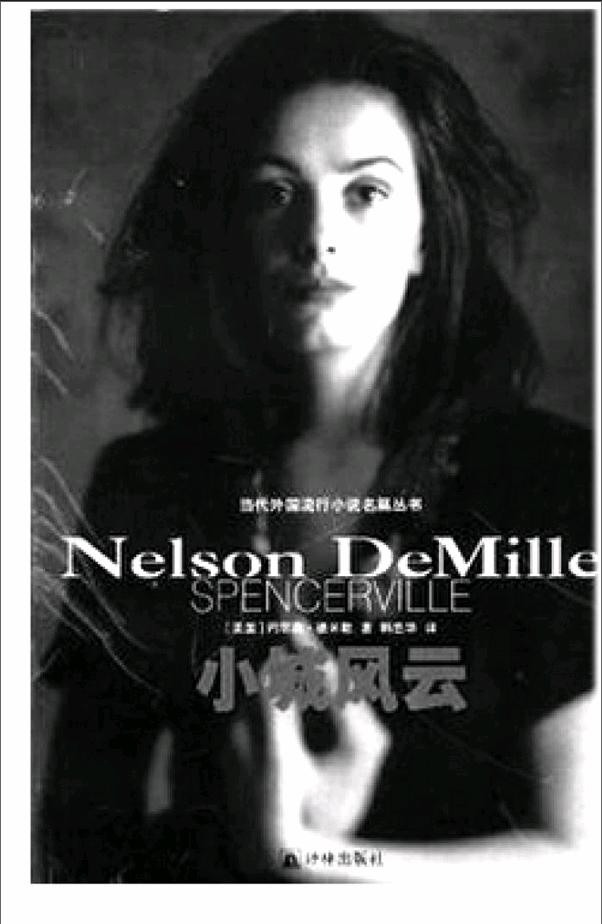
冷战结束了,大批冷战战士纷纷奉命退役。服役二十五年之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上校军官基思带着对美国政府的失望和厌恶离开了华盛顿,回到他的家久——大俄亥俄的小城斯潘塞,那儿,有他钟爱一生的女人安妮。安妮的丈夫克利夫是斯潘塞城的警长。这个色厉内荏的恶棍一面把安妮当个囚徒似的成天派人监视着,一面又在外面鬼混,二十五年来,安妮没有尝过幸福的滋昧。爱的激情使再度重逢的基思与安妮再也无法分开。但是基思和克利夫两人,必须有一个让步,或者,必须有一个死……
第39章
克基思坐立不安,但他知道时间越晚,逮住巴克斯特的机会就越多。他提醒自己,攻击一方始终具有出其不意和机动灵活的优势,更不用说对战斗做好心理准备了;防守一方则占有选择地利和做好布置的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条件的舒适。但正是这最后一点,有时使防守一方斗志麻痹,沉醉在致命的安全感里。
比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玻璃纸袋,把它撕开。
“你要吃点花生米吗?”
“不要。”
比利嚼着花生米,他说:“也许我们不必杀死狗。现在我已经看清他那边的布置,我想我们可以远距离袭击他。我们只要在空地边缘摆好射击姿势,发出响声,狗就会叫,他就会出来上那个高高的平台,这时我们就开枪打这头蠢驴,我们有瞄准器,可以每次打出两三发弹,让他来不及知道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击了他。”
“他穿着防弹背心呢。”
“啊,去他妈的背心。这些弹雨点般射到他身上,就是裹着背心也要受伤。也许击一只臂膀或一条腿,也许击这龟孙的脑袋,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你想的这个主意。好吧,就算他被击倒,然后怎么办?”
“好,他倒下以后,你快速前进——冲一百码到达房,登上平台,这也许要花十二三秒钟,同时我仍趴着掩护你。这样,如果他从平台上爬起来,我再开枪打他,如果你到那里他还不断气,你就割破他的喉咙,然后我上来挖出他的五脏腑。不是瞎扯,基思,我将把他开膛剖肚。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来冲上去,你躺着掩护。你下号令,尉。”
基思瞥了比利-马隆一眼。显然,比利洋洋自得;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他说:“标准的火力和布置,不错,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对。不管谁躺着,火力是安全的。冲向房的人得信赖另一人的射击本领。你的枪法准吗?”
“相当不错。你呢?”
马隆犹豫了一下,说道:“过去是最好的枪手。现在取决于我能保持多镇定。”
“那你能保持多镇定呢?”
“对付这个龟孙,我稳如磐石。”
基思点点头。他掂量着比利的主意。步兵学校的教官们会赞成这个主意。然而,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对方有个人质是一个因素;基思欲同巴克斯特面对面算账,这是另一个因素。战术课上没有讲授过这些,甚至情报学校也没讲过,报仇雪恨是全靠自学而得的。他对比利说:“巴克斯特有可能在受重伤之前找到掩蔽物,他可以绕到房的另一侧,或者更糟的是他可以退回到屋内。”
“是啊……可……”
“瞧,一百码射击不算太远,但现在是晚上,再加上那家伙穿着防弹背心,打不会把事情搞砸了,我不想让他退回屋里去。”
比利点点头,说道:“所以你或我得冲过那片空地,像飞毛腿一样快,不等他反应过来就扑到他身上。即使他逃回屋内,他也得受伤。”
“他可能会杀了她。”
“基思,他会被打,因为我们俩在那个距离用瞄准器不会打不。即使他退回屋里,他心考虑的只是我们和他自己。他不会去碰她的。”
“也许吧。”
“嗨,你心里还有其他想法?”
“对,我有。我担心的是我们俩有一个碰巧击他的脑袋。”基思又说,“我不愿让他很快死去。这是我的出发点。你该知道。”
比利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点头。“是啊……我已经估摸到了。我说,我不想让他前一秒钟还站着,后一秒钟就咽了气;弹穿过大脑,没有痛苦,没有四目对视。老天,我真想活活把他开膛剖肚。活杀他,基思,把他的肠拉出来放在他面前,冉盯着他的眼睛看。不过,如果你认为我们必须爬到那所房前,乘他不防时逮住他,我不赞成。我没那个胆量。你有吗?”
“有。”
“好吧,那你向前冲,我从树林掩护你。但你得先解决掉这些狗。”
“对。所以我买了石弓。这是对低技术问题采取的低技术解决方法。”
“我想是这样。”比利补充道,“嗨,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能做什么是两码事。我考虑的是怎样除掉这龟孙的安全办法,你给我讲的却是突击队的那些鬼把戏。”
“比利,不管用哪一种办法,你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在树丛摆好射击姿势。”
“嗨,我不担心我这无用的躯壳。但我不希望你在那片空旷地上挨黑枪,或者进屋发觉了埋伏。到那时我帮不上忙,老兄。”他说,“我的想法是:当我们接近他时,他不是死了,就是重伤。不论哪种情况,我都把他开膛剖肚。”
基思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比利:“我想要活捉他。”
“不行。”
“我要把他捆起来,扔在小卡车后面,交给司法部门处理。我一直在这样想,这就是我选择的办法。你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基思,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宁可死,也不愿去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可我得告诉你,该死的法律执行起来真荒唐。法律把我折腾得够呛,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我从不伤害别人,那个龟孙却能逍遥法外。”
基思思索着这个问题。巴克斯特会面临种种羞辱,然而一两年后他又可以在社会上无拘无束了。克利夫-巴克斯特有病,州法院可能会同意巴克斯特的律师的看法,说他需要治疗和接受心理咨询。他有精神创伤,因为看到他的妻与另一个男人睡觉——一个来自乡下的狡猾的诱奸者。于是,他做了任何男人都会做的事:他打了她妻的那个情夫,然后,他不是把他妻一脚踢出门外,而是带她出去度个短假,试图解决矛盾。当然,他做得过分了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原因,基思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尽管他答应过安妮不杀人,但克利夫-巴克斯特必须死。他说:“行……我们结果他。但我必须靠近杀他。他必须明白是我和你干的。”
“好吧……如果那样做对你合适,我没有意见,我赞成。希望我们能成功。”
“我们会成功的。”
比利说:“嗨,等我们收拾了这混蛋以后,我就到哥伦布去找她。他一天不死我就一天不能去找她。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过去对任何人都不敢正视,基思,我在城内闲荡,我在街上见到他,他就会嘲笑我。有时他见我喝醉就逮捕我,把我带进局里,让我脱光衣服进行搜身。这畜生还叫人给我拍照,有些照片上他就站在我身旁,他说他把这些照片寄给贝思。”
基思不做声。
“也许你弄不懂为什么我到处闲荡。我告诉你,因为我试图鼓起勇气杀他,但我始终没这个勇气……看来我永远鼓不起这个勇气来。一直到你来我才有了勇气。”他又说,“记住,如果我不成功……”
“行了,够了。”基思看看比利,他正背靠树坐着,凝视着黑暗深处。基思心想,比利-马隆现在清醒着,具有所有无望之人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他也许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基思觉得他的话兴许有道理,他想,比利已达到他一生那些难得的时刻之一,也许是最难得的时刻,即生或死同样美好的时刻。
他们等待着,听着秋夜时有的声音——一只金花鼠、一只松鼠、一头野兔或偶尔一只鸟。基思抬头望望明月,此时月亮差不多正当头顶。也许三四个小时后月亮就会西沉,那将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不过,如果他想用石弓射狗,那就需要月光了。
基思不愿去猜测屋内正在发生什么事,但他仍不由自主地猜度着。毫无疑问,克利夫-巴克斯特的精神已经崩溃,他的占有欲已转化为更为丑恶的东西。基思知道巴克斯特会殴打安妮,因她的不忠而侮辱她,惩罚她。事实上,巴克斯特是个**狂;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借口,来对他从未完全征服的女人发泄病态的离奇**。基思坚信,巴克斯特还没有制服她;当他看到她时,她会像他一样——挨打流血,但并不屈服。
他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以对付即将来临的局面。他的举动必须合理、冷静,与巴克斯特同样狡猾。他知道巴克斯特随时会杀她,但他相当肯定,巴克斯特还没有与她了结。他们之间目前正发生的事是巴克斯特一生所做的最精心的事,他不打算去结束它,除非到最后时刻,现在正是最后时刻,他们冤家狭路相逢,所有的事都集到了一起来:救援、复仇和偿还,都期待已久。
比利说:“我有一种感觉,他知道我们来了,我的意思是,他不了解,但他知道。”
基思说:“这无关紧要。它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对他或对我们都一样。”
“对。他已经走投无路。”他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想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可以离开,但我们不能离开。你知道吗?”
“我知道。”
“嗨,我能抽支烟就好了。”
“你需要喝一口吗?”
“嗯……你有喝的东西?”
“没有。我是在问你是否需要喝酒。”
“我……需要。不过……现在不行。”
“你知道,也许这事了结以后你的生活能够重新开始,如果你戒掉酒的话。”
“也许能。”
“我将帮助你。”
“算了吧。我们扯平了。”比利问道,“你想过我们很倒霉吗?”
“想过。那又怎样?一次大战以来,每个老兵都很倒霉,也许你不该再为你自己感到可惜。没有一场战争会长得或是糟糕得比你自己更能把你的头脑搞得那么糊涂。”
比利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也许你的头脑不会。你的头脑总是清醒的。可我的头脑接受不了太多的东西。”
“对不起。”
“告诉你一点别的,基思——如果你不认为你也有点心神不定的话,你就不会听从你脑袋里那些华而不实的想法了。”
基思不吭声。
他们又等了一小时,基本上沉默不语。最后,比利说道:“嗨,还记得我们毕业那年与芬德利队的橄榄球赛吗?”
“记不得了。”
“那天我踢卫,我们以七比十二的比分落后,我接过传球,甩掉左边对方那个抱住我的队员,他们在争球线拦住我,但我没倒下——我转身将球传给你。你那天踢后卫,记得吗?芬德利队的那些讨厌鬼都扑到你身上,但你把球一个长传扔给边锋——那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戴维斯。对吗?他还反应不过来,但他转过身,球落在他手里,他倒在球门区。触地得分,你记得吗?”
“记得。”
“这场球棒极了。你大出风头。即使形势不利,只要你在那里,就能抓住一个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保存着那场球的记录片。”
“有可能。”
“是吗,我想看看那片。你从学起就记得巴克斯特吗?”
“不……实际上,我记得。”
“嗯,他始终是个祸害。你曾经与他正面较量过吗?”
“没有,但我早该这样做。”
“君报仇,十年不晚。”
“这正是他想的,这也是我们都到这里来的原因。”
“是啊……不过我们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惹过他。我从来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他尽欺负别人。我弄不懂为什么没有人早早地把他的气焰给压下去。”
基思说道:“他专拣软柿捏。”
比利-马隆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说:“喂,他真的在你头上撒尿了。”他大笑,接着说道,“听我说,我在酒吧见到你以后,好像是第二天我头脑清醒过来时,我记起你和安妮-普伦蒂斯的事。我头脑有一种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你将与她相聚,一起找回失去的东西。这算不算聪明的想法?”
基思不回答。
比利继续说:“我猜测他也估摸出这件事。你知道,我过去有时在街上看到她——我是说,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她,但由于我们曾经是同班同学,她总是向我微笑,打招呼。有时候,她停下来,同我交谈几句,你知道,问我近来可好。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想:‘你的丈夫糟蹋了我的妻,我应该告诉你这件事。可实际上,我从未告诉过她。我不想谈得时间太长,因为我怕若被他看见我与他妻谈话,他会报复我,或者虐待她。”
基思说:“也许我应该让你将他开膛剖肚。”
比利看着他,说道:“这事我不需要你的许可。”
这话有点使基思出乎意料,但对比利来说,是个好兆头。基思说:“我们讲好的,我发号施令。”
比利不吱声了。
又过了一小时,天气变得寒冷了,基思看了一下表:十点钟。他急于想采取行动,但还太早,巴克斯特还醒着,警觉着,他的狗也如此。
基思看到月亮已偏西南,估计还有两三个小时的月光。
基思说:“好吧,告诉你我们的行动方案。乘有月光时我们把几条狗给收拾了,等到月亮下山,我冲过那片空旷地,你掩护。我爬上平台,在靠近玻璃拉门的地方背贴墙壁。行吗?”
“到目前为止还行。”
“现在你得引他出来,你会学狗叫吗?”
“当然会。”
“好,你一学狗叫,他就会出来,就像刚才那样。不过,这一次我在他背后用手枪顶着他的头。简单而又安全。你觉得有问题吗?”
“听起来没问题……这些计划听起来总是不错,不是吗?”
“对。有时候这些计划甚至很管用。”
比利笑了。“记得课堂里挂着黑板上橄榄球课吗?每场球都是触地得分。军队也是一样,可课堂上从来不讲当你的弟兄们伤亡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敌方正玩什么鬼花样来搞乱你的阵脚。”
“这就是生活。”
“是啊。”他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想我把自己弄糟了,我不要坏蛋来欺负我。”他又说,“不过我闲荡的时间够长了,现在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在又冷又黑的树林等着,用帆布雨披裹着身体。到午夜时,基思站起来,雨披掉在地上。他说道:“我们行动吧。”
第40章
克利夫-巴克斯特放下杂志,打了个哈欠,他喝光一罐啤酒,从纸袋里掏出一把椒盐脆饼吃着。他看看坐在摇椅上的妻,把几块脆饼扔到她的毯上。“别说我从来不请你客。吃吧。”
她对脆饼看都没看,也不回答。
他说:“准备睡觉吗,亲爱的?”
她仍望着即将熄灭的炉火,回答道:“不,我只想坐在这里。”
“是吗?坐一夜?”
“是的。”
“那么我抱着谁睡呢?”
“反正不是我,我被锁链拴在床头上。”
“是手铐铐住,不是拴住。”
“这对我有什么两样?”
“嗨,如果我能信任你,你就不会被拴在地板上或者铐在床上,什么都不用。我能信任你吗?”
“能。”
他大笑。“能?我能信任你把我脑袋炸开花吧。”
她看着他。“你怕我?”
他眯起眼睛,说道:“我怕任何会扳扳机的人。我不是傻瓜。”
安妮说:“对,你不是,可你……”
“什么?”
“你不信任别人,克利夫。你懂得怎样去信任别人吗?”
“不懂。为什么我该信任别人?为什么我该信任你?”
“如果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你,你会松开我吗?”
“不行。干吗为了手铐的事这样小题大做?”
“干吗?因为我不愿像动物一样被拴住。这就是干吗。”
“噢,你没有像动物一样被拴住,动物有更多的自由。”他大笑。“你像被逮捕法办的重罪犯人一样被锁起来。外面的猎狗从不做错事,所以它们能走动一百码左右,你惹了麻烦,女士。大麻烦,也许几星期后,我将把你钩在狗道铁丝网上,那时候你可以说你像动物一样被拴住,可以谢谢我了。”
安妮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克利夫……我那次曾经有机会杀死你……杀人不是我的本性。请相信……你知道的。你自己也这样说过。今天晚上让我不戴手铐睡觉吧,我手腕铐在床头板上睡不着。求你了。我向你发誓,我不会伤害你。”
“是吗?那就是说我醒来会发现自己被铐在床头而你早走了。对吧?对吧?嗨,不必回答。”他向她俯下身去。“这倒提醒了我。下次你要撒尿,可以就地撒。”
“克利夫……求你……”
“然后打扫干净。”他补充道,“但不能尿在床上。”他又打了个呵欠。“这么说,你宁可整夜睡在这张该死的椅上也不愿与我同睡?”
她摇摇头,“不……对不起。我不想整夜坐在这里。我要上床。”她又说,“我得上厕所。”
“是吗?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别动,对你有好处。”他向她走过来,掀开她身上的毯,把它扔到屋那头去,“冻你个半死,在你的椅上撒尿吧。”
“畜生。”
他狠狠拧了她面颊一把。“明天早晨你得挨十下屁股。整个晚上好好想想。不给早饭吃。你可以坐在自己撒的尿上,闻我做火腿煎鸡蛋的香味。”
他走到枪架前,开了锁,拿下那支AK-47,再锁上枪架。“我宁可与枪睡也不与你睡,枪比你还暖和呢。”
她坐在摇椅上,双臂抱着身,眼睛望着尚在发光的余烬。
他问:“你要我加一根木柴吗?”
她不回答。
“不管怎么说,不打算再加了。”
她看看他,说道:“克利夫,求你……对不起。别留我在这里。我冷,我得——”
“你应当好好想想再张开你的嘴,记得我养的那条德国短毛猎犬吧?老是冲着我叫,有一次还咬了我,好多人劝我枪毙它。嗯,任何人都会那样做。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教它懂得谁是主人,不是吗?结果调教成我养过的狗最好的一条。你也会这样,亲爱的。”
她站起身来。“我不是狗!我是人,一个人。我是你妻……”
“不!你曾经是我妻。现在你是我的财产。”
“我不是!”
克利夫把她推回摇椅,俯身站着,他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用讽刺的语调说:“好吧,那么,如果你曾经是我的妻,你该戴着结婚戒指才对,可我看你手上没有。”
她不吱声。
“如果你能找到你的结婚戒指,才能谈得上你是我妻。想一想,丢在哪儿了?”
她仍沉默不语。
“见鬼,你不需要戒指。你有脚镣和手铐。其实,我多年前就应该给你戴上这些玩意儿了,还得加一条贞洁带,不让你这**出事。老天作证,你根本没把婚姻誓言当真。”
“你……”
“什么?你想说我到处玩女人吧,那又怎么样?可我要告诉你——这些女人对我来说算个屁,如果你安分守己,我就不会四处拈花惹草;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也在搞婚外恋,不是吗?”
她不吭声。
他靠近她一些,她在椅上转过身去。他说:“看着我。”
她勉强转过身来对着他。
他说道:“你认为我会忘记我在汽车旅馆里看到的事吗?我不是说你跟他睡觉的事。见鬼,我曾想象过你与野男人多次上床。我是说你竟扑在我身上,所以他能……他能试图杀我,我是说你伏在他身上,弄得我无法砸烂他的狗头,你以为我会忘记这些?我会吗?”
“不会。”
“是不会。永远不会。”
基思和比利跪在空旷地的边缘。
比利通过步枪上的望远瞄准器扫视,基思则将双筒望远镜对准房。屋内有盏灯还亮着,但并不是基思刚才看到的靠近玻璃滑动门的那盏灯。这盏灯光线较弱,光来自他看到安妮身影的那扇老虎窗,靠近房央,那里有烟囱穿过屋顶。他猜想,这光线来自一盏台灯,他看不到有其他灯开着,也看不到壁炉里火焰的光,虽然烟还从烟囱里飘出来,烟仍然向他们飘过来,说明他和比利依旧在狗的下风,这是有利的。
他继续通过望远镜观察着房,从窗口看不到动静和人影。他也看不到易于暴露的电视机的蓝白色闪光;电视机本来会在屋内产生背景声音,对他们的进攻有利。当然,还可能有收音机或音带的声音,但基思深信巴克斯特不会为自己创造一个不利条件。如果基思必须猜测现在屋内正在发生什么——他的确只能猜测,他会说其一人或他们两人仍醒着,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也许在阅读,也许在谈话。他也推测安妮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否则巴克斯特就得时时刻刻提防着。
基思扫视房周围的开阔地。他看见那金毛拾-在狗道靠湖的远端趴在地上,也许是睡着了,他注意到另一条狗,在湖光的映衬下现出轮廓。这条狗在湖岸边走动,似乎也圈在一条沿灰湖走向的铁丝网狗道上。现在看不到第三条狗,它一定是在房后面的某个地方,他忽然想到,巴克斯特在隐退到他的巢穴之前,早就已经布置好了这些狗哨,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安全。基思想,如果他是巴克斯特的话,他也会采取预防措施的。
基思放下双筒望远镜,比利也放下了步枪,他们几乎纹丝不动,只能相互在耳边低语,怕惊动了狗。比利小声说道:“越来越难看清了。”
基思点点头。月亮现在已落到湖的西南端,离最高的松树仅仅十度。他曾盼望天完全黑下来,想等到下半夜三四点钟行动,那时狗和人都睡得最熟。但如果现在趁看得见时能够消灭这几条狗,那么他可以更好地在那片树林和房之间的空旷地上摸索前进。
他们等待着,希望屋内的灯会在月亮降落在松树后面以前熄掉。
基思拿开望远镜,凝视着房。他凝视的时间越长,它看起来越凶险:这座三角形的建筑物孤零零地高高耸立着,沐浴在月光之;四周是一片故意清理出来的杀人区,微弱的灯光从看不见的房间的某处射出来,此刻,湖面上有薄雾升起,更增加了周围环境的神秘恐怖气氛。基思试图想象房内正在发生什么事;安妮和克利夫-巴克斯特在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相互间在说些什么;既然两人都知道最终结局即将来临,他们会想些什么,感觉又是如何。
安妮继续望着克利夫。她想,过去三天以来第一次,也许是多年来第一次,他们的目光真正相对。许多年来她一直不爱他,他俩都清楚。最近几年以来,她甚至没有像关心一个人那样关心过他。但她从未真心要他吃苦,尽管他待她同样不好,现在,甚至在他给她造成许多**上的痛苦之后,她仍然为他感情上的痛苦感到内疚;她知道这种痛苦是真实而深刻的。她觉得对他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他早已毁了这种感情。不过,她的确希望他不曾看到他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看到的一切。
他似乎觉察到她在想些什么,对她说道:“你从来不会为我那样做。即使二十年前也不会。”
“是的,我不会。”她又说,“对不起,克利夫。真的对不起。你可以打我,强奸我,对我为所欲为,但我只为你感到可怜。也许其部分是我的过错,那就是没有早些离开你。你该早让我走。”
他不答腔,但她能觉察到这几句话对他的分量,她知道,她的话只会使他更加痛苦。然而,事已至此,既然人生已被剥光外衣露出**的本质,而且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话题,那么该是袒露诚实和现实的时候了。她并不认为她的一番话会一下改变他的疯狂状态,事实上这也许会火上浇油,但如果她即将死去,或两人都将死去,她希望他能知道她在临终时的想法。
基思感到那种熟悉的战前镇静支配着他;那是一种思想和**近乎超自然的分离,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知道,这是大多数人投入战斗前的一种心态,但稍后,当战斗开始时,你体内的肾上腺素释放出来,你就会突然摆脱自我克制,你的思想和**就会再度结合。
他想到了安妮。他希望她相信救助即将到来,希望她能坚持到底,即她不屈服,又不过分逼他。
巴克斯特从枪套拔出手枪。他举起它,说道:“这是他的枪。我从他家里偷来的。我要你知道,如果我开枪打你,用的是他的枪。”
“那又怎样?”
他将9毫米格劳克手枪对准她,“你要现在就了结?”
她看看对准她的黑色手枪。她说:“这事由你决定,并不由我。我说什么你都不在乎。”
“当然在乎。你爱我?”
“不。”
“你爱他?”
“是的。”
他顺着枪柄凝视着她,然后却将手枪举向自己的头,打开保险栓。“你要我抠动扳机吗?”
“不要。”
“为什么不?”
“我……克利夫,别……”
“你不想看到我脑浆四溅?”
她转过身去。“不。”
“看着我。”
“不。”
“没关系,如果我脑浆迸射,你拴在地板上将死得很慢很慢。你可以看着我腐烂。你可以闻我腐烂的臭气,正好就在你面前。”
她用手捂住脸,说道:“克利夫……求求你……别折磨我,别折磨你自己……”
“不是你,就是我,亲爱的。哪一个?”
“别这样!快住手!”
“再见了,亲爱的……”
忽然,从某处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基思和比利立刻卧倒。他们等了一下,却听不到第二声枪响,只有一阵犬吠声。
比利小声问:“枪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
“不清楚。”然而听起来很像。这不是户外步枪射击的清晰声音,而是一种不太响的声音,仿佛是房内手枪的射击声。基思举起双筒望远镜,发觉自己的双手发颤。通过窗他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产生了想冲进屋内的冲动,但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已成定局,他已无法挽回。
比利低声说:“保持冷静。我们不明情况。”
“是啊,但很快就会明白的。”
安妮听到手枪响,那震耳欲聋的枪声惊得她跳了起来。她转过头,见他站在那里,手枪在他的一侧,脸上露出微笑。他说:“没打。”他大笑。“吓出尿来了没有?”他又大笑。
安妮双手掩面,啜泣起来。
克利夫拿起他的AK-47、防弹背心和猎枪,关上台灯,让屋内一片漆黑。
她能够听到他在不远处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明天见,亲爱的。”
她不吭声。
“我说了,明天见,亲爱的。”
“明天见。”
“别梦游啊。”他大笑。
她听到他走出房问。
安妮整整一分钟坐着没动,然后睁开双眼。壁炉里的余烬发着微光。她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于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尽管他反常行为的阵阵发作确实使她心惊胆战,但她仍能让他在心头接纳一点劝告,使他按此行事。今天晚上,他不准备自杀或杀她。不过,他一定要她受罪,所以他要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赤身受冻,双脚锁在地板上。到目前为止,一切尚好,她还有一个机会,仅仅一个机会。她从摇椅上滑落下来,滚到地板上,向壁炉爬去。
基思仔细观察着。那扇有亮光的窗户灯熄了,过了几秒钟,房后,很可能是卧室的窗户内灯亮了。一分钟之后,这扇窗内的灯光也熄灭了。他放下双筒望远镜。如果说房间里刚杀了人,另一个然后关灯上床睡觉,这似乎不合逻辑。他宽慰自己,在狩猎的乡村,即使在晚上也有枪声,由于湖水和树林的缘故,很难判定那枪声是从哪儿来的。
他冷静了下来,瞥了比利一眼。比利正看着他,等他说点什么。在这等待发起攻击的时刻,他俩都知道,谈话已经精减到三个命令:行动;放弃;停下。“放弃”不容选择,“停下”则是你想说的,而“行动”则是不可撤销的,基思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