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父母为择校头疼
2016-06-30
Nikole+Hannah-Jones
一所学校如何成为平权运动和种族隔离的战场
2014年春天,我们的女儿娜雅(Najya)4岁了。我和丈夫突然发现,我们正面临成为父母以来最艰难的决定。
我们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史岱文森(Bedford-Stuyvsant, 以下简称“贝德福”),这是一个低收入但正向中产阶级转化的社区,居民绝大多数是黑人。附近的公立学校以发起过黑人民权运动的人物命名,比如1920年代的著名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以及“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的创办人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
这里的学校是纽约种族与社会经济分化的写照。在这座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城市中,这些学校的孩子几乎都是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都来自贫困家庭。贝德福地区学校的考试成绩反映了学生的边缘化处境。
我从没听过身边的任何中产阶级邻居,无论白人还是黑人,会把孩子送去这些学校。他们会设法送孩子读公立学校,或者让孩子参加其他地方的天才学生项目(gifted-and-talented program),甚至会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送到以白人小孩为主的私立学校去。我很清楚这些,是因为自从娜雅1岁时我们搬来纽约之后,就有过很多关于要把孩子送去什么学校的讨论。
一
我的丈夫法拉吉(Faraji)和我都希望把女儿送去公立学校。作为军人家庭的长子,法拉吉上的是为军事基地人员服务的公立学校。因此,他与其他美国黑人小孩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他从没上过公立的隔离学校(segregated school)。他可以随便走进一间屋子,很快跟里面的人聊起来,无论他们是聚在一起参加社区会议的年轻妈妈,还是端着精致小碟出现在豪华鸡尾酒会上的执行董事。
我在艾奥瓦州东北部城市滑铁卢(Waterloo)长大,穿城而过的河流隔开了黑人与白人,也阻断了他们奋斗的机遇。我最早上的是一所以低收入孩子为主的学校。我母亲形容,那简直是令人不安的混乱。对此我倒没有太多记忆,不过我的确记得一年级时班里只有一个白人孩子,虽然很可能不止一个。那个夏天,父母帮姐姐和我报名参加学校的“自愿取消隔离项目”,一个让部分黑人孩子离开他们居住的社区,前往以白人为主、条件更优越的城市北部上学的机会。
那是1982年,自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已经过去了近40年。该案裁定,让白人与黑人孩子在相互隔离的学校接受教育的行为违反美国宪法。那是美国反种族隔离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我父亲选择了一所颜色最“白”、最贵族的学校,认为这会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机会。
二年级开始,我每天早晨坐一个小时巴士,穿过整个小城去“最好”的公立学校金斯利小学(Kingsley Elementary)上学。在那里,我是仅有的几个来自工薪家庭的孩子之一,更是屈指可数的黑人小孩。我总是搭黄色的巴士去学校,是社区里“别人家的孩子”,下课铃一响,我就飞一般地想要跨过大桥回家。
对于那些年的记忆,我总是带着充沛的情感,也有难堪,不过它的确提高了我的成绩,拓宽了我的视野。除了严格的课程与优异的教学质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父母是医生、律师或者科学家的同学家里吃饭。我的母亲是缓刑犯监督官,我的父亲是巴士司机,双方家庭中的大部分成员不是在工厂工作,就是干着其他体力活。我明白,即使在那个时候,出于敏感和某种自我保护,我同学的父母比我邻居的父母要好得多,后者常常以计时工作谋生。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各种可能性,至少是我之前从没设想过的可能性。
很难讲,如果个人经历中的某一处被改写,是否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轨迹受到太多外部或者内部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丝毫没有怀疑过,正是父母把我从隔离学校中“解救”出来的举动,造就了我当下的人生—成为《纽约时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融合,对我丈夫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然而,想要把我们的女儿送去屈指可数的几所融合学校(integrated school)的念头却困扰着我。这些学校主要为中产阶级或者富裕阶级服务,白人孩子是绝对的主流,只有少数几个黑人穷孩子或是拉丁美洲学生,来给所谓的“多样性”撑门面。
在纽约,超过100万名公立学校学生中,白人学生仅占15%,并且一半集中在全市最优质的学校里。白人家长之所以对这些学校趋之若鹜,除了教学本身,还因为同学中有一些有色人种的孩子,但又不是太多。这种小心翼翼又有针对性的融合,常常被不少白人家长拿来吹嘘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简直就像联合国。为此作出牺牲的,是城市中其他黑人和拉丁孩子。
纽约公立学校系统中,41%的学生是拉丁裔,27%是黑人,16%是亚洲人,其中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2014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民权项目(the Civil Right Project)发布报告,指出纽约的公立学校是整个国家中隔离状态最严重的。黑人和拉丁孩子正变得越发孤立。85%的黑人孩子和75%的拉丁孩子就读的是“严重隔离”的学校,在那里,白人孩子的数量不到10%。
这不仅是纽约的问题。我的记者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记录整个国家出现的越发失控的隔离学校状况,以及隔离学校是如何危害黑人和拉丁裔孩子的。2009年《政策分析与管理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ment)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孩子在隔离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成绩越差。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指出,以黑人和拉丁孩子为主的学校,很难聘请到有经验的教师开设高级课程,很难获得充分的教学设备。
如今,大部分黑人和拉丁裔孩子由于种族与社会阶层遭到隔离,这极大地破坏了他们的学习环境。过去50年的研究表明,与家庭经济水平相比,学校的社会经济面貌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更显著。让娜雅就读于白人占主导的学校,就要不可避免地接受这套“两极系统”:一边是资源丰厚、主要是白人孩子和少数来自黑人拉丁裔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学校,另一边是资源贫乏、接纳着城市中绝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孩子的学校。
二
那年春天,我在信箱里收到纽约公立学校目录,我告诉法拉吉,我想让娜雅入读一所隔离的、以来自低收入家庭孩子为主的学校。我向他解释,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给女儿取的名字在斯瓦西里语中正是“自由”的意思—我们就会成为系统的帮凶。法拉吉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的孩子应该享受“优质”的公立学校教育,这种说法就像在暗示,“差”学校里的孩子就理应承担苦果那样。我很清楚,学校的隔离现状是个结构化问题,是由几十年来的住宅隔离、政治考量、政策制定者的算计,或者仅仅是惯性等因素造成的。我同样认为,是每一位家长的决定“滋养”了这个系统,我不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我已经看过太多家长,当他们的融合理念碰到“究竟该把孩子送去什么学校”的现实之后,所造成的种种冲突。
单个家庭,或者说几个家庭,是无法改变一所隔离学校的;但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那么什么改变都不会发生。把我们的孩子送去隔离学校无法改变种族上的融合,不过我们是中产阶级,至少在经济能力上多少能够创造一些“多样性”。作为记者,我看过一所学校是怎么依靠为数不多的几个中产阶级家庭,避免了被漠视的故事。我同样知道,我们有能力为娜雅提供学校所无法提供的一切。
我告诉法拉吉我的想法,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他中意的是教区学校,或者“优质”的公立学校,甚至私立学校。我们争执起来,一路把这件客厅里的“小事”升级到办公室书架上黑人奴隶与民权运动的高度,反反复复,直到陷入僵局。我们心知肚明,回顾这个国家的种族抗争史是多么沉重的话题;我们也知道,对方既正确又错误。法拉吉不愿相信,我竟然要把孩子送去我们两人都尽力逃离的教育环境。他担心如果把娜雅送去都是黑人和穷人的学校会伤害她。“我们是把对公立学校的理想主义放在自己孩子身上做实验吗?”他诘问,“我们是要让她输在起跑线上吗?”
法拉吉最揪心的问题正是我们这样的黑人家庭的痛点。我们来自工薪阶层,通过奋斗跻身中产,没有足够的家族财富或者安全网承担任何闪失。法拉吉认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实在不足以应付孩子可能面临的任何风险—我们必须要把她送去最好的学校。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指出,黑人孩子格外容易堕入向下流动的陷阱—10个中等收入黑人家庭的孩子中,有7个在成年后无法达到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我们没有犯错的空间,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保障娜雅的每一个优势。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吗?他反问,声音里充满了挫败的情绪,为了不让女儿上那些束缚住太多黑人孩子的学校。
最终,我说服他一起去参观几所学校。我们先后去了三所社区里的学校,第四所是307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 307,以下简称307学校)。307学校坐落于布鲁克林区的威里格山(Vinegar Hill),在东河(East River)附近,离我家约几英里。307学校的学区是法拉格特小区(Farragut House)10栋住宅中的5栋。法拉格特是有着3200名居民的公屋小区,位于布鲁克林造船厂附近。学校的学生中,91%是黑人和拉丁裔,10个家庭中有9个符合联邦贫困标准。
学校内部却不像这个城市里接收最贫穷学生的其他学校。这主要得益于它有位卓越的校长罗贝塔·达文波特(Roberta Davenport)。达文波特在法拉格特长大,她妹妹念的就是307学校。2003年,将近60年后,她成了这所表现差强人意的学校的校长。她在康涅狄格州与学校之间通勤,每天早晨她的车总是最早出现在停车场,这多半是因为前一天工作得太晚,精疲力尽,只能到附近的朋友家借宿。她声音柔和,却是个严格的人。307学校的孩子学习中文(普通话),上小提琴课,下国际象棋。由于她的辛勤工作,学校最近还得到了联邦公立拨款,资助了科学、工程和科技项目,以此来吸引学区外的中产家庭孩子入学。
法拉吉与我穿过307学校明亮的大厅,走过摆放着爬行动物标本的科学教室以及正在上钢琴课的教室。墙上装饰着对小学生而言有些深奥的格言。法拉吉后来告诉我,他为自己要把女儿“剔除”出这里而心生愧疚。
三
在提交入学申请时,我们填写了参观过的全部4所学校。2014年5月,娜雅被第一志愿—307学校录取。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有好几次,我受到自身对公平的诘问,我作出了对自己孩子不公平的决定。我始终都在担心,我是否为自己的女儿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我知道,我作出的是最合适的决定。
对诸多美国白人和数百万黑人和拉丁小孩而言,读隔离学校就像一种时代的倒退。这个问题不是早就解决了吗?在法律上,是的。1954年,最高法院作出有标志性意义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裁决,废止了黑人与白人孩子必须在隔离学校念书的规定。然而,该法律只是在国家层面上针对隔离现象的改变,而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的历史甚为漫长,在实际操作中,有太多可以规避的方式。
娜雅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她只明白自己很喜欢307学校,每天醒来就满怀期待地跑去学前班。她在学校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来自法拉格特的黑人小女孩伊玛尼(Imani),另一个是白人小男孩山姆(Sam)。学前班里的白人孩子不多,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经常搭顺风车。4位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有色人种,满怀喜爱之情与专业态度教导着娜雅与她的同学。法拉吉与我也积极投身学校活动,加入学生家长与教师联谊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参加各式集会,陪孩子一同郊游。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大大地舒了口气。
2015年春天,娜雅在学校的第一年临近尾声。我们在新闻里读到,与307学校相距不过1英里、位于相对富裕的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的公立第8学校(Public School 8,以下简称第8学校),正为过度拥挤的问题所困扰。一些原本属于那个学区的学生,原本有可能被划入我们所属的学区,这在地理上怎么都说得通。第8学校位于昂贵的学区,招收的学生从布鲁克林高地的曼哈顿大桥(Manhattan Beidge)至丹波社区(Dumbo)和307学校附近的威里格山。第8学校学区划片时,如今的社区还是工厂和仓库,不过高档住宅逐渐在丹波建起来,包围了坐拥纽约天际线美景与便捷通勤的曼哈顿东河。众多富裕阶层的白人和亚洲孩子住在307学校的河对面,他们被划入绝大部分白人学生就读的第8学校。
为了解决学生数量激增的问题,第8学校已经把戏剧和舞蹈教室改建成了普通教室,取消了学前班,不过每个班的学生数量依旧有28人之多。同时,307学校的教室却空着一半—它的学区仅包括法拉格特的几幢大楼,是整个城市面积最小的学区。由于法拉格特居民的年龄日益增长,学龄儿童数不断下跌,307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
2015年早春,纽约市教育局发出通知,告知申请第8学校幼儿园的50个家庭要么进入等候名单,要么被307学校录取。心烦意乱的家长们纷纷给学校行政部门以及民选官员寄信,要在媒体上曝光自己的遭遇。“我们在这里买了房子,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道可以读(第8学校的)幼儿园。”有家长说,决不会把孩子送去307学校。另外一位双胞胎孩子的家长,由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第8学校的学位,讲起话来更加直截了当。“我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他说,“我从没听过那所学校的什么好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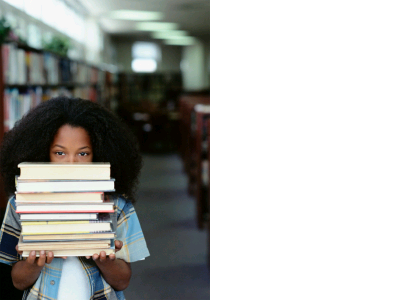
5月,我参加了由第8学校家长组织的会议。礼堂中,我为这些家长展现出的能量而惊讶。一场讨论学校超额收生的会议—仅仅事关整个教育系统100万学生中的50人,就聚集了一位男性州参议员、一位女性州众议员、一位市议会成员,一位市审计官员及数位其他民选官员。我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是融合还是隔离,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究竟谁有左右它的权力。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写过的:“如果黑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就一日无法摆脱拙劣的教育、肮脏的公寓和拮据的经济。”
在数位政客的注视下,两位白人父亲用PPT作了饱含激情的演讲。他们的诉求是,往已经满额的教室里塞进更多学生,而不是让第8学校的学生去307学校上学。另一位演讲人的孩子在等候名单中,在讲到孩子或许无法与玩伴进入同一所学校念书时,他声音哽咽了起来。“我们还没告诉他(没法读第8学校)这件事。”这位父亲眼中凝聚了难解的忧愁,“我们希望永远都不用告诉他。”
四
娜雅和307学校的其他孩子对这场混乱一无所知,家长们发动的抗争完全隔绝在这所学校之外。我丈夫法拉吉那时当选了307学校学生家长和教师联谊会的联合主席,另一位主席是本杰明·格林(Benjamin Greene),同样是来自贝德福社区的黑人中产家长,同时也在社区的教育部门服务。听说有可能重新划分学区,他们的主要工作被迫从集资和活动筹划,转向阻止这个呼之欲出的、可能导致这里变成另一所白人学校的计划。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让还蒙在鼓里的法拉格特居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法拉吉和我都体会到,要跨越法拉格特家庭与黑人中产家庭间的阶级分化是多么困难。家长们个个都很热心,尽管在学校外,我们几乎是分头行动的。当重新划分学区的方案正式提出后,法拉吉和本杰明与在307学校学区内公开教会(Church of the Open Door)的牧师马克·泰勒(Mark Taylor)联手,一一告知那里的家长关于该方案的方方面面。在此之前,没有一位家长听说过它。他们立即感到担心与恐惧:这对他们的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家长知道,307学校是为数不多的几所拥有优质资源的融合学校。
法拉格特的家长对各式会议和媒体上讨论307学校和他们的孩子的措辞感到愤怒和悲伤。数位丹波的家长告诉校长达文波特,除非被安排在同一个教室学习,否则他们不会把孩子送来307学校。法拉格特的家长担心孩子会被边缘化。如果学校最终涌入大量高收入家庭的白人孩子—丹波与威里格山居民的收入中位数是法拉格特居民的10倍,学校本来的特色将会改变,就像之前在第8学校发生的一样,而受害的只会是黑人和拉丁学生。此外,307学校还可能失去资助特别项目的拨款,比如解决低收入家庭困扰的免费托管班。
“我对那些人没意见。”法拉特哥社区的萨依巴·柯莱斯(Saaiba Coles)在讨论重新划区方案的会议上发言,“我只是不希望他们忽视已经在那里念书的学生。”法拉吉与本杰明收集了超过400个法拉格特居民的签名同意重新划区—他们提出条件,包括307学校一半的学位要保留给低收入家庭。这会确保学校在实质上保留融合特色,新来的高收入家长必须在决定学校未来发展方向上分享他们的话语权。
今年1月,教育局重新划区投票。近50位法拉格特的家长搭乘教会的两辆巴士涌入布鲁克林小学(Brooklyn Elementary School)的会堂,坐在一群忧心忡忡的丹波家长身后。这场在布鲁克林展开的融合抗争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公共电台(WNYC)纷纷发表文章。“布鲁克林嬉皮士为取消学校隔离而战”,新闻网站“一手新闻”(Raw Story)如此宣称。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家长们充满热忱地发言,恳请教育局推迟投票,为消除因经济、种族和文化隔阂争取时间。丹波和法拉格特的家长均表达了忧虑,担心如果不从长计议,所谓的融合方案很可能功亏一篑。
最终,投票在教育局主导下进行,通过了重新划区方案,保留低收入家庭50%的学位,307学校学区内的孩子享有优先权。这算不上什么保证,根据普查数据,在新的学区内,5岁以下的白人孩子数量大大超过黑人和拉丁孩子,并且这个数字只会不断上升,学校可能根本无法保障适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数量能达到50%。
教育局主席戴维·戈德史密斯(David Goldsmith)告诉我,他根本不觉得为一所学校保留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位能改变什么。他正着手在整个地区内快加学校的融合进程,包括307学校和第8学校。本杰明·格林为重新划区投下了反对票,他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着有人提出什么宏大的计划。”
对于投票这件事,教育局因推崇融合,被称赞勇敢和大胆。“全国都在看着我们。”戈德史密斯说,“投票‘赞成意味着我们拒绝成为过往经历的受害者。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应该为孩子做的。”
然而这个决定却更像是对维持现状的胜利宣告。重新划区不是为了保障307学校黑人和拉丁孩子的权益,而是出于布鲁克林高地富裕白人家长的考量。第8学校只会变得更“白”、更排外:教育局在会议上没有提到的是,法拉格特社区里原本3栋划入第8学校学区的学生,今后改划入307学校学区,最终令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彻底在第8学校消失,而这间学校也将成为整个纽约最贵族的学校。
307学校的命运也差不多。由于无法保障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位,随着学区内白人孩子数量的增长,学校可能“急转弯”,白人学生成为主流甚至超额收生。法拉格特的家长对此很担心,就像原来第8学校学区的孩子一样,他们的孩子或许在将来无法入读307学校。从今开始,推崇融合的人可能会大失所望:他们将看着307学校是怎么从一所以黑人和拉丁孩子为主的学校,一步步“融合”成以白人学生为主流的学校。
“如果不是要为孩子创造多元化的生活环境,我不会选择住在这里。”住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长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正考虑把双胞胎送去307学校的学前班。他边喝着咖啡边告诉我:“我想要的是多元文化。你很清楚,如果不想要这些,就会直接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或者搬去其他地方。说起来,我们住在布鲁克林就是希望多元化能够成为孩子成长的一部分。不过我也很容易理解家长的困境,‘又想要多元化,但又不想过于多元化。”他思考过,如果成为307学校里少数的中产家庭孩子意味着什么。“或许这会导致一些孩子的堕落。”他说,“我的孩子不是试验品。”最后,他还是觉得不能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冒险,要把他们送去私立学校。现在,他们是第8学校的学生。
“我们不要融合,学校之间的不公平可以通过给贫困的隔离学校输送更多资源来解决,并且制定更严格的教学质量考核机制。”根深蒂固的隔离意识所导致的无力感,令这种说法对保守和自由的双方都造成了致命的吸引。真正的融合与公平需要的是对现有优势的妥协与让步。可问题一旦涉及孩子,一切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娜雅头两年在公立学校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本人,作为从事隔离学校危害黑人学生研究的心理学家,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隔离学校。“我的孩子只有一次机会。”可是难道这个城市里其他在隔离学校念书的孩子就不是吗?机会对他们而言,也仅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