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的“冈仁波齐”和现实
2016-06-28宋彦
宋彦
“他的这个劲头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在午后的北京望京很容易遇到张杨导演。他一身皮靴、牛仔裤、皮马甲,再配一顶西部牛仔帽,出没在时髦的丽都商区,格外显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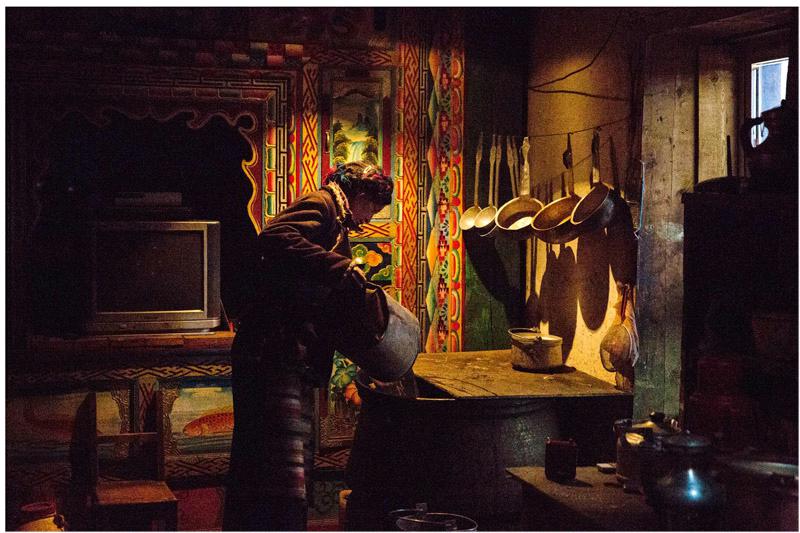
张杨这身康巴汉子造型已经保持了近两年。刚从藏区回来那段时间,朋友们常常认不出他来。有次在大理参加饭局,他去晚了,悄悄入座,好长时间没人招呼,直到有人开始认真打量这位“藏族兄弟”,大家才辨认出了他们熟悉的那个张杨。
“张杨是个藏族人了。”朋友兼大学同学刁亦男导演说。
在以“康巴汉子”造型回到北京之前,张杨失踪了将近一年。2013年底,他带剧组进藏,耗时10个月,拍摄了两部与藏族文化有关的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前者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跟踪拍摄了几个同村的藏族人一路磕长头,到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经历;后者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民间传奇故事。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拍和西藏有关的电影。在他早期的口碑大好的作品《洗澡》中,就有过类似的画面:一位藏族老人带着自己的小孙女,长途跋涉去圣湖洗澡,这几分钟的镜头把世俗生活中的洗澡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是点睛之笔,也有人认为是异域奇观,画蛇添足。“是张杨一定要加这么一段的,为拍这场戏,他差点因为高原反应把命丢了。”《洗澡》的编剧之一刁亦男回忆。
很多年前,刁亦男和张杨一起拍纪录片,去过几次西藏,当时他就觉得,张杨对西藏的感情和其他人不一样,“好像上一世他就是个藏族人”,“拍了《冈仁波齐》电影,总算是把他的心愿给了了”。
《冈仁波齐》看起来是纪录片,实际上是个故事片。导演的控制力在于截取藏族素人演员的生活,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孕妇,一家三口,一个屠夫,一位死在朝圣路上的老人,电影中的这些人物是早就设计好的,只有现场拍摄是纪录式的。”张杨说,他让演员们正常烧火、做饭、喝酥油茶,摄像机一直开着,碰到好的场景就暂停,想几句台词,加在刚才的场景里,“整部电影都是这样拍摄的”。
这种“伪纪录”的形式也曾出现在张杨的另一部电影《昨天》里。当年,张杨把演员贾宏声吸毒戒毒的经历写成了剧本,让贾宏声和父母一起,在镜头前表演他们真实的生活。《冈仁波齐》看似与张杨之前的作品不同,但“伪纪录”和公路片的形式都曾在他过往的作品中使用过,“形式和内核早就有了”。
在藏文化里,马年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张杨追求仪式感,希望在马年把它和《皮绳上的魂》拍出来。摆在他眼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找投资。早年拍电影,张杨没为钱发愁过,但眼前的两个片子,无论从题材还是他希望呈现的影像风格,都没有能赚钱的卖相,想要筹钱不容易。《皮绳上的魂》起码是个完整的故事,《冈仁波齐》连剧本都没有,他只能和投资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大致的拍摄方式和希望呈现的风格,能不能拍成他都不敢打包票。“谁敢投啊!”张杨也觉得,自己这看起来不靠谱的项目有些为难投资人。
眼看着已经到了2013年底,再不进藏,《冈仁波齐》就来不及拍摄了。这时,好友李力站了出来。作为合力辰光的董事长,李力最赚钱的一笔电影投资是《小时代》,从那部电影里看得到他追逐利益的本能。他也曾劝张杨拍商业片,大制作、大IP、大卡司(演员阵容),张杨总是犹豫不决。他投资过张杨的上一部电影《飞跃老人院》。那部电影没能让他赚到钱,眼前的这两部电影更没有赚钱的希望,但他依然对张杨承诺:“不管其他人投不投,你去拍吧,我给你托底。唯一的要求是,注意安全。”
2013年11月底,投资还没到位,张杨就带着一个30多人的剧组进藏了。剧组买了七辆面包车,一路走一路拍,遇到县城就住旅馆,没有旅馆就住帐篷。随队的有厨师和医生,饿了吃大锅饭,病了也有人照看。他们还在当地雇了藏族的摄影助理,刚开拍的那段时间,因为高原反应,摄影师扛不动摄像机,全靠助理们出力才能顺利拍摄。
拍完《冈仁波齐》,张杨把剧组扩张到120人,又花费两个月拍完了《皮绳上的魂》。在藏区的10个月,张杨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只有缺钱时,才打电话催催投资人。
10个月下来,张杨成了现在的张杨,皮肤黝黑,戴上帽子、手串和银戒指,坐在人群中寡言少语,他有意无意地与周遭保持着距离。“刚从原生态的地方回来,大家都不适应或者排斥乱糟糟的城市生活。”刁亦男试着分析张杨,“但他的这个劲头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困惑与焦灼
很多时候,张杨不愿被简单地归入“第六代导演”的行列。事实上,他与多数“第六代”所走的路也不一样。王小帅、娄烨等人的早期作品都在海外反响热烈,但也都遭受过电影被禁,拍摄资金短缺的坎坷命运。张杨的运气要好得多。他的处女作《爱情麻辣烫》与美国制片人罗异合作,电影不仅顺利上映,还创造了当时的票房纪录。
1995年,罗异从台湾来到大陆,在一众年轻导演中选择了张杨,打算与他合作,拍一部属于年轻人的电影。当时,张杨还没有任何电影作品,罗异看上的是他为摇滚圈拍的几个MV。
因为要为投资人负责,张杨的首部电影就呈现出与其他“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气质。他没有“关注边缘人物”,也没有太多“自传色彩”,而是讲诉了五段不同年龄层的都市爱情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当时是没有的,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张杨分析《爱情麻辣烫》的成功,“那时肯定也考虑市场了,而且抓得很准。必须拍一部能上映的电影,这是当时的底线。”
一部低成本电影,收获了3000万元票房,还排进了当年院线电影票房的前三甲。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来说,这是一个太完美的开始。
张杨当时找来的是大学时就一起折腾的刁亦男和蔡尚君,大家一起写剧本,后来刘奋斗也加入了。这几个人在若干年后都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成名了。刘奋斗凭处女作《绿帽子》拿到纽约翠碧卡影展的最佳故事片和最佳新人奖,后来的作品《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也在文艺青年心中有着颇高的地位。刁亦男渐渐把创作重心偏向犯罪题材,上一部作品《白日焰火》让他拿到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蔡尚君和刁亦男一样大器晚成,他在文艺片的路上苦苦挣扎而终有所得,两部作品《红色康拜因》《人山人海》都拿到过国际奖项。
“要不是张杨,我们也许没这个机会,后面各自的电影可能也没了,或者晚得多,谁知道呢。”蔡尚君说,“我们这些人,张杨能最先出来,是有原因的。他情商很高。你看,他就能把我们这群人都聚在一起。”蔡尚君说他刚做导演时,他在与人沟通上吃了很多亏,而张杨没有这方面的局限,他善于交流,在与人打交道上游刃有余。
那时北京唯一一家咖啡馆在三环路上,美国人开的,叫“真的咖啡”。他们这伙人每天都耗在咖啡馆里,每个人想一个故事,拿出来讨论,不行就过滤掉,再想新的故事。“是四个故事彼此独立还是全部打散穿插讲述,张杨和制片人罗异争论过,一度还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张杨妥协了。”刁亦男回忆。
《爱情麻辣烫》成功后,张杨又很快开始筹备《洗澡》的剧本。最后的定稿阶段,几个老同学又聚在了一起,他们把自己关在亚运村的一个宾馆里,一场戏一场戏地过,墙上贴满了故事卡片。
电影刚做出来时,张杨有那么一点担心。接受采访时,他袒露过当年的顾虑:“我们不是要拍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吗?这个会不会太老了?观众会不会睡着?”市场反馈很快打消了张杨的顾虑,《洗澡》不仅票房大卖,还帮他拿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银贝壳奖”。
蔡尚君说他因此一度为张杨的未来担忧:“头两部电影《爱情麻辣烫》和《洗澡》在口碑和票房上都很成功,这个成功对年轻导演来说是非常好的事,但后面怎么走,有点难。”
《洗澡》之后,张杨的电影更像“第六代”的作品了。《昨天》《向日葵》都探究个人的精神世界,或多或少有了自传性质。也是从这时起,张杨开始变得小众。电影票房不尽如人意,曾经一起写剧本的好哥们儿各自单飞,他也不再和制片人罗异合作,接下来的电影该怎么做,张杨要重新选择。
2008年前后是张杨最困惑的时期,他很难静下心去拍两部与商业不沾边的电影。那几年,国内电影票房暴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矛盾撕扯着他。总有人把过亿的投资和剧本摆在他面前,要和他一起谋划“票房奇迹”。在这样的状态下,张杨先后拍摄了《无人驾驶》和《飞越老人院》。这两部电影,一部失了口碑,一部输了票房,他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摇摆,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那两部电影经历过很多复杂的过程,拍完之后,我自己都不太满意。”张杨承认,两部电影自己拍得都不纯粹,“考虑了太多市场和观众,商业的东西太多了”。“拍摄过程中换过几次演员,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有些东西不受自己控制。”他说。
刁亦男和蔡尚君都不知道张杨为什么会拍《无人驾驶》,觉得那部电影很不张杨。从《无人驾驶》的演员配制来看,张杨在这部电影上降低了艺术追求,寄托了商业野心,但结果依然未达到预期。在创作上,《飞越老人院》要好于《无人驾驶》,故事的整体构架符合张杨的想法:“但原本是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因为一些原因,改成了一个有点温暖的结局,这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飞跃老人院》的口碑远远好于《无人驾驶》,但电影1300万元的投资和600多万元的宣发只换来了350万元的票房。张杨总说自己不在乎票房,但面对眼前的落差,他还是有些猝不及防。
采访中,张杨、刁亦男和蔡尚君都提到,他们怀念几个人一起搞创作的日子。一起写剧本,一起打牌、泡咖啡馆、游泳,大家都不掖着藏着,有多大劲都使出来,互相成就。而如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有时在酒吧和饭局上碰到,还是像以前一样一起喝酒,一起打牌,但聊创作的机会并不多。
“怎么聊呢?技术上的互相帮助没有问题,但你要是想给对方的电影安个魂儿,这事儿就没法聊了。”蔡尚君说,走到这一步,大家都有了各自的方向,精神上的焦灼都只能独自面对。
摇滚,现实和城市
回头看自己的前几部电影,张杨觉得,《爱情麻辣烫》和《洗澡》都有市场的考量,而《昨天》的气质和表达的内涵更符合他当时的心境。
电影中的贾宏声是张杨的好朋友,他们都热爱摇滚。《昨天》讲的就是贾宏声自己的故事,他和同为演员的父母一起,在镜头前演绎了自己吸毒、戒毒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痛苦不堪的内心世界。
“我特别理解贾宏声,他的困惑,他和世界的那种隔阂,那种孤独感,我也有,只是他太极端了。”张杨说,他在这个偏执的同伴身上,看到了他们这群人的痛苦。
贾宏声是张杨最喜欢的演员。“他身上有那股劲儿,我们这些导演都喜欢都市题材,贾宏声长得洋气,有范儿,他身上有我们喜欢的城市感和时代感。”如果一定要把自己归入“第六代”导演,张杨觉得,自己与其他人的共通点就是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小说、戏剧、当代艺术到音乐,他们极度渴望摆脱上一代人的乡土气。
“我们喜欢法国‘新浪潮的戈达尔、特吕弗,喜欢德国的法斯宾德,喜欢拍纽约的马丁·斯科塞斯,归根结底是喜欢两样东西:现实和城市。”
“我骨子里其实挺摇滚的。”一身藏族行头的张杨突然定义自己,“摇滚的本质就是自由,别管我做什么、穿什么,只要是以个人意志做出的选择,就都符合摇滚精神。”
在眼前这个“康巴汉子”款张杨身上,很难找到热爱摇滚乐的证据。但他的大学同学、DJ张有待说,当年张杨从中山大学转学到中戏,发型突兀,一身行头也与众不同,人如其名,非常张扬。
因为代表中山大学在人艺演出了话剧《行星启示》,张杨被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看中,转学到了中戏导演系。上世纪80年代末,摇滚乐开始在中国传播。有一天,张杨被同学施润玖带到学长张有待的寝室,张有待给他们放了几首摇滚乐,张杨瞬间就爱上了,欲罢不能。“那感觉就像掌握了人间真理,一下子觉得电影啊、戏剧啊,都不重要了。”爱上摇滚的张杨越发愤世嫉俗,觉得身边都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而他不一样,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要反抗、要自由,要探索生命的意义。
很快,张杨就和施润玖、张有待,还有一个舞台美术系的哥们儿组起了乐队,取名Hospital(医院)。鼓是乐器里最贵的,大家把它留给了张杨来解决。家里人宠他,他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最后,他果然要到钱,买了个二手鼓。”张有待回忆。
“那会儿特疯狂,真跟传教似的。”张杨说,当时,他们有一个音箱,下午四五点钟一下课,大家就打开窗户,把音箱放在窗台上,用最大的音量放摇滚乐。“后来还真有人入坑,周边的中学生也来我们这倒磁带,中戏成了摇滚乐的一个小据点。”
与此同时,刁亦男、蔡尚君、张一白和孟京辉等人成立了文学社。一开始,乐队和文学社势不两立,互相看不上。后来,因为一些外力,两伙人走到了一起,开始疯狂地搞实验戏剧。那时的戏剧和摇滚乐一样,是他们对抗世界的另一种方式。“《等待戈多》不让演,我们就站在煤堆上念剧本,必须表达。”张杨把年轻时的荷尔蒙献给了摇滚乐和戏剧,当然还有不愿被提起的那些爱情。
与今天对藏族文化的迷恋一样,张杨当年对摇滚的热爱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精神上的支撑,他需要以这种支撑凝聚能量,再以音乐、戏剧或电影的形式表达自我。
“张杨是我们这群人里成熟比较晚的,很多时候都像个小孩。”刁亦男觉得,张杨的底色其实不是摇滚,也不是藏文化,而是温暖。“他的电影总是讲一些市井生活,父子情、兄弟情和温暖的爱情。他总是用温柔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忧伤。别管他是文艺青年还是摇滚青年,温暖才是他的基调,电影和人都是这样。”
在和朋友的相处中,张杨也的确温和。各种被友情邀请的电影首映和发布会他都尽量参加,低调地出现在现场,不争也不抢。碰到电影好看,他会对着朋友和媒体夸两句。但多数时候,电影都很烂,他要给足朋友面子,又不愿说假话,不得已总会在电影演到三分之二时偷偷离场。
继《冈仁波齐》参加了北京电影节的展映之后,《皮绳上的魂》也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影节上首映,放映结束后,张杨在朋友圈实时分享了大家对电影的褒奖。他准备为电影出书,我们采访结束后他约了人来挑选新书配图。他还和发行公司商量了全新的电影宣发策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上映,把电影的档期尽可能拉长,靠口碑拉动票房。”
与拍《无人驾驶》《飞越老人院》时期相比,现在的张杨平静多了,但矛盾依然存在。“电影拍完,后面的事就和导演无关了。”张杨顿了顿说,“当然,哪个导演不希望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