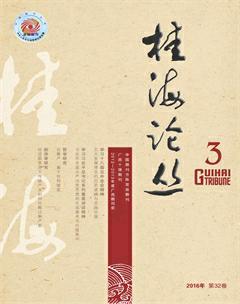“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
——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赓续
2016-06-24傅义强王苑青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
□傅义强,王苑青(南方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0515)
“中国奇迹”的政治逻辑
——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赓续
□傅义强,王苑青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最终导致解体的对比明显。这其中的深刻政治逻辑就在于,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放权,并始终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延安道路”,为改革开放后30年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邓小平的改革,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奇迹”;政治逻辑;毛泽东;邓小平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启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问题是像原苏联这些国家也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可是为什么他们改革不成功最后导致解体,而中国却取得成功?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政治逻辑?这就要从改革开放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与发展角度来考察和分析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期的关系。
一、“中国奇迹”产生的逻辑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经济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改革开放32年后的2010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9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高出7%。201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979年的24.25倍和17.16倍,城镇化率达到52.6%[1]。西方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之为“中国奇迹”。
原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在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改革高潮,但都不够彻底。到了7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进入80年代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据1987年1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所显示,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71-1975年的3%降低到1976-1980年的2.3%和1981-1985年的2%,东欧国家在这三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9%、1.9%和0.5%[2]。面对这种情况,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80年代又重新掀起了经济改革的浪潮。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改革最终失败并导致苏东剧变,而中国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让西方舆论界大为震惊,也对“中国奇迹”充满了疑问。尤其是原苏联,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上都明显优于中国,农业人口比中国少得多,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却比中国高得多,中国又面临着一些土地紧张、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到底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中国经济改革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逻辑?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计划覆盖一切经济领域,排斥市场调节和竞争。国民经济的运行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驱动,企业吃“大锅饭”,政企不分,缺乏生机和活力。这种特定时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把国家经济管的过死过严,阻碍了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这也是原苏联和东欧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原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已经比较成熟,有严密的行政系统保障经济的控制和管理,计划经济体制相当完备。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够完备,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中央计划要想通过行政系统控制地方有一定难度。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是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的破坏分不开的。对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其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指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的分权化使得中国没有建立起来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3]。甘阳也认为,邓小平改革成功的秘密恰恰是因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决定性地破坏了新中国成立后想要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使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4]6-8。可见,毛泽东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解构为邓小平的成功改革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没有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邓小平的地方分权化道路难以实现。
二、改革开放前30年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中央和地方关系历来是国家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毛泽东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发动了两个大规模的放权运动,并始终坚持革命时期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延安道路”,动员了地方力量,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为新时期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一)毛泽东的两次大规模放权
毛泽东在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上,虽然采取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但却是其对中央和地方关系整体思考的逻辑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一度效仿苏联的发展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对各地实行完全的管理。这种模式存在着很多弊端,过度的集权导致中央对地方管的过严、统的过死,严重削弱了地方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我们党和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转而关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一直都强调放权地方。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并于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强调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发挥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思想,“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5]。
此后,毛泽东接连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放权运动,一次在“大跃进”时期,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也是毛泽东“虚君共和”思想的具体体现。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4]7-9。放权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并导致了财政赤字危机。1958年到1961年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超过了180亿元[6]72,为此1961年,下放的各种权力被重新收回。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向地方放权的努力,1964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毛泽东又开始对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形式进行批判,再次提出要“虚君共和”。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中央只管大政方针,让地方政府多做一些。他指出,中央政府和中央机关将许多企业过度的集权化,这些企业必须要“重新下放”,中央机关也必须进行放权。于是,毛泽东在1970年开始了第二次放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超过2600家中央管控的企业,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开滦煤矿都下放到了省级或市级,中央机关直接掌控的国有企业数量从1965年的10533家骤减到142家[6]2。用熊彼特的话来讲,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两次放权就是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用高度的地方分权取代苏联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用放权的方式已经基本摧毁了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与原苏联产生了经济结构上的明显差异,为以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毛泽东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延安道路”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与苏联体制显示出巨大差异性的原因,美国学者弗朗茨·舒曼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进行了分析。舒曼认为,新中国在开始现代化建设时,面临着走苏联工业化道路和走中共“延安道路”的基本选择,“苏联道路”不同于放手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延安道路,”而是强调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落实中央计划[4]10。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循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到50年代中期,许多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在广大农民和工人为主要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中国,过分依赖少数技术专业和中央计划部门,会导致广大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逐渐被边缘化,逐渐置身于工业化建设之外,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不出它应有的潜力。面对这一现实情况,1955年底,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苏联模式存在着某些弊端,苏联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为此,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国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应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来发展重工业。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重视农业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5]241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关注农民,就是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以群众为基础的“延安道路”。同时,舒曼还认为,从大跃进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已经逐渐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延安道路”[4]12。毛泽东对我国国情的准确判断,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专家路线”,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改革也奠定了政治基础。戈尔巴乔夫的原苏联改革最终失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支持。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两次放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1978年以后改革派领导人的政策选择。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改变政府对企业“管得过细、统得过死”的情况,邓小平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采取放权让利的方式,在企业领导体制上采取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放与让之间,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激发了国企的盈利意识和发展意识,为国企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大的放权运动。这次放权运动鉴于城市的既得利益比较稳固,选择了从农村改革开始。1979年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被打开了,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合同书,推动了家庭联厂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可见,改革开放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城市公有制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厂长责任制”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分权化”轨道上进行的。另外,得益于改革前的农业分散经营和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留下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农业的分散经营还为一个新的大型集体即农村工业或乡镇企业提供了基础,乡镇企业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8]。社队企业,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能起来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队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培养了一些生产经营的人才,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客观上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达到264.8万,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2.1%[9]。邓小平实行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放权是在南方讲话以后。中国在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中国的改革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汇聚了地方改革的力量,在南方讲话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放权,推动了地方政府改革的成功。
此外,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放手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路线,也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改革的很多措施都是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邓小平曾说过:“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0]包括经济特区的创办也是来源于群众的设想。邓小平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1]239可见,邓小平设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与广东的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之后,我国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取得了显著成效。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改革就没有办法起步,更不用说取得成效了。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十分注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1]213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积极下放权力,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衡量改革工作好坏的标准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取得成功,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时代提出不要走苏联的弯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强调放权地方,甚至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组织结构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改革开放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城市公有制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厂长责任制”等都是在这种“分权化”轨道上进行的。同时,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放手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路线也不同于苏联道路的“专家路线”,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改革也奠定了政治基础。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就是西方所称的“中国奇迹”产生的政治逻辑。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16.
[2]王有录.世界通史:下册[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399.
[3]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12.
[4]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J].读书,2007(6).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5.
[8]刘元贺,孟威.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内在政治逻辑—从谢淑丽的解读谈起[J].社会科学论坛,2012(8):212.
[9]李受恩.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J].实事求是,2002(5):1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50.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何成学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3-0088-04
收稿日期:2016-0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逻辑研究》(14JD710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傅义强,男,历史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苑青,女,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