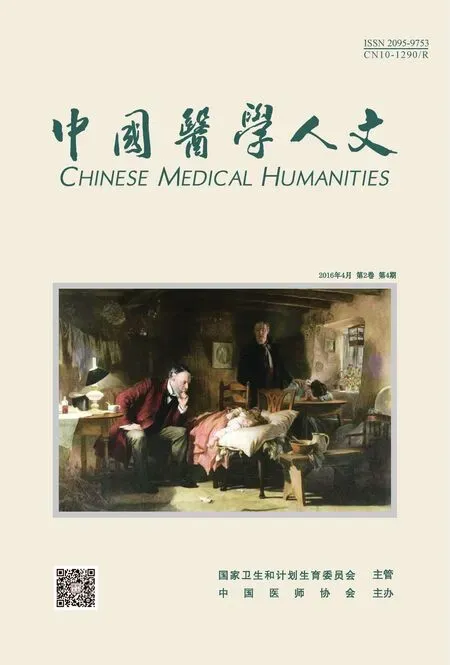用沟通与信任架起医患理解桥梁
2016-06-07周佳梁
文/周佳梁 周 令
用沟通与信任架起医患理解桥梁
文/周佳梁 周令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6年3月初,一个事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说是不大不小,大概因为此类事件大多形式多变而内核一致,似乎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又实在脉络清晰、矛盾鲜明,不能不引起深思。事件大致过程为:人民日报微博于2016年3月3日发布一篇名为“医生将冰冷血袋抱怀里:求求你快点升温”的博文,讲述河南某医院医生用身体加热从冰箱里取出的血袋以求尽快救治伤员的事件。该微博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方认为医者仁心,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作为医生的辛苦,而另一方则提出质疑:为何不用微波炉或水浴加温?人民日报此举是否矫情?随后,一名职业为医生的微博博主“白衣山猫”于当日发表一篇长微博“为什么要用我的身体温暖你的冷血?”回应此事,详细解释了为何要用医生身体加温的质疑。微博最后,他写道:今天我说出这一切,不求点赞,不求欣赏,唯求一份理解。

笔者大致浏览了微博下的评论,不出意料的出现了两种声音,支持和质疑,但双方都没有兴致把节奏放慢仔细探讨问题,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大概是中国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大原因:不了解,不理解,不辩解。所谓不了解,患者及患者家属不了解相关医学专业知识及医疗流程;所谓不理解,医患双方在维持这样一段特定关系时很难做到换位思考,因治疗过程可能涉及大量隐私,很可能造成沟通不善;所谓不辩解,医生在受到误解时往往在最初的申辩无效后选择沉默,引发更多的误解。

漫画绘制/曹永祥
作为一个口腔医学五年制的大二在校学生,笔者对医患矛盾的解读也许尚浅,但这个过渡性的身份使自己有一定的发言权。首先,医学生具备一定的医学相关知识,比大多数其他职业者接触更多的医学观点;其次,医学生兼具所有人共同潜在或目前具备的属性——患者或患者家属;最后,医学生既没有成为职业医生,又因其阅历尚浅很少直面医患关系中作为患者一方的问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医学生尚处在一个不清不楚却还未深陷其中的定位,可代表一部分中间属性人群的声音。
成为医学生之前,笔者曾信誓旦旦立下flag绝不学医,为什么呢?医患关系太过紧张,医学专业学习周期过长,成为医生后所闻所见所感负能量过多。然而阴差阳错,或许有缘,笔者被填报的一众志愿中唯一的医学专业录取,成为医学生。就读一年多,接触的专业知识不多,但发现了很多曾经观点的偏颇。
在上医学课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老师为自己的职业骄傲,并且为学生灌输这样一个观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作为医生不求回报,救治患者是一件光荣且幸福的事情。但同时,所有老师在上课时会反复强调专业技能以外的能力如人际沟通能力、察言观色能力等等,他们会用真实事例告诉学生一个星期一早上由两个成年儿子搀扶来拔牙的老年患者很可能存在碰瓷的风险,病例记录上一个数字的差错很可能让你成为别有用心者手下待宰的羔羊,这时候老师们的形象就很像小时候讲“你再哭就有狼外婆把你吃掉”的故事的父母们,听得我们面面相觑感慨医生不好做,前一秒好好的救死扶伤下一秒就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说好的医患一家亲呢。这恰恰说明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医患关系有其特殊性,双方非常不对等。虽然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却是一方在另一方的隐私范围内实施方案,且医生只能将治疗计划的浅显部分为患者解读,而医学并非典型的科学,因患者个体差异性及医疗水平发展有限需要更多的人文内容,所以在表面的专业外壳下实在是两方人在用肉身对抗被未知因素包裹的病魔。
医患问题自古有之,中国古代职业分士、农、工、商,而没有提到医,这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了,但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就有看病难的问题,高官显贵王侯将相生病了,满天下地搜罗名医,小伤小病的在家也是有大夫在侧的。而普通老百姓就没那么容易看病了,不说普通医馆里大夫的医技,单说看病抓药的价钱就已成问题,所以走投无路的人们宁愿烧香拜佛,这样看来,医生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这也是相对的,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治愈率低下,一个不小心大夫就会被权贵杀掉,现在的古装片里不乏这样的情景:高官威吓医生,“你若医不好她(他),小心你的脑袋了!”神医如华佗,也仅仅因为曹操的疑心病被冤杀,可见医生的地位也不是那么高。到了近现代,庸医误人的事情被陆续披露,民众有了一定的自主见解,开始对医生群体产生不信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医患关系更加僵化。
而一些额外因素使这一矛盾尖锐起来。第一,无论患者有多高的受教育程度,在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时就做不到那么淡定了。过少的医学知识使他们对治疗预后期望值很大,俗语说“死马当活马医”正说明了患方在特定情况下无法客观,于是在期望值和结果不能对等时会怪罪于医生。第二,很多医患矛盾起因是沟通不善,有些甚至并非在专业词汇上的误解,一名当护士长的老师曾举例:手术前叮嘱四川老汉的不要吃饭被理解为可以吃馒头,说起来好笑,身临其境或是另一番感慨。第三,往往是医疗纠纷的个案闹得过大使真实事件失真,可以坐下来好好沟通的事情一旦发展为医闹、游行示威就近乎鱼死网破势不两立了,而客观地说,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十分重要,起到舆论导向的决定性因素,许多案例中都有媒体的影子,一旦未查事实或报道中不够客观,都会引起严重后果。第四,如上所说,医患关系的性质特殊,风险巨大,即使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不良预后有所预测也无法做到精确,一旦失误损失的是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医患交往如履薄冰。于是如何改善这一问题成了当前医患关系中的首要问题。
所有人都有成为患者的可能性,所以需要在问题出现前做出行动。首先,笔者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医学常识十分薄弱,非医学专业人士大多对心肺复苏的认识停留在影视节目中的人工呼吸,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简单止血包扎的位点及步骤?因此,简单的急救常识等是需要我们在平时多加了解的。其次,做到换位思考。这一点就是老生常谈了,但试想医生何尝不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生死人肉白骨只是传说,医生并非万能,给予更多理解,更多沟通,更多信任而非依赖会对矛盾缓和不少。最后,不发表轻率言论,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交流迅速,一个人的声音会被无数人听到,所以在不了解事实的时候切勿轻易对医疗事件作出评价。
作为医学生及医生,需要更多的努力。第一,科普宣传。医学知识不能囿于医学界这个小群体中,医生有责任为大众科普简单医学知识以防紧急情况。第二,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熟练的专业技能,这是医生保护自我及救治患者的根本。第三,增加沟通。医生为病人解惑时最基本原则是用通俗语言让患者理解专业知识,懂得沟通技巧,如询问“我是否讲清楚”而非“您是否听懂”会减少误会。第四,具备一定法律知识。在遇到不可调和的纠纷时,医生始终要保持冷静,双方的不冷静会导致矛盾激化,医生最好的武器是法律而非暴力,掌握基本法律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技能。
从医疗体系角度来说,我国正处在医疗改革的阶段,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在被讨论并解决。例如,病患的很多个人信息是不被医生所了解的,而其又对医生制定治疗方案起到指导作用;中国对死亡的现行性定义是呼吸心跳的永久性停止,而随着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出现,脑死亡的定义被更多人了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家属及医生对死亡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医学生目前学习的医学伦理学课程中涉及的逻辑问题往往纸上谈兵,因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在中国并未完善……但相信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有所改善,如多年不招的儿科医学今年开始招生,打击医院挂号票贩子,这都是国家重视民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