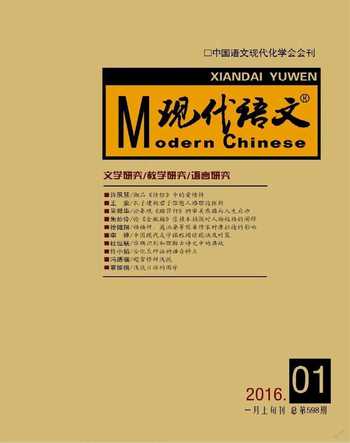灵魂的追寻与守望
2016-05-30夏雨潋
摘 要:张炜的《九月寓言》是一部内向性的、极富精神内涵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该作品中流浪、奔跑、小村、野地等一系列意象的分析,从三个女孩子的人物命运切入,对大地的叛逃与守望的精神内涵做了进一步思考,从奔跑的意象、对土地的坚守两个方面来解读张炜所坚持的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在当代文坛上特有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张炜 《九月寓言》 奔跑意象 土地精神
张炜的《九月寓言》在当代文坛中是厚重的,也是别致的。它创设出一个无时间化的背景,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一个生气勃勃、纯朴美好且藏污纳垢的小村。这一片名叫“小村”的野地充斥着苦难却又时刻喷薄着生命的热力。作者通过诗性的言说,运用大量隐喻和象征,以陌生化的形态歌颂山野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细读这部作品的过程,是一次感受土地的神性和诗意的过程,是一次细细内省个体自身精神家园的过程,也是一次灵魂返璞归真的精神追寻的过程。
一、对“奔跑”意义的两种理解
王安忆提出,《九月寓言》实际上是一个跑和停的故事,它是一个奔跑的世界,奔跑就有了生命,停下则是死亡。
故事的最开始,是在一个饥荒穷苦的年代,一群流浪者发现了一块盛产地瓜的富饶土地,便停驻在这块名叫“小村”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流浪者们善于奔跑、生命力极其旺盛,带着群体劣根性,被邻村的人蔑称为“?鲅”。?鲅是一种剧毒的海鱼,在这种蔑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小村人被这个主流世界所抛弃的悲凉境地。他们从遥远的南山迁徙而来,一路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唯有奔跑。奔跑带给他们的是对恐惧和苦难的逃离,对觅食与繁衍的渴望。书中有一段描写龙眼先人赶路的片段,交代了这个小村最初群体聚居的原因:“老爷爷挑着担子奔走在雪地上……雪地上的脚印一会儿变成了一溜儿不断线的银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跟上来,抢着,追着……那群人直追了两天两夜,捂住破衣烂衫,低头一看,银币全都化成了水。他们懊恼得呼天抢地,可这会儿已经回不去了,只有跟上这溜脚印儿,向北向北。”[1]这一群“?鲅”是一群来自各地的流浪者,他们中有因对生之眷恋而奔跑的,有因贪欲而奔跑的,也有因从众心理而奔跑。在这次漫长的奔跑中,人性的光辉与丑陋同行;也正是这次奔跑,小村的先人们找到了这块可以喂养他们的土地。细究这群“?鲅”奔跑的原因,书中有一段描写金祥死前抽搐的片段给了我们答案:“像有什么致命的东西催逼着他,这东西跟了他一辈子啦。……在路的尽头处,他终于把它生生逮住,它的名字叫‘饥饿。”[2]饥饿让死亡变得真切,正是因为人们对饥饿的畏惧才一路狂奔,企图寻找吃物和能养活他们的土地。这也是作者张炜想向我们传达的思想——人类对农作物的天然崇拜、自然界优胜劣汰法则的焦灼感,促使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书中主要讲述了两代人停留在小村时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小村人一直处于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状态,以地瓜为生,性情乖张、民风彪悍。书中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劳作与生活的:“他们不怕寒冷,大笑大叫着干活,有时还跳起来。劳动空隙中他们就在泥土上追逐,翻斤斗,故意粗野地骂人。如果吵翻了,就扎扎实实打一架,尽情地撕扯。”[3]到了晚上,饱腹又无事可做的小村人是焦躁的:于是男人打老婆,把女人的心火打掉;女人则给丈夫拔火罐,把男人的心火拔出来。书中反复解释了小村人的一系列粗暴行为的原因——“瓜干烧胃”。细究其背后的深意,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赐予人类粮食,人要想饱腹生存就必须坚守土地,而这种停滞的生存状态让流浪者内在的生命力无处宣泄,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无处释放。在丰收的九月,小村人把地瓜切片、曝晒、妥善保存,作为村里人一年的吃物。如果瓜干在变干前挨了场雨,口味会变得苦涩,人食用之后会吐酸水。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鲅”一旦停下来,就失去了追求更好生存环境的斗志,他们满足于生存的底线,只要饱腹就畅快知足,愚昧落后的农耕文明让他们过着半兽半人的“边缘人”式的生活,但他们却乐在其中。他们也羡慕周围工区的城市化的生活,吃着黑面饼穿长筒胶靴,他们中的部分年轻人也试图冲破这个落后的小村,但他们改变不了生死于野地、流浪于野地的宿命。人类社会的车轮不断向前,停驻下来的终将会被抛弃,这个小村最后也没有逃出被毁灭的命运。从小说的结构看“奔跑”的内涵,曹文轩作了很好的阐释:“《九月寓言》以‘奔跑——停留——再奔跑为架构,隐喻着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循环:漂泊——栖居——再漂泊。[4]”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理解“奔跑”这一意象,我们可以把奔跑这种行为看作是小村人对自身灼热生命力的肢体表达。他们对“生”存在感恩之情,对“粮食”保有敬畏之心,对“劳动”充满着持久的热情,这些都归根于他们在野地奔跑,灵魂融入到野地里,大地赋予了他们纯朴、自由、奔放的个性,让人性回归到最初至纯至美的状态。其中最让我为之震撼的是露筋与闪婆的爱情故事,笔墨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露筋是小村的一个天才流浪汉,当他第一次遇见盲女闪婆时,便开始了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幸福的奔跑。在闪婆父亲的枪口下,露筋冒死抢走了她,背着她一路狂奔。在奔跑中,他们相爱了。他们的结合没有得到家人的祝福,从此流浪于野地。但匮乏的物质条件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绝望,他们觅食、饮酒、奔跑,日夜恩爱,过上了逍遥自在的生活。书中用了诗性的语言描述了露筋临死前对这段流浪生活的回忆:“有谁将一辈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给无边无际的田野?那时早晨在铺着白沙的沟壑中醒来,说不定夜晚在黑苍苍的柳树林子过。日月星辰见过他们幸福交欢,树木生灵目睹他们亲亲热热。泥土的腥气给了两个肉体勃勃生机,他们在山坡上搂抱滚动,一直滚到河岸,又落进堤下茅草里。雷声隆隆,他们并不躲闪,在瓢泼大雨中奔跑西颠,哈哈大笑。”[5]这两个人物因“奔跑”而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我们体验到了他们在奔跑中极致的生命喜悦,感受着他们舒展自由的人性表达。在这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的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精神世界却趋于贫瘠,社会的高强度竞争压力致使人性异化、人类道德水平下滑,而在整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回归人性真善美的渴望,对自然、放松、富有尊严的生存姿态的希冀。
二、“土地精神”的叛逃与回归
《九月寓言》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在肥、三兰子、赶鹦这三个年轻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故事。她们是“?鲅”中最年轻、聪慧、美丽的姑娘,她们的共同点是都与工区的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先进的城市文明充满向往,但她们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肥是作为公开视角叙述的人物,这个“白胖得像水生植物似的”姑娘看似安静得与世无争,其实内心是反叛的,从她抗拒父母为她定下的婚事这一点可以看出。在父母双亡后,她常常会思考同龄人不曾想过的问题:“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可以在书中感受到她对土地的依恋、对自我身份清晰的认知,她知道自己是“?鲅”的后人不能离开小村,但内心对小村枯燥愚昧、无依无靠的生活是厌倦的,所以她常常夜色中奔跑找寻自己的出路和归属。直到她遇到钟情于她的少年挺芳,这个来自工区瘦弱的男孩,甘愿为她挨打险些丧命,默默跟随守候她,甚至要撇下父母带她私奔。肥坚守小村的信念渐渐动摇,她开始相信这个痴情的男人会给她一个家。小村人善于奔跑,却永远也跑不出这土地,这一点在闪婆一家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走得再远,哪怕是畏罪潜逃,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归自己的故土。但肥不一样,“肥”这个名字与“飞”谐音,预示了这个人物的命运——飞出小村。肥最终抛弃了落后愚昧的小村,逃脱自己的宿命,奔向一种文明现代的生活方式。她是小村的叛离者,也是灵魂的放逐者,她无视祖辈的村规,不惧同村人的谴责,只为和所爱的人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种逃离没有充斥物欲杂念,是一场单纯为爱的私奔,所以土地成全了她。
三兰子是这部作品中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个女孩长相一般,但心气很高,是小说中最向往工区城市化生活的人。当她在委身于语言学家之后吃上了黑面饼、穿上了让人羡慕的大胶鞋,可当她怀孕了才发现这个男人是个有家室的人。她打掉了孩子,用碱水洗净肠胃,受了很多苦。之后,为村里人所不齿的她嫁给了争年,做了大脚肥肩的儿媳妇,又受尽了恶婆婆的毒打虐待,最后吃老鼠药惨死在婆家。作为一个被困于小村想走出去的女孩子,三兰子没有肥和赶鹦那么幸运,她没有能带她远走高飞的男人,也没有足以让外村人垂涎的容貌,只能靠出卖自己的灵肉来试图改变自己“?鲅”的命运。细细想来,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三兰子”,她们心气高、不甘贫穷,一心想离开宽厚质朴土地,走出去才发现,城市的狡黠让他们措手不及。作者借着这一人物的悲剧性,作者描写了试图抛弃土地、冲破命运的桎梏不得善终的这样一类人的苦难,并表达出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悲悯,这也是作品的诗性力量和人文关怀之所在。
这部作品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赶鹦这个角色,她是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空间。首先,她是美的,她的外表美得惊为天人。文中是这样描述她的:“赶鹦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尥动不停的圆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臀”“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灼人;唇沟深深,上唇微翘,像是随时都要接受亲吻”“一匹热汗腾腾的棕红色小马,皮毛像油亮的缎子,光溜溜的长脖小血管咚咚跳。”我们能够想象到一个五官俊美、身材姣好的女孩,浑身放射着灼热的生命之力,在原野上奔跑欢笑的样子。她是整部作品的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她带领着“?鲅”中的年轻人在夜晚的野地上奔跑,从而使得整个小村长久地保有生命的活力。年轻人在她的带领下,尽情享受夜晚野地的静谧、快乐和自在,在奔跑中尽情释放自己燥热,驱逐对饥饿和死亡的恐惧。诚然,她对土地是热爱的,她的美都是生她养她的原野给的,她在野地的夜晚洒下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她曾与风流的有妇之夫工程师相恋,父母的百般阻挠没有让她死心,可当她看到小村地下因被工程师采煤而挖空的那一刻,她彻底放下了这段畸恋。我们可以理解为,赶鹦是大地最忠实的守夜者,她无法接受外来的先进文明对土地的侵蚀与践踏。她曾向往过工区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但她最终选择留在野地,终其一生守护自己的家园。小说的结尾把整部作品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小村因过度开采而地陷,被工业文明所摧毁,除了出逃的肥,全村的人都丧失了生命。书中的最后一段采用寓言式的叙述:“一匹健壮的宝驹甩动鬃毛,声声嘶鸣,尥起长腿在火海里奔驰。它的毛色与大火的颜色一样,与早晨的太阳一样。”赶鹦最终化作一只宝驹浴火重生,她把一生的热力都献给了土地,并殉葬于土地之上。这种涅槃重生,这也表达了作者对回归“土地精神”的美好愿望与信心。
三、融入野地的灵魂修行
张炜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6]也许这个真实就是人对土地的一种归属感。当城市人长久地生活在逼仄局促的生活空间,城市中无形的压力和繁杂的信息化阻隔了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原初感受,找不到人性中最初的简单快乐,孤独破碎的灵魂无处安放,唯有在对土地的一次次薄奠之中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相比之下,作者极力歌颂处于粗糙自然形态下的质朴原始的人性,认为尽管它无不愚昧,但这种愚昧比之嘈嘈营营的城市文明也可以容忍的。在这部作品里虽然看似诉说小村贫瘠生活状态,实则是在写他们在野地上舒展的人性之美和天然的快乐。在这块纯朴的土地上,滋养了龙眼母子的亲情、刘干挣与方起的友情、露筋与闪婆的爱情……在大地混沌、苍茫的底色中,那里的人在劳作中、进食中、欢爱中体验着最朴素、独特的欢乐,这种人性之光这正是作者所要歌颂与感召的。
在历史的力、社会的力、文化的力的作用下合成了人性内容。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生活的压力与竞争感让人心焦躁,精神世界贫瘠,缺乏信仰的。张炜在《融入野地(代后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愿冥冥中的手为我开启智门。比起我的目标,我追赶的修行,我显得多么卑微。苍白无力,琐屑慵懒,经不住内省。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那样,漫长的消磨和无声的侵蚀我也能够陪伴。”[7]这个光点,是所有20世纪末把精神关怀当作终极关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守望。当城市放逐了野地,野地已然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故乡。在这方精神驻地上,人与野地共存共生,哪怕物质生活贫瘠乏味,但精神世界是丰饶美好的。人融入野地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和修行,意味着人可以寻回真实洁净灵魂,接近世界的本源,这充满诗性魅力的呐喊是对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召唤,也是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涵所在。
注释:
[1][2][3][5]张炜:《九月寓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第79页,第7页,第71页。
[4]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6][7]张炜:《融入野地(代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第308页。
参考文献:
[1]张炜.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J].当代作家评论,1993,(1):66-74.
[2]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夏雨潋 浙江杭州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00)
猜你喜欢
——品评《张炜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