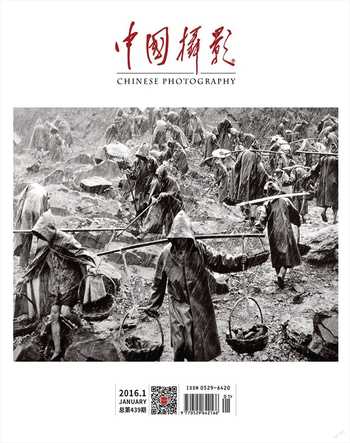消失在2015年
2016-05-30任悦
任悦
五年前,一个人死了,动静没有现在这样大。
要是再往前,关于一个去世的名人,消息更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一点点传来。2004年,布勒松在这一年离去,我忘记从哪里看到这个消息,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后来却发现是八月。要是在今天,这样一位大师离世,它作为一条爆炸性消息热度能持续多久呢?但恐怕人们终究会在另一场刷屏运动中将之刷走。社交网站上的关怀,始终是非人性的。
我想从一个不太起眼的逝者开始我的讲述。之前查阅一篇尤金史密斯的文章,我翻到他的博客—哈罗德·范因斯坦(Harold Feinstein),这位先生曾帮尤金的“匹兹堡计划”做专题页面编排,他当时26岁,还给相当落魄的尤金·史密斯提供了一间住处,这个位于一幢爵士乐手排练大楼的房间,促成了尤金《爵士屋》项目的出现。哈罗德曾谈到自己的父亲,“他慷慨地给我买了第一台相机,但同时却也是一个酒鬼,暴戾且总是充满怨念。”这位父亲的脾气,竟然和尤金史密斯一个模样。
2015年5月26日,哈罗德博文的开头是“伤心透了”,摄影师玛丽·艾伦·马克(Mary Ellen Mark)在前一天去世,终年75岁。1960年,哈罗德·范因斯坦在费城安尼伯格传播学院教书,玛丽·艾伦曾是他学生,博客里所配的两张肖像就是当年拍下的,哈罗德说,这两张照片一静一动,正是她的两面,20岁的她充满活力,那迹象就已经预示着她将在摄影领域有一番作为。
2015年6月20日,哈罗德也去世了,84岁。留言悼念的人并不多,有一位医生说:“在我们的接待室里挂着你的艺术作品,非常美,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摄影师离开了,他们偷来的时间却得以幸存。
中平卓马在1973年烧毁了自己几乎所有的照片和底片,也让这位在日本摄影史上理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摄影师一度销声匿迹。不过,他却有选择地留下了拍自1971年巴黎双年展的1500张黑白照片。
有人还记得那一天,1971年9月28日,中平卓马迟到好几天才到场,脸上充满失望,对当代艺术的失望。在他看来,这些貌似要和社会体系对抗的作品,却只是一种无用的怨言,创作者对改革毫无兴致,其用意不过是实现它们作为一种“艺术商品”的价值。中平卓马的展览开始了,他白天拍照,晚上冲洗,第二天清晨照片还未干就粘到墙上,之后是地上。墙上的巴黎日记—时间、地点、人物—是这位摄影师在巴黎的即刻存在,是其和物质世界接触过程的转印。照片的生产全然不在计划之中,也没有任何要挂在墙上永生的愿望,毫无选择,没有任何主题。
真实就是中平卓马对这个虚伪世界的最大的挑衅。
“个体成了商品”,中平卓马几十年前的反抗,今日仍在艺术界盛行。作为著名的《挑衅》杂志的创始人,这里推出了森山大道,而“粗颗粒、虚化、虚焦”这些来自1960年代晚期的“日本风格”至今仍在流行。但怎样才是挑衅而不是卖弄?
中平卓马曾撰文介绍尤金·阿杰,他说尤金的巴黎给他一种“不可重现”的感觉,把你带入画面,但同时又将你拒绝,这大概就是这位艺术家同时被称为纪实摄影师以及超现实艺术家的原因。而另一个容两种极端为一身的艺术家是贝歇夫妇,他们的作品发端于纪实,最终却成为观念。确凿的事实成了巨大的能量场,得以容纳完全相反的事物两极。
希拉·贝歇(Hilla Becher)教会丈夫使用大画幅相机,在这之前,伯恩·贝歇(Bernd Becher)正在试图绘制故乡锡根一些正在消逝的工业建筑,画的速度太慢了,相机才成了画笔的替代。他们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却就是这么简单。
中平卓马,贝歇……都离开了。2015年,社会新闻里也零星记录着一些人的死亡,一个俄罗斯的年轻人因为自拍不甚从屋顶跌落,一个婚礼摄影师不幸在彩排中砸中脑袋去世……,除去这些新闻的噱头,我看到,死亡毫无计划地到来。
史泰德出版社创始人格哈德·史泰德(Gerhard Steidl)希望自己最终可以死在书堆里,而查尔斯·哈伯特(Charles Harbutt)这位以工作坊的方式展开摄影教学的老师,在上完工作坊最后一天的课之后,于夜晚的睡梦中悄悄地走了。
《纽约时报》摄影博客的讣告里对这位先生的称呼是:“摄影师、教师、导师”,要我看,顺序应该倒过来才是;但很显然,说他是摄影师,更能让大家接受,因为追忆一位摄影教师实在有些困难,他没有显赫的作品,如果他的学生勉为其难算作他的作品话——但这通常非常尴尬,因为有谁不会认为成功是归于自己呢?
这位曾两次担任马格南图片社主席的摄影师,在其职业摄影师生涯的巅峰退出图片社,之后转向摄影教育。工作坊之所以成为哈伯特热衷的教学方式,因为他始终关心摄影里的不可言传,他的一位学生—阿历克斯·韦伯(Alex Webb),在其20岁的时候参与了这位老师的工作坊,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到,哈伯特告诉我们,摄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语言,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假使能够用文字来替代,就不值得用摄影的方式做。
我认真地阅读了摄影师们的讣告,一个人死亡,附着在其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而去,他们的那些“名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留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1967年,慕尼黑,贝歇的作品第一次博物馆正式展览,有评论家说这展览难道是给工程师看的?但在贝歇的纪念文章里,没人在乎什么“类型学”,《纽约时报》的悼念文章,标题是这样的:希拉·贝歇,记录工业景观的摄影师,终年81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