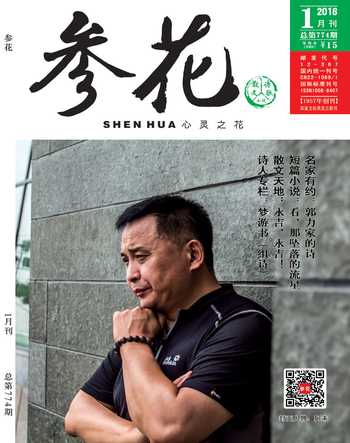雪落故园
2016-05-30陈庆礼
早晨推开窗,小区一夜之间笼罩在银色的世界里,多年未见的大雪,让人惊喜万分!我急忙穿衣出门,登上楼顶。放眼望去,蜿蜒起伏的九里山脉像一条白色的玉龙横卧市郊北部,比往常显得巍峨壮观了许多。此时此景,让我想起了远方的老家,那村庄东头的祖籍老宅。仿佛回到了昔日宅院里的情景,年迈瘦小的爷爷抱着扫帚吃力地清理积雪;奶奶踮着三寸小脚拿着竹竿正向大门外驱赶鸡鸭鹅狗;高大健壮的父亲穿着厚底茅窝挑着铁桶走向村中井台;体弱多病的母亲在锅屋里烧水做饭,忙个不停。又似乎听见老宅院子里传出的鸡鸣狗叫,水缸水桶及锅碗瓢勺碰撞的叮当声……
故乡在苏北平原,大沙河东,微山湖畔,一个偏僻小村的最东头。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老宅原是三间秣秸箔铺顶、碎麦草抹墙的碱土屋,爷爷奶奶健在时住在东间,靠北墙打了个厚厚的土坯炕当床,房间里靠南墙处还摆放了许多盛粮食的瓦缸条囤之类。屋当门一间作客厅。西头一间是父母的卧室。老宅院坐北朝南,身后有一排笔直的大杨树,屋前生长一棵盆口粗的梧桐树。树木遮天蔽日,冬天落叶,春天吐绿,我和小伙伴们在树下嬉戏打闹,鸟儿在枝头上婉转啼鸣。
1965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正在熟睡中的我被扑通一声巨响惊醒,老屋的半个东山墙突然倒塌。天一放亮,父亲就忙着向邻居求助,找地方把全家临时安顿下来,开始着手找工匠对房子进行修缮恢复。后来,随着我们兄弟姐妹渐渐长大,三间土屋住着显得越来越拥挤。父母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决定扩建三间配房。从那时起,我们姊妹几个才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到了1975年春天,大姐、大哥都参加工作,家里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了,父母亲又决定在老宅上再盖三间南屋。中间当院门,当地人叫神仙过洞,其他两间住人。还把各个房子之间的空地拉上墙头,老宅院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四合小院。当时,大姐在邻村小学教书,每天早出晚归,为了她工作方便,又不影响其他家人休息,让大姐和二姐、小妹搬进新建的南屋去住。从此,三姐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闺房。
老宅院四周挨着有五家邻居,平时和睦相处,互相帮衬,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打记事起,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周围几个邻居家玩耍。父母经常嘱咐我,对人要有礼貌。我虽然很听话,可还是时有失误,闹出不少笑话。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收入不断提高,年迈的父母用他们积攒多年的钱,对老宅院进行了一次大的翻新,将主房打倒,原地建了二层小洋楼,还把配房和院墙全部粉刷一遍,又打了2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铺了一条15米长的砖石院路。后来,父亲从县城集市上买来三棵柿子树和一棵石榴树,分别栽在院子角落。靠小院西南角开出二分多菜地,紧挨园子打了口20余米深的压水井,并把祖传下来的大石槽放在旁边用于贮水。每年春夏季节,院子里繁花似锦,香气四溢。至此,也算实现了父母晚年的一大夙愿。可没过几年,父母相继病逝,我们兄弟姐妹也都去外地工作生活,老宅院开始闲置起来。我每到逢年过节给父母亲烧纸时,才能看望一下老宅,心里总感觉到老宅院如祖传石槽一样,在那里静静地守望着它曾经的主人及子孙后代们。
我时常思念老宅小院,不仅因为它承载着童年的美好时光,还因它联系着难以割舍的浓浓乡情与亲情。
雪落大地静无声,雪中的老宅,此刻,也会和我一样,在雪中默默地回忆那逝去的岁月吗?
作者简介:陈庆礼,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期刊《百家》《歌风台》执行主编,江苏省沛县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