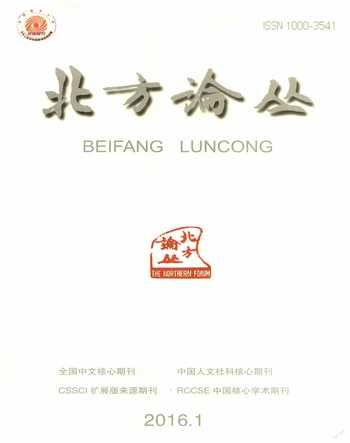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2016-05-30张良丛
张良丛
[摘 要]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关键词]迟子建;创伤经验;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50-05
Abstract: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Chi Zijians novel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an important topic. From the individual trauma and aesthetic restoration, collective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building, cultural trauma and Culture Reflection three respects,the text analyzes Chi Zijian trauma personality. thus showing a Chi Zijians aesthetic value and deep meaning. The traumatic characters in Chi Zijians novels, which is based on the “sad and not desperate” creation principle, each of the trauma characters would repair, so that people can see the hope of life in sorrow.
Key words: Chi Zijian;traumatic experience;cultural reflection
创伤不仅是一个病理学的概念,更是个文化概念。在《沉默的经验》(Unclamed Experience,1996)中, 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提出了“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她认为,“创伤”是人们经历了某一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在内心造成的阴影和伤害。心理创伤具有滞后性,而且会反复出现无法控制的幻觉。创伤理论把不同的创伤者群体作为整体来考察,将他们的创伤与社会政治期待、文化心理、社会结构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出受害的身体背后蕴含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制约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心理创伤往往以个体经验表达,很难呈现公共空间的言说。文学作品恰恰为创伤经验的言说打开了一扇窗。在迟子建的小说叙述中,我们发现有一类特殊的人物,经常浮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就是有着创伤经历的人物。迟子建从个体创伤,到集体创伤,再到文化创伤等多个层面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通过小说讲述各色人物的创伤故事,使小说具有特殊韵味。探析迟子建小说中的创伤型人物,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小说的内在结构和深层内蕴。
一、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
个体创伤主要是个人的生活历程中经历过某些事情,从而导致某种心理创伤。这种创伤总是与某种情感紧密联系。“病人在侥幸逃脱死亡、突发事故或酷刑等恐怖经历后会患上种种神经官能症”[1](p186)。普通人也是这样,在经历这些恐怖经历后也会形成一些特殊的心理经验。创伤经验首先来源于个体经历,伴随着过去的情感性记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大批有着个体创伤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其长期的生活经历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打击,在内心深处压抑大量的心理负能量,从而呈现出奇异的人格形态。心理创伤需要修复,如果没有完成修复,会产生病态人格或神经官能症。迟子建小说也对个体创伤的修复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显示出特有的思想深度。
个体创伤的千姿百态,构成一幅人生百态图。人生百态,各有各自的创伤,都深入到内心深处。个体创伤有的来源于个体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期生活经历,这种创伤直接贯穿其一生。《树下》中的七斗就遭受了母亲死亡、父亲离开和死亡、姨妈冷酷、被姨夫强奸、儿子死亡。这一次次的心理创伤对她形成一种穿透,似乎世界上所有的悲伤都降落在她身上。这种悲惨境遇很容易磨掉生存的希望,七斗一次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她之所以能活下去,因为有一段马蹄声一直回响在头脑中。《鬼魅丹青》中的罗郁,他的心理创伤来源于父亲因强奸罪入狱,母亲自杀,再加上周围男同学的侮辱,女同学的躲避。他只能靠消除欲望来获得心灵解放。《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蒋百嫂就是一个典型。她的丈夫蒋百矿难死亡,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瞒报了蒋百死亡,以钱弥补了蒋百嫂,自此蒋百只能躺在自家的冰柜里。对蒋百嫂而言,本来蒋百的死亡已经是可怕的创伤了,而日夜伴随着蒋百尸首,痛苦无法对人言说,更加深了她的伤痛,使她深陷创伤中无法自拔。由此,蒋百嫂呈现出千奇百怪的行为。与不同的男人乱搞、喝酒买醉耍酒疯、听悲苦的“丧曲”等行为都是这种创伤无法表达的表征。这种深重的伤痛,只能以奇异的方式表现,才能得到修复。
迟子建笔下创伤的描述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创伤的修复是迟子建小说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体现出作者对创伤的深刻反思。创伤的修复是研究迟子建小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学问题。创伤的修复有多种方式,如审美幻象的构造、创伤的叙述、信仰的建构,通过文学、艺术、宗教等形态达到对欲望对象的填充。对此,王杰先生指出:“对于个体来说,创伤的直接结果是个体欲望对象的空缺。欲望的投射对象由于真实的存在的缺失而转向以替代性的象征物来充任,个体的内在欲望由于无法完全对象化而走向‘焦虑和 ‘浮躁,由此产生出对审美幻象的强烈需要。”[2](p95)创伤伴随着痛苦的恐惧性情感体验,这些往往压抑在人的内心深处,会随着语境的契合被唤醒,引发早期的创伤记忆,从而和现有的创伤语境构成一种综合征。
创伤经验建构起审美幻象,依靠幻象给创伤经验的平复提供了重要前提。《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蒋百嫂和陈绍纯创伤的修复就是在审美幻象中完成的。蒋百嫂创伤的修复除了非理性的性欲释放和借酒浇愁,听民歌是最为重要的修复方式。“在乌塘,最爱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她从不进店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3](p36)。陈绍纯的歌声触动了蒋百嫂早期心灵深处的创伤,歌声的悲凉正是其构造审美幻象的媒介,在审美幻象中,蒋百嫂获得心理创伤的暂时解脱和修复。而陈绍纯唱悲调为主的民歌也是因为一次死亡的经历和“文革”被迫害,而唱民歌是他构造审美幻象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蒋百嫂和陈绍纯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在民歌构造的审美幻象中获得了解脱。同样,《树下》的七斗也是借助于内心构造的一段马蹄声来修复心理创伤的。实际上,七斗和白马上的鄂伦春小伙子只见过几次面,不是很熟悉。对七斗而言,白马和鄂伦春小伙子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七斗在内心深处塑造出的一个意象,象征着七斗对自由的渴望。这其实是七斗内心的一个幻象。而这个幻象就一直伴随着七斗,为她撑起生活的希望。
创伤的叙述把创伤变成一个表述的对象,也是非常有效的修复方式。创伤理论认为,创伤者故事的讲述首先能保护自我免受过去幽灵的干扰。当然,它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创伤经历需要有听众、有人见证,通过非直接的、非常规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经历,才能分享共有的经验。叙述者恰恰是在分享公共的创伤经验,才把个体创伤融合到集体创伤中,个体经验转变为集体经验,降低了个体创伤的浓度,才获得了心灵的修复。《世界上的所有夜晚》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的解脱,似乎是在哀伤对比中获得了解放,其实不然,她的创伤的修复是来自自我创伤被不断地引起,从而不断复述。再深入一步说,这里的“我”难道不正是小说作者个体情感经历的文学叙述吗?《晚安玫瑰》中的赵小娥,在精神病恢复之后,也是依靠叙述个人的故事,慢慢修复个人的创伤。在这种文学叙述中,创伤得到审美修复,就像一只湖蓝色的蝴蝶轻飘飘地飞到遥远的天边。
除了审美幻象和叙述的方式,迟子建小说中还提到一种重要的创伤修复方式,这就是信仰。信仰最为集中的文化形态就是宗教。宗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修复自我的方式,很多时候在于她能够提供一个想象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有一个神灵在倾听倾诉者的内心。神灵给倾诉者指出一条康庄大道,给生命的黑暗点上一盏明灯。《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在被继父出卖给日本人迷奸之后,毒死继父。被侮辱和弑父使得吉莲娜心灵遭到无限的创伤。如果没有一种很好的修复方式,她无法获得生存的理由。吉莲娜找到了她们的民族宗教犹太教,在神的面前忏悔,洗脱了自身的罪恶。这种修复方式,在文学的表述中,也成为一个审美想象的构造,彼岸世界成为一个审美的象征物。
二、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的塑造
迟子建小说中还出现了很多普遍性创伤,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创伤。集体性创伤多是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社会变革等公共原因导致的,通过集体创伤故事的讲述,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对社会的控诉和反思,从而使一个个创伤故事带有集体的共有意义。集体创伤的讲述构成了某个家族、某个阶层、某个民族、某个国家创伤表征。集体创伤的讲述对于构造集体记忆、塑造族群的历史、共享集体经验、增强集体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指向了共同的结构。当然,集体创伤与个体创伤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讲述集体创伤也是通过个体的故事来完成的。近年来,迟子建在小说中塑造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人物,也塑造了社会动荡,以及社会变革给人们造成的创伤,叙述了一个个创伤故事,显示出迟子建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反思。
集体创伤的造成,自然灾害往往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根源。瘟疫、地震、雪灾、水灾、旱灾都会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灾难,造成普遍的集体创伤,从而构成一个个叙述,叙述着伤痛中人的故事。迟子建的小说也对这种集体创伤进行了讲述。《白雪乌鸦》就是其中的典型。小说叙述的是1910年的哈尔滨大鼠疫,通过对鼠疫中的哈尔滨老道外的民众日常生活的讲述,塑造出自然灾害中的民众面对集体创伤的人生百态。王春申在妻子和儿子死亡后,选择了参与到鼠疫死亡者的尸体搬运中,在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了心理创伤的修复。于晴秀则是在公公、丈夫和儿子死于救灾中,默默地承受了创伤。伍连德临危受命,从整体上拯救了哈尔滨的民众,长子长明却死于食物中毒。这些集体创伤事件的讲述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讲述,背后也充满着讲述者本人的思考。“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4](p259)。迟子建讲述的这个集体创伤故事,本身并不是要呈现历史,而是在寻找创伤背后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崇高品格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社会动荡不安也会造成很多悲剧人格,迟子建的小说充分表现了这类人的创伤。《伪满洲国》中的杨浩更是一个社会动荡的牺牲品。在灾难发生之前,他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围绕在他的周围。仲秋节,他们一家五口来到了平顶山煤矿和奶奶叔婶团圆,全家人却遭到无妄之灾,只活下了10岁的他。他所遭受的创伤也是从天而降。因抗日游击队袭击了日本鬼子的采矿所,平顶山的百姓就受到了日本人迁怒,全部被屠杀。杨浩却非常幸运地在屠杀完毕和掩埋之间醒过来逃出来。逃出来后,杨浩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死去的亲人时常出现在眼前。从常理来推断,一个年仅10岁的儿童在这样一个屠杀事件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迟子建的笔下,杨浩却存活了下来,而且被一个老汉救回了家。这种描述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很明显,杨浩的创伤描绘,迟子建是在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深深控诉,让人感到的是揳入灵魂的伤痛。创伤理论认为,创伤的修复最为有效的手段是讲述,通过讲述自我的创伤经历,创伤会慢慢得到修复。而在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之下,作为幸存者的杨浩,却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心灵创伤,只能把伤痛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慢慢地舔舐自己的伤口。悲愤无处说,幼小的心灵不断地承受创伤的折磨,这种控诉不是更加令人记忆深刻,难以忘记吗?杨浩的创伤正是近百年来多灾多难民族创伤的表征和寓言,伤痕累累无处言说,只能自我慢慢地修复。
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不是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变革,同样会给人们带来普遍性创伤。迟子建的小说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的百年历史,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在她的小说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幅活生生的心理图画。《树下》中的有精神疾病的船长就是社会变革的牺牲品。他本来是一个森林勘探工作者,却因为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坐了7年牢,在此期间他的孩子夭折,妻子悬梁自尽。出狱后,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精神极为不正常。很明显,船长是因社会运动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修复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办法就是返回过去,在回忆中获得心理平静。这个回忆的载体就是一条对他有恩的狗“雪地”的第九代玄孙,他给狗讲故事,爱抚狗,对狗发脾气,其实都是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中获得心灵平衡。而当他在众人阴谋和冷眼中被剥夺了这个幻象后,就在被送往精神病院的途中自杀了。迟子建塑造的船长形象传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文革”的社会变动中,船长不是一个单独的形象,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典型的塑造,迟子建反思了那场社会运动给中国带来的集体创伤。
文学呈现集体创伤就是提供给每个人一次回忆,是集体思想和情感经验的再现。“每次回忆,无论它如何个人化,即使是有关尚未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回忆,都和其他许多人拥有的一整套概念相关共生:人物、地点、日期、词汇、语言形式,即我们作为或曾作为成员的那些社会的全部物质和规范的生活”[5](p36)。迟子建对集体创伤的描述,并不是简单呈现一个悲伤的故事,引起读者唏嘘感叹。集体创伤是许多人共同承受的创伤经验,其具有共同性。共同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渐渐地沉淀到历史中,变成一种潜在的社会无意识。只有借助于相同情景的浮现,社会无意识才能重新进入集体意识中。迟子建对集体创伤的文学浮现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激活了人们共同的经验,恢复了共同的记忆。
三、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
文化是族群的生活构建起来的生存方式,每个族群都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自己特定的文化。族群成员只能在其文化中获得身份认同,构成一种文化标志。一旦超越该文化区域,作为个体的人就面临如何重构文化身份的问题,有可能造成文化创伤。文化创伤主要指在文化转换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身份的丧失,而造成的心理伤害。文化创伤能影响整个群体的存在状况。当然,文化创伤不全是负面作用的,还具有积极意义。从文化创伤中,人们可以更好地反思文化状况和历史,从而构建新形态的文化。对于少数族群而言,文化创伤可以唤起集体记忆,从而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不失为一种讨伐主流社会压迫的边缘反抗中心的策略。在文学表征当今社会文化转型的今天,文化创伤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迟子建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迟子建描述了文化冲突中的文化创伤,人们可以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族群文化进行反思,从而思考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最为合适的文化,才能提供诗性生存方式。
文化冲突会带来个体命运的转变,造成一种心理创伤。《白雪乌鸦》中的翟芳桂本来是一个普通农家大女儿,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天晚上她去河边洗头,回家的路上,知道因信仰基督教父母和妹妹遭了无妄之灾被活活烧死,她已经无家可归了。自此一系列灾难陆续降临到她的头上。通知她灾难消息的张二郎却趁着混乱强奸了她。为了生存,她跟随了张二郎,张二郎却因为教堂的钟送了小命。随后,她到哈尔滨投靠姑姑,在姑姑死亡之后就被卖到了哈尔滨的妓院,成了妓院头牌香芝兰。翟芳桂的创伤完全是义和团运动排外导致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创伤。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对洋人和华人基督徒进行了暴力运动。正是这个社会事件,直接导致一个与此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折,遭受了无尽的痛苦。迟子建描绘的是翟芳桂的创伤,其实更是从文化上反思义和团运动排外的盲目性,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思了一个文化事件。义和团运动是一种文化冲突,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而翟芳桂不过是这个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转换也会给人带来文化创伤,很多人成为选择的文化的钟情者。《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伊莲娜是一个踏入现代社会的,而被现代化文化弄得遍体鳞伤的人物。伊莲娜是鄂温克女子,她也是艺术家。她的艺术启蒙发生在鄂温克居住地的河边,是跟外祖母学习岩画开始的。自此,她就和祖居地的山水丛林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灵魂扎根在鄂温克文化中。当她作为鄂温克第一个大学生踏出丛林,走向外面的世界时,生存之路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自此,伊莲娜就陷入了两难中,她每年都背着画架回来看外祖母,“伊莲娜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回来了”[6](p250)。伊莲娜挣扎在痛苦中无法自拔,最后她辞职了,重新回归到山林中。但是,她仍然没有完全回归,在创作完两幅皮毛画后又进城了,因为她仍然没有找到灵魂深处真正需要什么。可见,这时的伊莲娜虽然回归灵魂的呼唤占了上风,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回归,直到她看到妮浩祈雨后,才彻底贯通了内心的灵魂,受伤的心灵才开始真正地得到修复净化。她拿起了笔开始了两年的祈雨画创作,画作完成后,伊莲娜化作一头洁白的驯鹿,真正地把生命融入到她寄托灵魂的山水中。伊莲娜的人生就是寻找如何修复骚动的心灵的历程,她不安的灵魂就是现代文化和鄂温克的原始文化冲突产生的,是在现代文化还是在原始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构成了一种心灵创伤。很明显,这是一种文化创伤,是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造成的。迟子建最后把伊莲娜的归宿放在回归原始神性文化中,心灵的创伤获得真正的修复。无疑,这是一种诗性处理方式。
不但是少数族群进入现代化文化中会感觉到身份认同的困惑,造成文化创伤,同样,跨入异域文化的人也会遭受心灵的创伤。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描述,在她们身上异域文化带来的创伤明显地体现出来。《北极村童话》中的“老苏联”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可怜人,但是她的最令人可怜之处却是孤独。作为一个苏联人尽管认识汉字,会说汉语,但在北极村村民的眼中,她始终是一个“老苏联”,无法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也无法融入北极村。只有一个文化身份还不是很明显的7岁小女孩,才能克服大人给她灌输的观念,凭借好奇心偶尔进入到她的世界。而老苏联却和小女孩只能形成感情交流,散发出慈爱的光辉。但她毕竟无法获得更多的情感交流,最后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孤独地死去了。在《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中,苏联老太太又出现了。这里的苏联老太太命运好多了,丈夫跑了却留下了两个儿子。但是,她还是被周围人排斥,“外祖父就嘱咐我,不准去老太太家里玩”。由此,在周围人的冷落中,“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7](p214)。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看着小姑娘吃完蚕豆,跳舞后哈哈大笑,最后也是孤独地死去了。我们看到,苏联老太太有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它根源于文化语境的差异。外来人的文化身份往往在新文化语境中很难获得,只能被排斥在该社会生活之外。正如麦格所言:“除了一套共同的文化特性,族群成员之间展现出一种社群意识,也就是一种亲切的感觉或紧密联系的意识。更简洁地说,就是族群成员间存在着一个 ‘我们。”[8](p10)而后来进入该群体的人,却是他者,是被这种社群意识排除在外的。她们无法获得认同是必然的,也是无奈的。
由此可见,迟子建是一个典型实践型知识分子,她“不仅是书斋式的、学究式的、批判性的,更主张走向操作和实践,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改变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的浓厚的精英主义迷雾和乌托邦色彩”[9]。从创伤理论的角度透视,迟子建小说文本具有特殊的意味。她的小说从平凡的小人物故事出发,对个体、社会、族群、文化等方面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多维度透视,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感悟。从平凡的人物中见出深刻的内蕴,体现出作家的深刻经验式感悟,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当然,迟子建小说创伤人物的塑造,还是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一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留下了希望。或许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说的那样,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到对“存在的遗忘”。在创伤经历中投射出的希望的力量,或许是迟子建小说更为吸引人的地方。
[参 考 文 献]
[1][英]安东尼·斯托尔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M]尹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王杰审美幻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4]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7]迟子建黄鸡白酒[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8][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第6版[M]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9]张玉勤历史·社会·实践:本尼特美学研究的理论维度[J]北方论丛,2010(3).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