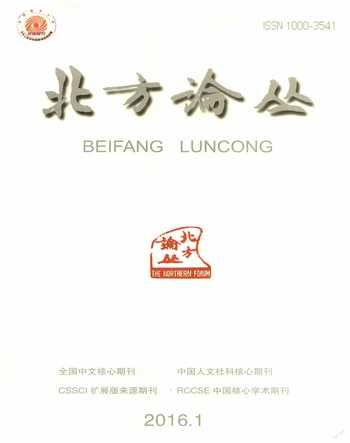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2016-05-30王立
[摘 要]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关键词]复仇主题;“弱势群体”;“食仇母题”
[中图分类号]I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13-06
如何复仇?复仇成功之后怎样处置仇敌?复仇的结果为何?实际上涉及复仇主体实施计划的缘起、过程与具体方式,以及本族群的社会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与复仇的集体潜意识等更深层次的理念问题。比较西方民族的复仇文本书写,则不难发现,“食仇”以雪恨的复仇过程与处置手段常常会被详尽而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食仇”叙事模式,除了有表现复仇者咀嚼苦涩的“成功”与泄愤的异变快感,还荡漾着本民族遥远记忆的内在张力,是民族文化基因对扩大化复仇行为——“食仇”的怂恿与默认,也是社会政治伦理建构的民族基本心理素质与行为规范。
一、“食肉寝皮”与古代复仇行为道德意识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甘心”字眼时常出现,且常常用以表现女性或善良弱势群体的心理追求与最终愿望。《诗经·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这里的“甘心”是情愿的意思。而《左传·庄公九年》写:“管(仲)召(忽)仇也,请受而甘心焉。”注曰:“言欲快意戮杀之。”《后汉书》叙述吴许升妻吕荣,丈夫为盗所害。凶手被捕获后,她“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获刺史的许可:“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1]
《列子·汤问》称:“魏黑卵以暱嫌(私恨)杀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来丹谋报父之仇。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顺风而趋。虽怒,不能称兵以报之……誓手剑以屠黑卵。” [2] 直到阮葵生《茶余客话》还转述宋潜溪《王先生毅小传》:“山阳殷子通,以儒术教授,里中人熏为良善者众,及邻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歼之。长吏恶攘其功,使人杀子通,其门生毛术手刃杀者,枭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义。”[3]清代《镜花缘》写多九公等见披虎皮的少女:“把大虫胸膛剖开,取出血淋淋斗大一颗心,提在手中。收了利刃,卷了虎皮,走下山来。”原来是为母报仇的骆宾王之女骆红蕖以药箭射伤大虫,取虎心祭母[4]。可见“甘心”,亲手处死仇凶,属中国古人理想化复仇的书写模式。这样的书写理念当与下列社会群体意识密切相关:一是家族成员的伦理义务。活着的亲人有义务为被冤杀者报仇,以维护本家族的生存尊严。二是族群远古仇杀记忆的遗留与适时宣泄,这是族群延续的内在调整机制,是“适者生存”法则的道德化规范。三是文本记忆与民俗记忆交互强化作用。这令个体化或家族化的复仇行为社会化、道德化以至政治化,成为被动接受的社会存在价值观。如此一来,古代“杀仇”报复行为书写,不仅是猎奇与传奇的叙事行为,还是在展示族群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普遍民族风习。对孝子而言,其常态是循规蹈矩的道德模范,而复仇孝子身体力行、直接操作的“杀仇”,不仅对个体存在价值非常重要,简直就是最基本的仪式性社会人的必备要求。普通男性或许也会因其模仿孝子的杀仇行为,也获得“孝子”尊号,即使他在亲人活着时并未显示出“孝悌”品质。这或许是道德价值观主宰的社会政治伦理掌控下的中国社会,多有超越社会进程的原始血腥复仇模式的根本原因。
然而,亲手执利器杀死仇凶,对于暴怒的复仇主体来说,往往还达不到泄愤目的。在手刃仇人行为实施过程中,复仇者的情绪可能还在继续变异之中,于是“啖仇食仇”之肉的行为每多发生。《北史·序传》写李充打胜仗后,“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魏书·獠传》载:“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刘餗《大唐新语》卷五载王君操报父仇:“密藏白刃刺杀之,刳其心肝,咀之立尽,诣刺史自陈……州司上闻,太宗特原之。”《新唐书·孝友传》转述王君操报父仇更细致:“密挟刃杀之,剔其心肝啖立尽,趋告刺史曰:‘父死凶手,历二十年不克报,乃今刷愤,愿归死有司。州上状,帝为贷死。”有意味的是,当初仇人作恶行为似被叙事者有意忽略,却“理直气壮”地“刻意”描绘复仇者用“利刃”刺杀并生食仇敌“心肝”的过程。因此,“食仇”行为的另一面常常被忽视:复仇者同样是残忍的。只是仇敌先于他杀死他的亲人,这是一个允许“非法”杀人的族群,只要时机成熟,并无法律的规范,可以情绪化地、适应社会需要、合乎社会风习地杀死对手。也就是说,在社会道德规范下的伦理价值取向维度上,“仇敌”行为绝对合乎族群正义。
由于男性复仇者的先导轨范作用,女性复仇主体,有时也是将如此观念落实到行动中。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写戴十妻梁氏,丈夫被通事无理害死,这个贵家奴想用牛和银子赎罪免死,但梁氏表示:“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人不可夺其志,问她敢亲手杀死这人吗?梁氏说:“有何不敢?”取刀便欲亲手砍斫:“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 [5]
“食肉寝皮”在古代复仇作品中,大多并非仅只一句口号,而是诉诸行动的泄愤快意之举。明末清初《八段锦》第七段写良家妇女韩氏,因无赖应赤口诬陷,遭丈夫打骂避难尼庵,众尼对这恶人“恨不得一朝撞见,食其肉,寝其皮”,利用其好色灌醉捆住手脚,一块块咬掉其肉后才杀死 [6]。文本渲染的“一块块咬掉其肉后才杀死”复仇方式显然带有强烈的民间狂欢意味。在人类“食仇”本能冲动下,裹挟着群体从众心理的交感作用,似乎在“正义”复仇行动中,在实施现场的观众就应该“同仇敌忾”,分一杯羹才能消解“共同”的怨气,以实现合乎道德的“快意血腥”,没有人试图阻止“苦主”的报复行为。清代更有对“战俘”施以“挖心挖眼”的酷刑,施刑者的“果敢”在印证着古老虐囚规则也是当下的“合理合法”报复手段,说韩雍征伐时,取俘数人,“探心脑啖之,立尽。见者失色,而雍谈笑自若”;而某督抚公镇海疆“凡遇剧贼,辄抉其目珠”。载录者竟会从社会效果上予以肯定:“窃谓此法以处剧盗大猾,纵不即行诛戮,亦可杜其后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淫刑为御史所参矣。” [7]话语权力执掌者依仗社会赋予的威势,肆意残害被俘对手,则展现的不独是胜利者的生杀予夺威权,更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观念作祟,这也是明清时期“蛮夷”不开化民族的族群标志及远古潜意识再现,是蛮夷等级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形象化书写。
食仇,作为远古巫术思维孑遗,原始人那里通常是吃人心,“以求吃的人得到心的原有者的素质”。弗雷泽总结:“吃了神的肉,他就分得神的特征和权力。神是谷神,谷物就是他的主体;神是葡萄神,葡萄汁就是他的血。所以信徒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就是吃了他的神的真正的血肉。”[8](p717)而从上述古代中国“食仇”母题书写,则毕竟以泄愤为主,“增添勇力”则是复仇行为的衍生品,融合着“厌胜术”痕迹,意图以消灭仇敌的肉体来阻止其转世投胎与伺机报复,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
二、“阉割”负心汉与女性生存权的社会性困扰
从跨文化的角度,这样的观察当是很真切的,即中国古代复仇文学强烈的伦理功利性。长期居住中国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东方,西方与小说》中指出:“宣传性的小说,在西洋是极力反对的。在中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每本小说都带有一种说教的态度(我不能说他是目的),虽然除了佛教故事很忠实的带有宗教目的之外,我不相信还有一部完全说教的小说,但是每本书里,都有小小的道德观念含在它主要的目的里。一件可怕的暗杀案发生以后,当我们正在恐怖的状态中,就会发见一件报复旧仇的事情,而凶犯是曾经被死者伤害过的,于是这暗杀便马上不是一件罪恶而是一件道义的行为了……换句话说,中国小说根本上是有趣味而有人性的。半途里加上一样东西去适合社会的惯例,因而每个人都满意了。”[9] 赛珍珠揭示出“暗杀”事件的问题核心。这也正是关注“情理”的家族核心社会结构的政治功能,完全可以忽略“法理”的社会规范价值。
人们熟知,古代民间活跃着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母题,对于这类负心汉的“报复”是复仇文化圈中普遍性民俗心理之一,而另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阉割”负心汉母题,却罕有提及。母题极具性别文化色彩,并涉及种族延续与生存权利再分配等社会群体核心价值观问题,虽有叙事,欲说还休的说教反倒显示出社会性的困扰。比较众多复仇手段与方法,女性“阉割”负心男子阳物以报情仇,当属一种奇特的复仇方式,较早表现在女鬼向负约丈夫报仇的描写。南朝刘宋时袁乞妻临终得到丈夫不忍再婚的承诺,可丧服过即再娶,于是亡妻白日显形责备:“君先结誓,云何负言?”随即“以刀割其阳道,虽不致死,人道永废”[10]。尽管此时作为复仇主体的鬼灵总体上神通还不算大,却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严惩了负义违约者,爽约便恩断义绝,也蕴含着不可随意“承诺”的行为规范。夫妻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女性作为行为主体的复仇叙事,折射出中古汉译佛经故事所挟印度民俗传说的影响,具有与幻化、托梦、仙师培育、神奇兵器等母题交叉融汇等性别意味[11],似乎作为弱势群体的复仇,就必须采取超常规方式。而对于成年须眉男子,只有女性才有近距离接触并可出其不意袭击。虽民间此类故事肯定代有不绝,在宋明理学的阻遏下,直到清代这一具有性别色彩的复仇方式才较多地传播和被载录,当然其中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固有的性别冲突,种族歧视与种族间等级观念亦不可忽视。明清时期的男性读书人,借助女性“阉割”阳具的奇异复仇模式,表达男权社会很重视“弱势群体”的女性化复仇心态及其行为逻辑。
如潘纶恩写汉阳妓女曹翠之资助商人姚崇恺三千金,有丝罗附松柏之托。不想姚返乡后别娶,翠之据理将金索回,对负恩者恨之入骨。后姚到汉阳理业仍找翠之叙旧,翠之乘负心子醉酒,“诱姚而宫之”,其在被割去生殖器后负创蒙羞逃回而死,随后翠之还特意将阉割下的仇人“情根”保存。尽管后来被告官处死,得到评价甚高:“曹虽女流,其行动则慷慨丈夫也。姚以丈夫而恋恋有儿女之私,冤对相逢,谁能堪此夫?非自蹈水火乎?” [12]叙事者的“感佩”之言,不同于之前男性对女性的“怜悯”之情,有明显的男性群体自身沦为种族压迫社会中的下层之后的感慨,深味被抛弃女性的社会“多余人”处境与自暴自弃,甚至同归于尽的毁灭性感受,这种矛盾心理和两难评价也正是多数下层读书人的真实写照。清代《述异记》讲述少女无奈之际向养父复仇。她先在畅饮后“作羞涩迎拒之态”:
女预藏剃刀,以被冒(养)父首,左手执其势,右手持刀,即时割下。天成负痛起,扼女喉气绝。少顷,割处血流不止,昏晕仆地。女得复苏,遂持势并刀,出喊邻右。众咸入验,无不骇异,即引女至秀水县陈令名綍者。陈询验既确,即告郡公,大为叹赏。立呼方姓之子,当堂完姻。天成被创深重,三日,痛苦难堪,服毒毕命。[13]
另一种似乎较“温和”的复仇方式也具有同样效果。满族作家和邦额写林澹人邂逅丽人余白萍,两人欢爱,可是林科考得第却许婚富家女,成婚时白萍即来责备其薄倖:“乃命二鬟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数十,更以溪沙傅其阴,置诸石上,而后舍去。乃林之被辱也,身如梦魇,转侧由人。次日黎明方可动步,遂踉跄而返……林自此觉私处冷如垂冰,缩似僵蚕,百治不举,盖已病萎。新妇失所欢,不能无外遇。” [14]女鬼用让负心汉“阳痿”的方式报复,实际上也扩展到让仇人断子绝孙的更大范围。毛祥麟也写某高官公子纵仆劫外来卜者女,次年遭入室挟持,被不速之客“去其淫具”,留书:“公子不法,本当杀却,今姑从宽,去势留命。”[15] 原来是太华山剑侠借点穴术以“同态复仇”方式严惩作恶者,很可能是受害人求助剑侠前来行使正义。研究者认为,这种以割去阳具方式教训怙权纵淫的公子,“不过女剑侠尚存一念之仁”[16],即留下性命,甚是,这也符合清代女剑侠来去如风的一贯行事风格,与女性复仇这一独特方式相契合。
此系列复仇方式,都带有强烈的性别文化意味,但仍有“同态复仇”的无意识遗存。似乎非正义的最初肇事者,其“作恶”在先,其行为与身体的某一特定部位有直接关系,因而所受仇报也当与这一部位(器官)不可分开,成为复仇者泄愤迁怒的一部分。拉法格《正义的起源》指出:“产生同等报复法的复仇行为对于原始人是个人自卫的方法。原始人发展复仇的情感,给它一种为现代文明所不能有的生活力和力量,因为对于现代文明人个人复仇失掉了作为方法的意义。让欺负人者简单死去是不能满足的,需要让他经过非刑拷打紧张地死去,恢复了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可怕的复仇行为的中世纪的诚笃的基督教徒就是这么说的。父权制初期的人们为复仇欲所苦恼,只能理解可怕地好报复的神:宙斯惩罚自己的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而耶和华把自己的复仇延伸到七代。” [17]对于复仇对象的愤恨,扩张到对象身体的每一部分,而那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最应首当其冲成为毁损的目标。这一部件正是男女性别的本质区别,也是社会地位划分的社会生物学基础。大多数女性因其体力以及见识短浅,偏执地认为,只是某个男性的某个部位对她形成致命伤害,而忽略了性别的社会结构张力。导致女性运用性别优势——也是其生存的劣势——诱惑并泄愤,这样的认识误区与报复手段正是全社会女性价值观与生存权利观的文化结果。作为个体女性复仇行为的结果,更是男权社会男女两性生存权利对抗的极致,只是在种族压迫社会环境中,下层读书人才不情愿地发现男性的女性化生存困境,真正关注到“食仇”模式的亚型——“阉割”母题的警世价值:一是警告个体男性勿超越权利与义务,要给予女性以适宜的生存环境与相应的生存权,否则“玉石俱焚”自杀式复仇将不再是文本书写;二是“阉割”复仇模式的主要行动者是女性,既给予男性个体以最大羞辱,也强化了两性间的不信任感,动摇社会结构基础,形成对种群延续功能的最严厉惩罚,从而最终反作用于全社会的道德政治机制。
三、“食仇”叙事:他族情仇雪恨书写模式的文本间性
通过对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基本考察,可知西方式复仇偏重于从精神方面折磨仇敌,达到意志与灵魂的双重毁灭,精神复仇甚于肉体惩处。而传统中国则是通过残杀肉体以泄愤,着意于宣示复仇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格在复仇进程中完善与提升,以及族群对此行为的认同与传扬,是个体存在伦理精神与社会道德政治功能的融合。完成复仇,实际上也是品尝成就伦理使命的快慰。“弱势群体”复仇特别是“食仇”的肉体毁灭,其意义远远超越杀仇食仇报复行为本身,而有更深远的社会政治功能。中西方“杀仇”“食仇”叙事中“异中有同”的书写模式,达到复仇者“社会价值提升”的异曲同工之效。
法国巴尔贝·道勒维小说《一个女人的报复》叙述了一个新奇恐怖的复仇故事:“其中没有流血事件,既没有刀剑,也没有毒药,说到底是个文明化的罪行。”[18](p310) 说一位高贵的公爵夫人为替被丈夫残忍杀害的情人(当着妻子的面让狗吃掉其心)复仇,潜逃后甘愿当了低贱的妓女,她深知仇人(公爵)对名誉比对生命还更加看重,“想侮辱他的名誉,而不是杀死他”,病死前特意让人把其头衔与妓女并列写在棺柩与墓碑上[18](pp306-345)。对视名誉如生命的公爵而言,夫人出轨以至于沦为妓女,令其无地自容,更是对其掌控家庭能力以至社会政治地位的质疑与嘲讽,这远甚于肉体生命的毁灭。小说折射出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结构中个体功能张力的形象化展现,每一个体都有生存权利与存在价值,残害剥夺他人生命者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而真正以残杀仇敌方式泄愤的叙事文本,则至少可追溯至卜伽丘《十日谈》所写菲尼美达的故事:萨莱诺亲王唐克莱寡女绮丝梦达,爱上父亲侍从纪斯卡多,生死不渝,但专制的父亲发现后怒不可遏,女儿坚持说看好纪斯卡多的品德才能,可是萨莱诺亲王还是低估了女儿意志,不用暴力:“却打算惩罚她的情人来打击她的热情,叫她死了那颗心。”派人绞杀纪斯卡多把心脏盛在金杯里,说“把你最心爱的东西送来慰问你”,绮丝梦达此时已配好毒液,面对情人心脏恸哭后服毒,唐克莱难过地遵遗嘱合葬二人 [19](pp326-368)。第四天故事九也写罗西雄爵士刺死妻子的情人,取出心脏烹成精美菜肴,说给妻子吃野猪心,夫人把心都吃下后才被告知,是不要脸的女人“情人的那颗心”,妻子即刻怒斥其不公正:“天主在上,我吃了他那颗高贵的心,从此再不吃旁的东西了!”投下城堡而死[19](pp424-428)。未料复仇后果的罗西雄惊吓懊悔,惧责出逃。当地居民将一对情人合葬,刻诗墓上为念。对此,仅从一般性的喜剧、悲剧和狂欢节理论概括不够,似应把问题放到世界性的复仇习俗和心理表现上认识[20]。比较上述,亲王唐克莱是以“杀死”对手的方式报复对手超越等级的爱情,而女儿绮丝梦达又以“自杀”的方式回敬父王的专横,唐克莱将二人合葬表达了对个体追求平等自由爱情的认同尊重。而故事九中罗西雄畏罪出逃,当地居民把一对情人合葬,两个维度的行动均表明:罗西雄刺杀情敌并“吃掉”是伤及无辜的“扩大化复仇”,有违爱众生的基督教精神,不被大众认可。也就是说,叙事者对于追求真挚爱情者给予同情,为其合葬,寄希望于在另一空间中他们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崇尚“同态复仇”,以及更重视个体存在价值,此与中国传统文本中“甘心”与“快意血腥”有本质不同。
类似《十日谈》的故事,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费伦佐拉(Firenzuola,1493-1543)半个多世纪后所写奇特的复仇故事说,乔万尼神父爱上了托尼亚,托尼亚贪图他允诺的一副袖套就幽会了,但诺言未兑现,话语尖刻,恨之入骨的托尼亚就联合丈夫恰尔帕利亚设圈套复仇:神父被恰尔帕利亚兄弟当场捕获,大骂着要“吃掉这个负心婆娘的心”,将神父裸身装入大箱,他那东西因被压住受伤而肿痛难挨,只得拿起剃刀,亲手在自己身上实现了“恰尔帕利亚”的复仇,成为一个“没有那玩艺儿的人” [21]。乔万尼神父确实受到了严惩,但托尼亚在失去女性尊严同时,也失去了丈夫及亲人之爱,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报复模式显示,叙事者是以薄惩恶人的“狂欢节”式情节,暴露了男性依仗社会地位优势与女性依仗性别优势以实现贪欲的性格悲剧。事实上,法国巴尔贝的小说《一个女人的报复》也是此类母题的延展,但复仇惩恶功能显然更深远、更沉重、更令人反省。这说明不同文化传统辐射下的“杀仇”“食仇”模式相似而本质各异。
民俗学家研究美洲印第安人“通奸和惩罚”母题时,注意到平原印第安人故事:一个丈夫发现妻子与一条蛇通奸,他将蛇杀死并惩罚了妻子,有一些异文则讲“他用蛇肉或蛇的生殖器招待妻子”;而有关女人与其蛇情夫的故事,在高原地区和太平洋北岸的异文有:“女人不知不觉地吃下了自己的被谋杀的情人的某些器官。这是一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性的情节,在欧洲,通常情况下招待女人的食物是其情人的心脏。”[22]可见,不独小说《一个女人的报复》,包括其他模式各异的“杀仇”“食仇”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报复方式表现,说明“食仇母题”的普遍性,也说明族群心理进化的相似性与控制法术套路的趋同性。
此外亦不能忽视,叙事者关注到“杀仇”“食仇”个体力量彰显过程中反社会性反伦理道德与反社会政治性。在当代小说中,这被透彻地揭示出来。较多承领西方文化影响的金庸,其《天龙八部》恼恨丈夫段正淳用情不专的刀白凤:“要找一个天下最丑陋、最污秽、最卑贱的男人来和他相好。你是王爷,是大将军,我偏偏去和一个臭叫化相好。”她与乞丐段延庆生下了段誉,以破坏“仇敌”遗传基因改变其族群血统,实行报复。刀白凤的“复仇”,表面上看颇类似法国巴尔贝小说中女主人公甘当妓女以向无情丈夫泄愤,但从更深层面上看,又是最残酷可怕的报复,是男性群体与个体都不能承受的种族延续之重。因此,可以说,女性复仇这一母题在金庸小说中达到“中西合璧”的完美结合。
至于复仇母题中的“食仇”行为的民俗基础,文献载录的意义指向较为复杂。弗雷泽在讨论“杀人者的禁忌”时指出:“胜利者在胜利的时刻还要加以很不方便的限制,其动机之一大概是害怕被杀者的愤怒的灵魂。而这种对于要复仇的鬼魂的害怕,确实影响着杀人者的行为,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明显的证实。”[8](pp318-319)吃掉仇人身体,的确可宽慰地认为是免于被报复了。在人类学有关原始部族的研究中,这被理解为一种“顺势巫术”,即具有增长勇力的功能。不过,在欧洲《十日谈》等小说中写“食仇”,却不同于泄愤与添勇,而主要是为了在精神上刺激,折磨仇人及共案者的灵魂。
相关的习俗风尚制约复仇目的手段的选择,而这种目的手段往往又反馈复仇主体对仇人雪恨的思考。由于偏重从精神上折磨仇人的泄愤方式,而不是在较短期间内干净利落地了账,复仇所费的时间与周折必定要多得多;而在较长时间的痛苦煎熬中,复仇主体也滋生出不愿让仇主一下子结束生命的想法,以为这样做未免有些太便宜了仇人。事实上这也是原始心态中“同态复仇”的心理遗存,期望仇人也像自己或受害者那样历尽苦难。早年学者曾揭示,如1918年刘半农曾注意到,中外小说(这里的“外”其实主要指西方、欧洲)对残酷场面的描写及接受态度大为不同,其指出外国戏台上往往不是直接演出谋杀、决斗、战争诸事,只是在谈话中用悲恻的神情表白,死刑都在隐僻处执行,灾疫等也不在贵客妇女前谈论,而中国则惨杀之事尽可在大庭广众下谈论:“官厅里杀起人来,必守着‘刑人于市,与众共之的古训;戏子们更荒谬,‘三更三点的见鬼,‘午时三刻的杀人,几乎无日不有……试问人家到了将死的地步,中国人全无恻隐之心,反要大开玩笑。此种‘忍心害理的思想,是人类应有的不是?”[23]其实,类似的虐杀描写,在古代中国复仇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体现的嗜血欣赏趣味是无可否认的,但个体“食仇”行为何以会具有普遍性的快意?不完全是族群的嗜血本性,而更多显现出族群结构间每一受压迫个体扭曲的奴隶性心态的对象化宣泄。
这样看来,中西方复仇主题中的“食仇母题”就蕴含着比较复杂的族群文化意义与社会政治结构功能。
首先,从叙事模式上看,西方较为偏重复仇者对仇敌灵魂的冲击与掌控,偏重于复仇进程中仇敌精神被摧残的过程描绘;中国则较为关注复仇事件本身的结局,包括关注复仇者自身在成功复仇后的命运。二者一个是侧重在个体人性的揭示,另一个是侧重在个体面对群体舆论时的伦理实现。
其次,从叙事结构手法上看,西方的复仇书写,注重复仇主体性格异变与人格完善的过程显现;中国则偏好于主体行为的社会伦理化与教化功能,夸饰性的屠戮行为描绘,意在追随舆论张力。为迎合民众的接受心理,省略了必要的心灵冲突与心路历程描叙,而让最为痛快淋漓的仇凶毁灭的结局尽快地充分展露,以期大快人心,得到族群社会的潜在认可。在这一视点上看,说古代中国复仇主体具有嗜血习性,复仇的成功与彻底的感觉与评价,往往包括“食仇”这一仪式化的举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次,从文本审美意义看,西方复仇之作常引发人们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让人反思深省;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愉悦感,让人们在惩恶扬善的印证中,一再加深对善恶伦理实现必然性的认识。以西方复仇文化观为参照,可以对中国传统复仇观进行深刻的反思。从食仇泄愤角度来说,民国武侠小说家就在某些复仇残忍时就罕有涉笔[24],食仇描写的“缺项”也是对国民性批判的体现。
最后,在相关文献中不难发现,“食仇母题”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文本的自有之意。这一母题在中西方复仇叙事中虽有上述区别,但其具有的相似性也不能忽略。一是趋向于以“吃掉”的生物本能的方式结束复仇的恶性循环;二是趋向于“力量”的较量,包括体力、智力与权力。二者除了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学的文本间性及其影响,更重要的当是种族心理习性进化过程的相似性,是族群古老记忆的当下显现,这是至关重要的。从另一个维度表明,“食仇母题”的书写往往不是叙事者无意的猎奇之作,而有更深层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报仇绝不仅仅是个体的报复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呈现为泛化的社会期待,这说明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些层面的缺失与不完善。种种原因导致女性或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受到强大外力的挤压,而族群社会又缺乏自动调节机制,以至“杀仇”“食仇”这一反社会反政治道德行为出现。“恃强凌弱”丛林法则的社会化、政治化、合理化,是“手刃仇敌”并吃掉的政治基础。这是“食仇母题”最值得研究与反省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九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4]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续夷坚志·湖海新闻续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4)[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7]朱梅叔.埋忧集:卷十·挖眼[M].长沙:岳麓书社,1985.
[8][英]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9]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刘敬叔.异苑: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1]王立,等.男权社会中的完美女性——《水浒传》中的侠女复仇故事[J].山西大学学报,2010(5).
[12]潘纶恩.道听途说:卷四·姚崇恺[M].合肥:黄山书社,1996.
[13]王文濡,辑.说库:下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
[14]和邦额.夜谭随录卷八·白萍[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15]毛祥麟.墨余录:卷十四·某公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龚鹏程.武艺丛谈[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17][法]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18]郑克鲁,选编.一个女人的报复——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9][意]卜伽丘.十日谈[M].方平,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0]邱紫华,陈素娥.十日谈中的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J].四川大学学报,2003(2).
[21]后十日谈[M].王惟甦,罗芙,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22][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3]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刘卫英.《蜀山剑侠传》女性因爱生恨复仇的主题史开创[J].西南大学学报,2011(3).
(作者系大连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