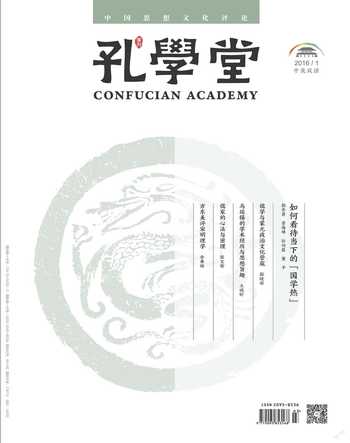儒学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
2016-05-30林庆
摘要: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源远流长。虽然最早传入的时间定为西汉之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作者认为,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儒学已经深入到大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教育、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随着元代科举制在大理地区的实行,至明清时,儒学思想更加深入民心,尤其深刻影响了白族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涌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精英。
关键词:儒学白族传播
作者林庆,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云南昆明650031)。
一、汉晋时期:儒学初传,“学则开于汉”
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源远流长。有学者推断,儒学思想传到云南大理是司马迁南行讲学时传过来的,理由是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大理府王案山条载有“司马迁到此观西洱河”。民国《大理县志》卷三《建设部》云:
汉元封元年,中郎将司马迁奉使南略邛筰、昆明,立讲台于叶榆。《滇云历年传》:“滇云讲学之始,或日司马迁以武事西征,略涉滇境,何暇学问、谈经?且司马迁亦不系道学之人。旧《志》虽有司马讲台,恐属附会。故今《志》删之耳。窃以为不然,司马氏未仕时,亦曾讲业齐鲁,观孔子之遗风。今得位行政,怀远宣化,尤当施教于殊方,以被文德于无外。况昆明乃今丽江旧通安州地,自邛筰至昆明,必经叶榆,又先已有受经学赋如张、盛二子之产于是乡,此可一变至道之邦也。则其讲学之遗基,有令人低徊留之而不能去者,尚何疑其虚诞而削其迹乎?”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二载有“司马迁立讲堂于叶榆(今大理、洱源、剑川,治所在今喜洲),为滇云讲学之始”,由此认为司马迁的足迹到过昆明、大理等地。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传到大理是由于汉武帝为了统治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而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不断渗透的结果,也是大理与北方汉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而形成的文化相融现象。理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叶榆人盛览、张叔到四川若水(今四川西昌附近)学习汉学,“归教乡里”。另据天启《滇志》载:“大理府儒学,在府治南,汉章帝元和二年建。”《滇略》卷五《绩略》称:“相如至若水,叶(榆)人张叔、盛览等皆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该书卷六《献略》云:“同时有张叔者,天姿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余里。叔负笈往,从之受经,归以教乡人。”冯苏《滇考》卷下《滇南科目》称:“夫滇与闽、粤,皆开自汉武帝。其时盛览、张叔己从司马长卿学赋、受经。”乾隆《云南通志》卷七《学校》云:“滇南建学,肇自汉时。张、盛受业长卿,尹、许执经中土,滇之文风由此渐启。”该书卷二十一《人物》称:“览与张叔开迤西文章之始。”天启《滇志》卷十四《人物志之一》、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一之《人物》及《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七十八《大理府》亦持此说。著名诗人赵藩在《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其一中,也不无自豪地写道:“古诗之流厥有赋,赋家之心靡不赅。西汉辞章溯初祖,长通亲受马卿来。”明代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也在《大理府重修儒学置学田记》中写道:“学则开于汉,衍于蜀汉,闭于宋,复于元,盛于国朝(明)。”但是,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东汉章帝时蜀郡人王阜任益州太守才在滇池一带“始兴文学,渐迁其俗”。
总的说来,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在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叶榆等地属于“巴蜀西南外蛮夷”,该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汉文化程度较低,很难产生出像张叔、盛览这样的才学之士,因此盛览、张叔从司马相如受学说并不一定属实。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大理人对中原文化的倾慕和对儒家学说的高度认同,这既是大理人对西南地区早期士人在传播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深刻体认,更是对司马相如的文才及其开发西南夷历史功 绩的充分肯定。随着时间推移,大理乃至云南地区的汉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盛览、张叔从司马相如受学 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元明两代,大理乃至云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 关系空前紧密,文教事业日趋发达,汉化速度亦明显加快。我们认为,如果说大理地区“学开于汉”似 乎还嫌依据不足的话,那么从现存的文献看,早在8世纪初南诏境内就已经出现“崇儒”“立孔子庙” 的举措,则是儒学传入大理的不争史实。康熙《云南府志》卷二十一《艺文六》所录刘让《重修呈贡县 文庙记》云:“汉唐以来,学校罕闻。”范承勋《改建云南省城府县学宫碑记》云:“云南有学,始于汉章帝元和二年,其说存,其地未可深考。自汉以下,历时兴替,亦未有定所,迨元而建置始可考焉。至于有明,人文之盛竞于中土,咸日学校为之也。”应该说,这一说法比较符合云南文教发展实情。
二、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儒学兴盛,“蔼有华风”,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儒家思想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很盛行,并对后来大理地区的民族部落尤其是乌蛮和白蛮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南诏(649-902)初期,王室崇奉儒学,盛罗皮于玄宗先天元年(712)已“立孔子庙于国中”。另据史料载,李世民于贞观四年(630)诏令“各州、县皆立孔子庙”,今巍山文庙正建于其时。当时,蒙舍诏正积极主动依附唐王朝以求生存和发展,并得到了唐朝的封赠,唐朝诏令建文庙,盛逻皮自然遵从。可见南诏时期汉文化影响之深,儒学传播之广早在南诏统一洱海区域之前便己奠定基础。当时白蛮大姓已“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白蛮是南诏的主体民族,南诏文化实质上是白蛮文化,南诏的知识阶层主要出自白蛮大姓。根据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描述,在贞观年间,以杨、赵、李、董为代表的白蛮大姓汉文化水平己不低。《焚古通记浅述》称贞观二十年(646)细奴罗已“劝民间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南诏汉文化之高,由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可见一斑。碑文中有“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通三才而体制,用六府以经邦”之词句,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思想观念。该碑还记载,盛罗皮的孙子南诏王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尝学贤人之术”。他在进攻宿州时俘获西川西沪令郑回,因“重其悖儒”,遂让他“俾教子弟”,此举使异牟寻以后的王室儒学文化提高,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善待俘获读书人的善举,表明南诏王室对儒学和儒生的重视。
贞元十年(794)苍山会盟之后,南诏与唐王朝重归于好,从异牟寻时代(780-809)起,每年都要派遣大批大姓子弟到成都、长安学习儒学经典和汉文化,有的学习汉文经籍前后达五十多年,由此培养出许多精通儒学和汉文化的人才。史载:“国王更以重金,聘中原、江南、西川学识渊深、贤名远播者入滇讲学,并建太学监于叶榆城,为皇室子弟学所……蒙段两朝之治学与唐宋无异,皆以四书五经为仕者必知之书。”《报南诏坦卓假道书》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分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异牟寻在给唐使韦皋的信中特别强调南诏境内“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不能不说是南诏推行儒学的结果。当时白蛮大姓的赵叔达、杨奇鲲等人的诗作被广为传诵。
两宋大理国时期(937-1253),中原儒学文化对大理地区乃至云南的传输有所衰减,但影响进一步加深,大理地区进一步如饥似渴地吮吸中原文化,儒学和汉文化与大理地区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日益加强。这一时期大理国政权与两宋王朝的关系有这样的特点,即官方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大为减少,而民间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增加。大理国曾主动热切地希望发展与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关系,然而宋王朝因为政治、军事上积贫积弱,自感无力经营边疆,因而以自身安全为由,划大渡河为界,奉行“闭关锁国”,拒大理国抛出的橄榄枝于千里之外,人为地隔绝与大理国的关系,多次阻绝友好通使,此即《大观楼长联》所说的“宋挥玉斧”。此局面的出现,使得大理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往、传输衰减,从而难以及时得到和吸收中原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但交往的减少并不表明交往的中断,也不表明儒学在大理地区传播和影响的弱化。
有史料表明,大理国存在的300余年间,大理各族人民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此外,两宋王朝因频繁同北方的西夏、辽和金政权开战,因“关陕尽失,无法交易”,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宋王朝急需战马而难得,为了得到大理国的战马,曾经通过广西大量购买大理马。大理国商人也利用卖马之机,到广西采购中原文化用品和典籍,以补充通过官方渠道传入中原文化的不足。茶马互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对促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对推动大理国地方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垄断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利,以其所需茶叶换其所有的战马,以达到互通有无,方能保证宋朝所需的马源,又能达到控制诸蕃的目的,于是“茶马互市”制度应运而生。因此,历史上茶马互市对大理国政权及今天白族民风民俗形成的影响值得深入关注、探究,而宋人周去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岭外代答》中有“蛮马之来,他货亦至”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长期互市、交往中,儒学不断传入大理白族地区,内地和边疆白族等少数民族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儒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不同文化并行不悖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兼容
并尊、相互融合、交融的新文化格局,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 纳,不同的民族习俗、宗教被彼此尊重、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固有特点的文化和谐局面,而文化的和 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和,形成了各族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互相离不开的亲密关系,进而促成少数 民族地方政权归服中央、心向统一的民族大团结格局。受这种环境的熏陶,大理地区的白蛮最早改变 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经商和重视文化的习惯,白族商人的精明能干和汉文化水平之高,由此远近闻 名。儒家思想使大理国在316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安定的日子,给生活在这块肥沃土地的少数民族创造了永久和平与安宁,使古代大理地区长期保持着繁盛和国泰民安的生活景象。
三、元代时期:科举初开,“巍巍然有知经者”
对大理白族地区来说,儒学是一种不同于白族传统的外来的文化或哲学思想,要想为白族接受、传播、吸纳与融汇,儒学就必须与白族地区的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否则就会因水土不服而被抛弃。自从南诏、大理国时期以来,大理白族地区一直深受儒学和汉文化的影响,崇尚儒学之风日深。但在元代之前,整个大理乃至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仍带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受教育权被王室、清平官等贵族、官员垄断,教育只培养王室、官员世袭子弟,普通土民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但这不代表儒学思想与当时的普通民众隔绝。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宋孝宗乾道癸巳冬(1173)李观音得与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赴横山议市马,作有《与邕人书》。其辞有云:“古人云:‘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其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合,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儒学已为普通大理国人所熟悉和掌握,孔子的言语己成为他们日常为人处世的口头禅。这些卖马人言谈见识如此,可见当时大理儒学传播之_斑。
元代在云南地区大力提倡儒学。赛典赤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广建学校,从此学校教育和文庙联在一起,逐步废除佛寺教育,佛学与儒学分离,中原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悄然兴起,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了汉唐以来新的高潮,所谓“北人鳞集、爨焚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驵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设立学校,以弘既富而教之义。如爨焚(白)之类,巍巍然有知经者矣。”1276年,云南行中书省建立。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来滇主政,并决定先在中庆(今昆明)、大理二路开设学校,修建大理孔庙,今大理留存的《加封孔子圣诏碑》《大理路庙学碑》《大理文庙圣旨碑》等几通碑碣记载了当年儒学的兴盛局面。
元代大理儒学的设置,在客观上逾越了统治阶级狭隘的心理,大大提高了白族地区的汉文化水平,当时已有较多的白族文人、学士运用娴熟的汉文创作诗文、著作并通过了科举考试。据《新纂云南通志》统计,元代所设云南儒学教育机构仅分布在中庆路(今昆明)、大理等靠内地区;通观整个元代,云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仅6人,大理地区仅赵州苏隆1人。新近发现的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大理府卫州县历科进士题名记》碑云“元时亦有进士王楫、李进仁辈”,但因其事迹迄不见载录,故不知其详。元时出名的大理地区的学者除以上3人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知名外,还有“文章政事名于南诏”的王惠、王升父子和杨渊海(白族),他们熟读儒家经典,“正三纲,明五伦,教跪拜”,均是名垂千古的佼佼者,可见“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元时早已深入人心”。元代时期,通过大理儒学的设置和文人学士的科举选拔,客观上逾越了两宋时中原王朝统治阶级划河而治的狭隘心理,大大提高了大理白族地区的汉文化水平。
四、明清时期:精英辈出,“文教事兴,科第继起,蔼乎成弦诵之风”
至明代统治者为风化边夷大行儒学教化,大理地区出现了许多一应俱全的文庙,文庙附近设书院。当时最大的有大理、蒙化、鹤庆三府的文庙,其他各县均有相应的庙学,全省最著名的西云书院就是儒学流传的结晶。随着书院设置和科举选拔制度的推行,儒学在大理地区得以广泛、深入地传播,为大理地区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使儒学在明清之际的大理地区成为洋洋大观。明王朝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化政策主要表现在:建立地方儒学,优先照顾少数民族子弟入国子监,为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考开方便之门,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员额数予以照顾,最终使得儒学教育的范围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科考人数也快速增长,这是历代所没有的。以传播儒学为宗旨的各类书院、学校的兴起,始终未脱离“学而优则仕”的目的,由此大理科举之风大盛,尤以白族地区最为突出。正德《云南志》卷三“大理府风俗”日:“郡中汉、焚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盛他郡。”此后,白族地区修习儒学之风日盛一日,读书、求仕以光宗耀祖成为当时白族民众的普遍向往与追求,也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精英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元朝开始统一大理,那么明朝则全面征服和控制大理、以儒学教化大理,并极力推行汉文化,儒学随之长驱直入,在客观上使大理地区白族本土文化起了质的变化,实现了大理地区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可以说,明代是大理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明朝对云南的管理实行了变革,推行改土归流,废除了以前原有的由本民族进行统治的政策(土司制度),按中央统一边疆地区规划进行流官管理,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白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此时洱海地区出现了汉文化水平较高的白族精英群。明代大理崇儒之风更盛,表现有三,一是“宋明理学”兴旺,二为大量孔庙的修建,三为科举考试中进士人数大大增加。
明代理学在大理的盛行曾令当时的学界瞩目,白族人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星璀璨的局面。生于明初的大理下阳溪白族文人杨黼,虽然自诩“不理性命”,但专心注疏《孝经》,“读五经皆百遍”,“行仁义礼”,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新儒,他还创作了白语诗体《词寄山花》,“山花体”从此成为白语诗的通名。稍后的李元阳终身潜心于性命之学,写出哲学著作《心性图说》,李根源赞其为“理学巨儒”。李元阳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王畿、罗钦顺、罗洪先都有过很深的交往。巍山明代文人朱光霁则是明代理学泰斗王阳明的真传弟子。他在贵州王氏门下学成归滇时,王阳明特地写了《赠朱克明南归序》相送。明朝末年被当局授予“当代贤儒”的邓川州艾自新、艾自修兄弟,其理学名著《二艾遗书》是大理地区新儒学不可多得的遗产。总体而言,在元朝基础上建立的明王朝对大理白族地区的统治,是大理白族政治文化发展和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也是白族精英知识分子哲学思想凸显并得到外界学者认可的时期。在明王朝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统治政策并以儒学教化天下这一大背景下,大理白族地区的白族精英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加快了融入中原儒家文化的过程,表现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及为人处世的伦理观念日益儒学化,于是出现了刚正不阿、坚决捍卫儒家传统的李元阳“议大礼”而被贬事件。
然而同时,这些白族精英在强烈的长期的民族感情驱使下,本身固有的白族传统思想、文化基因并未因文化、经济、政治的融合过程而丧失,恰恰相反,其民族独特色顽强地表现出来,尤其到了明代中期,洱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汉文化水平较高的白族文学家群体,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大理古代文化推向了高峰,此举被人们誉为“文化盛世”,而李元阳、杨士云、吴懋、杨达之、梁佐、董难等白族精英正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是名动一时的知名人士。在杨慎带动下当时出现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学流派“杨门七子”(大理人杨士云、李元阳、吴懋,保山人张含,开远人王廷表,晋宁人唐锜,昆明人胡廷禄),他们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曾盛极一时,其诗文创作与学术成就是明代云南和大理地区文化繁荣与兴盛的见证,正所谓“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他们的著作、文章留传至今,众口皆碑,这与明代大理儒学的兴盛不无关系,他们的表现就是“宋明理学”的兴旺。这时的白族士人作为云南大理地区文化自觉者的代表,其政治心态经历了从明初的甘贫守节、不仕新朝(如名士杨黼、杨士云)到明中的心系黎民、积极进取(如杨南金、赵弼、张云鹏等),再到明后期的辞官归里、逃禅念佛(如李元阳、赵汝濂、朱飒等)的嬗变。
这些白族精英对儒学的推崇深刻影响了大理地区的教育发展。明代大理白族地区孔庙大量兴建、书院办学兴盛、文人辈出,在李元阳等大儒的带动下,白族民间读书习经风气逐渐形成,儒家文化对大理白族的影响持续深入。当时最大的孔庙有大理、蒙化、鹤庆三府的孔庙,其他各县均有相适应的庙学、书院。明洪武年间创建于大理城外西南的苍麓书院是现今有史可考的大理最早的书院,中进士前的李元阳就读于此,后杨慎来滇也常讲学于此。明代大理书院己发展到23所,清代时又有所发展,出现了弥渡中和书院、香山书院等,出现了全省最著名的大理西云书院,这些都是儒学在大理地区流传和兴盛的标志,一些文化名流常年讲学于此。史载一代名师、弥渡硕儒谷际岐主讲于昆明五华书院,“滇中名流大半出其门下”,深受时人敬仰;编著《滇系》的师范,参与编修《云南通志》的李彪主讲于大理西云书院、弥渡中和书院,并创建香山书院。他们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浓浓的墨迹。明清两朝大理地区科甲鼎盛、文人辈出,甚至出现了以张士铨为代表的科举家族(张士铨是清同治元年壬戌科进士,张氏一族,出了1位举人4位进士),大理市博物馆所珍藏的“科举题名记碑”就真实记录了明清两朝时大理地区科举考试的情况。据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共举行进士考试201科,云南仅有数次未参加考试。两代的会试和殿试,全国共取文进士51624人,云南籍(包括在云南的外省籍人士的后代)举子共有950X(明代257人,清代693人)中文进士。经细致统计、整理、划分,大体上可以认定这950个进士中大理府(今大理市由明清时期的太和县、赵州合并而成)中进士人数为153人,明代49人,清代104人。儒学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培育了杨南金、杨士云、李元阳、邹尧臣、赵汝濂、高封等一大批白族著名学者,对这些白族精英的文献记载资料,是研究明清时期大理白族地区文化教育状况及地方士人、科举考试的重要史料。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有意识地通过科举考试在白族地区陆续选拔接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白族文人,他们当中不乏闻名全滇的出类拔萃的精英。同时,这一时期,儒学对大理地区白族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影响更为深入。随着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和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哲学、村社生活、民族意识等的融合,一种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以村社和水系为纽带的开放而多元的民间宗教文化本主崇拜正式形成,进而逐渐成为白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本主崇拜中的这些内容与形式显然已区别于原始宗教,被打上了深深的儒学痕迹,表明儒学和本主崇拜实现了结合,从而深刻影响了大理地区的民风民俗。
总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两朝,是大理地区民族文学、哲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文人大批出现,有的甚至闻名全国,如段福、段光、杨黼、杨南金、李元阳、杨士云、何邦渐、陈佐才、王崧、师范、张端亮、赵藩、赵式铭等都闻名遐迩。大理白族地区这种宿儒群星璀璨的现象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实属罕见。如史学家和经学巨擘洱源白族文人王崧在乾嘉时代较有名气,作为少数民族的他被列为清人经学大师之一,这在全国来讲都是很少见的。又如赵藩,他在成都武侯祠撰写的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