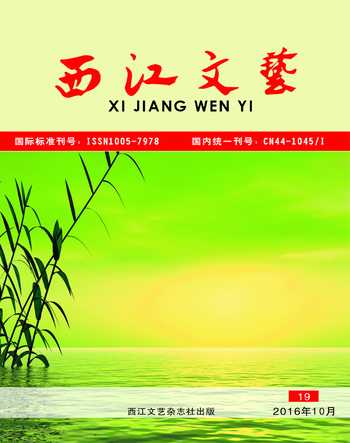音乐与生命哲学——来自酒神精神的启示
2016-05-30任治丹
任治丹
真正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活动。
——尼采
当代我们国家对于音乐美学问题的研究在不断的发展与探索中,翻开相关的学刊,登载着一篇又一篇的关于音乐美学理论的文章。可在读过之后,我们很少感到欣悦,刊物越来越多,而我们从中领悟到的却是越来越少了。
一提到音乐美学,便不能不涉及到哲学。音乐美学与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都达成了共识。2006年音乐美学专题笔会上学者牛龙菲更是斩钉截铁地说道:“音乐美学要如何有劲,一是哲学上的恶补;另一方面,乐养上要恶补。我们音乐美学家必须做到,第一,在哲学界我们可以跟第一流的哲学家对话,你的发言、文章就要把他们震了;在音乐技术理论方面就要能跟音乐家对话。不提到哲学,不提到乐养,音乐美学断无前途可言!”这段话说得多么痛快,强调了哲学是研究音乐美学的前提。可是对于全国范围内众多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之中有多少真正接受过哲学教育的启蒙,对哲学又有着怎样深度的理解呢?多数的学生缺乏基本的哲学素养,一遇到艰深难懂的音乐美学著作,看到充斥着半生不熟、未经消化的学术名词和概念,便对音乐美学、音乐哲学望而生畏,不敢问津。我们的学生贫于对哲学的认知,我们的美学研究呢,也仿佛从根本上缺少了什么,缺少的是灼见和胆识、缺少一针见血地切中问题的核心和要害的力度。令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一些堆积的数据、冷冰冰的教条和模棱两可的观点。以下是我在音乐美学刊物上随机抄来的一段:
音乐不可能表现和再现人类情感,音乐的美是一种特定种类的、“只属于音乐的美”,它是由音调及其艺术的组合方式所构成的。这个观点代表了典型的形式主义美学立场。我们如果真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想音乐与生活的关系,就一定会只进入音乐的审美趣味维度,或对音乐采取抽象理智的态度,而不能理解为何某些伟大的音乐作品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震撼与启发。
我们可以想想,究竟能从这样的表述中学到些什么呢?我们能獲取什么样的启示?这些故作艰深的陈述除了把我们的脑子搞混以外,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可以被拿来当作反面教材使用。只有非常迂腐的读者才会忍气吞声地读完这类文章。然而这正是目前许多音乐美学理论著作的风格。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从哲学最初的含义入手探讨哲学与音乐的联系以及最终得出的结论:音乐的最高点与哲学相通。
一、哲学是对人类最高问题永远的追问。哲学在古希腊语中原是“爱智慧”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爱智慧呢?智慧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被动的,静态的,智慧却是从人生深处焕发出来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也认为哲学源于惊奇,惊奇于浩瀚无垠的宇宙和渺不足道的个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类爱智慧正是出于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必定会有一个时刻,也许在某个夏夜,抬头仰望,突然发现了广阔无际的星空,一个巨大而朦胧的问题开始叩击他的头脑:世界是什么?[1]
哲学活动就是询问那超乎寻常的事物。[2]对世界本质的思考无可厚非地落在对空间和时间的思考上。先秦哲学家庄子在《秋水》中写道: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则寓言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然而其中河神和海神的比喻只是相对的,海虽然是无边无际的,然而这也只能在河面前逞威,要是拿宇宙,甚至用银河系来相比,大海又成为一个渺小的微粒。宇宙无穷无尽,银河系以外,还有其他无穷尽的星系,在这悬殊的比例对比之下,银河系又要退避三舍,在我们看来辽阔无垠的银河系在浩瀚的难以体会的宇宙中同样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不足七尺之躯的人,感受更是甚于望洋兴叹,沧海一粟。这才只是对空间的思考。然而时间更是不可思议,有史至今,已经是人生的千万倍,任凭我们是谁都无法去调查世界的开端。在世界的冷眼里,我们是目光短浅、不知春秋的蟪蛄。况且往后还有不可想象的未来。仰观世界之大、之久,哪一个真实的人不感到既惊且疑呢?这种对最广泛且最深刻最终极又最原始的问题的追问正是哲学上形而上的思考,也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可是如今许多研究音乐哲学或美学的学者却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否认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再过问哲学源自对最高问题究根问底的冲动,正如开始我提到的哲学的本义,倘若否定了终极追问,哲学就失去了真相,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哲学和音乐的姻缘
艺术与哲学原是一对双生的灵魂,他们相互追逐、糅合、碰撞出灿烂如火的灵光,是名副其实的佳偶。如果将他们拆散,各自将失去一半以上的光辉。哲学走近艺术,为艺术罩上永恒的神秘面纱。而艺术的灵性激起哲学轻盈优雅的舞步。真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相通的,他们是气质相似的人,不世故、不功利,怀着“无所为而为”的信念去从事艺术的事业,正如怀着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追问人类的最高问题,它看似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可往往就是这种不追求任何实用价值的精神,成就了艺术创作中最难得的品格,本着这样的态度,在艺术上做出的成就才可能是大成就。一切学术皆应如此,艺术更应是如此,而音乐作为掌管一切艺术的缪斯女神的最娇宠的小女儿,妖娆、妩媚,倍受青睐,被尼采称为“最具有哲学深度的艺术”,尼采更是不含糊地说,“一个人愈是音乐家,就愈是哲学家”。这并不意味音乐家必须掌握所有的哲学理论知识,而是是否拥有哲学家那股子“形而上学冲动”的气质。任何时代,人类对于宇宙的思考,都是音乐创作最可贵的主题。创作时给音乐注入深邃、深刻的生命哲学情感,令其闪烁着智慧的光华,这是令音乐达到最高境界最有力、最值得肯定的完成。
三、音乐中的“酒神”精神
酒神,产生于哲学和音樂结婚的蜜月。
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明音乐与哲学之间的联系。许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被某一段音乐深深震慑住时,我们的感受力奇迹般地有了张力,甚至会觉得麻头顶、竖汗毛、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说得再玄妙一点,就是神灵附体、猝然中箭的感觉,当然这样的体验非常稀少,毕竟这样的音乐作品太稀罕了。究其根源,却很难说清是什么因素赋予了音乐作品这样的质量。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用“酒神”解释了这一现象。尼采将艺术的风格分为阿波罗式的明亮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放,这两种风格在音乐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对于音乐中的酒神精神,尼采解释为这是一种个体获得了与天地宇宙相融合的快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巨大、激烈的快感,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尼采说,音乐中的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3],是一种迫使人进入一种情感的巅峰,进入一种狂喜或者痛苦或两者交织的癫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将人的体验升华到与宇宙万物浑然一体,作为“驱向放纵之魄力”[4]支配着人的意志。从以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酒神”精神并非一般的狂热情绪,而是一种具有哲学思考和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性情绪。
日神教人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它强调人生的美的外观,赞叹人生的喜悦,歌颂生活中积极乐观的一面,回避追究世界和人生背后的终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追求简单快乐的生活,而在尼采看来却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人生有其更深邃的一面,就是去探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而“酒神”正是拨开这层美丽的外衣攫取内在的意义,要解开这永恒的人生之谜。然而人生之谜是容不得追究的,人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与日神相比,“酒神”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因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尼采认为,悲剧可以带给人们快感,是因为它使人们获得了与世界本体相融合的感觉。“酒神”不愿浮在事物的表面,它要追溯本源,究其本源,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呢?因为音乐提供给我们一个美好世界的意向,象征着一种能够超脱尘世的事物,使我们相信会有超越于我们、比人类更伟大的精神存在,指引我们去思考,去不断追寻自己在这世界上存在的意义。音乐中最浓烈的成分,令听者深深震撼颤栗的某种东西,一定是拥有酒神精神。
音乐中是否包含酒神精神,就是看是否能将音乐的境界和宇宙人生的境界聯系起来。有人会疑惑,音乐就是音乐,一定要和宇宙和人生拉上关系吗?可是广义上的音乐不就有如人生,包含在宇宙中,包罗万象,有着广阔的天地吗?虽然这并不是要求音乐里一定要有包含宇宙时空的主题或题材,但说明的是应该具备这种宽广的意识和胸怀。然而,中国当代的许多作曲家或音乐美学家对于这种“酒神”精神是陌生的,我们的音乐中形而上的部分实在是太缺乏。许多音乐家还初步停留在“河伯”的层面,这样肤浅的音乐不能对听众的全生命发生敲击的力量,不能起到沁透的功效。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作曲家或每首音乐作品都包含“酒神”精神,就像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哲学家一样。这不是每个音乐家都能达到的境界,也不是每个音乐家愿意达到的境界,许多人觉得不需要达到这种境界。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音乐家,他的心怀无所不容,他的所思所想绝不停留在一世一代,不停留在眼前的事物上。到这一阶段,他同时具备了哲学家的情怀,他所理解和创作的作品,有形而上的修养和品德做背景,这才能够得着大音乐家的位置。当然,当代社会也不乏拥有异常天赋,才思焕发的音乐学者,追求音乐完全是自身浓厚的兴趣使然,绝非急功近利之辈,这种精神固然可贵,但如果缺乏酒神精神的底蕴,不能够深入一个独特的深层世界,即使刚开始有所创造,长期以后,便无以为继,难以有音乐精神与风格上的大突破,难以使音乐具有立体感、厚重感,深沉感。所以学音乐的人,在掌握了一定技能之后,必须进而体会“哲学的”“形而上的”“酒神精神”的高度,以求音乐方面的进步。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四、三种境界
人的三种境界 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根据这三种生活把人的特性分为兽性、人性和神性三种级别。“人生”就是饱含这样深意的三层楼。住在第一层的人,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人生的意义不过求个温饱,有些人但求工作一天,获得三餐一觉,已经感天谢地,对人生再无其他奢望。食色性欲是每一个人正常的需要,只要吃得着东西就吃,而不管其他的道理,然而吃饭穿衣都是用下等感觉,是无条件的,人以外的动物都是如此。物质丰厚的人更求锦衣玉食,雍容富贵,但还是不能超越物质追求的范围,终究难脱人生最低层,这也体现为人的兽性。抱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乐于或有力走楼梯的,就想爬到二层楼去看看,或者久居在里头,除了物质生活,他们还重视精神生活,专心致力于学术、文艺、美感等研究,他们把剩余的精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心思寄托于文艺的创作与欣赏,这正体现为人的“人性”,同样身为人,可其间的差别却大得惊人。人是不应该苟同于动物的,人身上应兼备求知性和道德性,除了强壮的体格以外,心理方面真善美的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要“怡情养性”,才无愧于人被号称为“万物之灵”的称号。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得比例少,但绝对量还是很大的。再往上走,只有极少数的人高居在第三层,他们的“人生欲”很强,物质欲和精神欲都不能满足他们,在他们看来,物质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文艺学术只是暂时的美景,他们把眼光投在了更远地追究灵魂的根本,探索宇宙的秘密,他们追求的,正是人类精神永恒的,唯独这样才能真切体验到人生的意义。他们的人格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质量,到这一层,人的周身已经被笼罩上一层崇高而神圣的光环,到达一种“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境界,这乃是人的崇高境界,充满着神性。然而高处不胜寒,他们的观念往往因为缺少实用性和不易被理解而不断遭受漠视甚至排斥。
文学的三种境界 王国维于知命之年,创造了文学的三种境界——诗人境界、学人境界、真人境界。诗人境界,平仄对仗合乎文字运用的规章法度,对于什么都能言中有物,都能成诗,但却没什么精彩,更没有什么独创。学人境界则更进一步,经过深入的揣摩,对于各种文体都有所涉猎,然后荟萃各时期各大家的长处,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体系,写出的作品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然而到这一步,却仍旧不能脱离“匠”的范围,因为,这还属于人工所能及之事,任何人只要功夫成熟,自然就达到了。而到了真人境界,不但文学修养成熟了,而且胸襟学问也日趋成熟,成熟的文学修养与成熟的胸襟学问融为一体,文字间不仅可以见出驯熟的手腕,更能表现高超的人格,哲学宗教的意蕴。这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即是否有意识将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体现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来。这种境界,实际并不好理解,许多人滞留于第一境界,不曾超越。第一種境界——诗人境界,乃常人之境界。这完全在凡间的。而第二、第三种境界逐渐脱离凡间,当为王国维所说半超越与超越。所谓真人之境界,应当为无人境界。这才是文学的极境。
音乐的三种境界 音乐的三种境界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艺术的三种境界,叔本华用天文生动地将此分为流星、行星和恒星三个等级。流星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当我们仰视而惊呼“快看!”,它们在转身间就消逝了,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作品不外乎所谓当下流行的小调,崇尚一些低级的浪漫主义,表现廉价空虚的感情,贫血的梦想,这一类作品只顾发泄一时的情绪,无法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一旦时尚的烟雾散去,它们的生命便化为灰烬,万劫不复。第二等级的行星当然比流星耐久得多,离我们的视线较近,光芒很容易到达我们的眼睛,亮度更似胜过恒星,很多人认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行星所思所想从不超越一世一代,更何况其光辉往往借自他人,所产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不久后必然消逝。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作品过分地重视政治性和时代性,符合“当前之用”“当世之用”,看重眼前的现实,它们的生命力只够生长在当前,等到时过境迁,只能沦为历史的一个小注脚,附带的社会意义也会褪尽光彩,烟消云散。在通常情况下,最富于“时代性”的作品,往往也最容易过时,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这类作品的意义,一个知名作曲家在有生之年的作品中如果没有爱国忧国的情怀、没有涉及到当代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题材,是难以自解的,作曲家应该有此使命感。关键是能否将时代的题材接通永恒的真理,既有迫切的时代感,又有普遍的真理性。然而这是处在第二层中的作曲家难以达到的。能达到的只有极为罕见的少数的第三等级。只有第三等级的恒星是恒久不变的,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都保持着相同的影响,他们属于全宇宙,他们的精神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有限的肉体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然而恒星太高了,往往他们的光辉很久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视线。这样的作品才是垂之不朽的,才能成为音乐文明中灿烂永恒的瑰宝。绝对不依靠占取时尚或社会的丝毫优势,只有靠本身内在的价值,赤裸裸地去面对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综上所述,無论是人、文学、还是音乐,到了最高点,他们必定是共同带上了“形而上”的色彩,具备了一种哲学的修养,也就是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在茫茫的宇宙间,当万籁俱静,万象喧嚣渐渐沉寂,真正引领我们上升的,是贝多芬的《命运》,或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它们以永恒的姿态伫立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令一切靡靡之音湮沒无闻。
注释:
[1]周国平《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无用之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德]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
[3]《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第10节。
[4]《强力意志》,第798节。
参考文献:
[1][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赵鑫珊《贝多芬之魂》,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