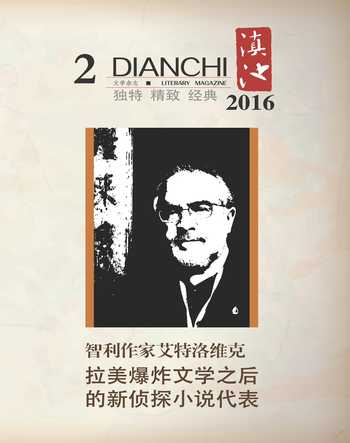乌崩村书
2016-05-30邓学品叶青
邓学品 叶青
早年,读到著名诗人臧克家的《三代》:孩子 /在土里洗澡;爸爸 /在土里流汗;爷爷 /在土里埋葬。身为世袭的农家之子,当时,会以为自己也将成为诗中三代人其中的一代,在土里洗过澡,流过汗后,最后安眠于村后长满松树、麻栗树的山上的两尺红土里。
那时,站在家门前,面对经年耕种过的熟地肥土,每个农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和来生。
在那样每年均由农历二十四节气划分得一目了然的岁月,人们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井闾相错,婚姻相通,任恤相感,庆吊往来。人们安身立命,一代代繁衍生息。一个人往往一落生,就与蚂蚁、鱼虾、猫狗等众多生灵结下缘分;一学会走路,就见习农耕。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五谷六畜,风霜雪雨,将伴随他或她一生。
当然也有血泪、辛酸、屈辱,生离死别,也有乱世,瘟疫、灾害,但如麻雀、野草,以数量取胜的农人,世代连绵,让那片土地呈现出抱朴守真、师法自然的底色。
我们,从何时起,开始愚蠢地隔绝大地仁慈的地气滋养?
2013年暮春,接到弥勒市巡检司镇乌崩村委会的邀请,去给该村编写一本村志,笔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熊培云所著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贩奴船》一节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
苇岸在《鸟的建筑》里,也曾这样写过:“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性的变迁。”
这样的哀挽心祭,早已属于平坝乡野那些在城市的疯狂的铁蹄追赶下,落荒而逃的村庄,而暂时不属于离县城 80多公里、至今仍被自然山水养护的乌崩和乌崩一样的山村。
多年前,笔者就曾无数次走进重重大山包围的巡检司镇彝族阿哲人居住的龙树村。
那是星落棋布于滇南那片红色的热土上无数山村中的一个,她小巧玲珑地藏在离滚滚南盘江 (弥勒段 )十余公里的群山中。村里有 70多户阿哲人家,380多个男女老少,护卫和耕管着几大山坡绿林几百片山地几十亩梯田。家家房前屋后大棵小棵的果树和杂木树上,时常落下密集的鸟语,人从下面经过,就像盛夏洒下滴滴雨水的清凉;十数个长年或季节性的水潭,和这里大大小小的屋舍一起依山而布,鲜活的清泉,使这个小村常年润泽秀美,潭边的水田,亭亭玉立着干净清纯的白荷红荷;村前一条小溪四季歌着舞着,像一位青春期的阿哲少女在蹦蹦跳跳地赶赴一个幸福的约会。在山外平坝间已彻底淡出的乌鸦和老鹰,不时云一样无声无息地掠过村对面的林子低空,似在寻找它们遗失在大地上的什么珍宝。而一种黑头的鸟高叫着明白如话的“老倌好过”,从这座山林飞向那山林,叫一声换一个地方,乐此不疲。曾有村人爬上高山顶上的大树梢上,以鸟的视角俯视龙树村,发现她像一张碧绿的荷叶,水潭是上面晶莹的露珠,风吹来,有一种波光潋滟的动感。
8月,正是这儿最美好的时节。苞谷在雨水灌透的土里集体拔节,一天到晚响着噼噼啪啪的声音,像是地里的蟋蟀们在欢度什么节日即兴演奏的乐曲。梯田里的稻谷也在忙着灌浆,成群结队的麻雀一天十几次起落于其间,稻田不设防,连稻草人也没有一个,所以麻雀的举止十分从容。牛群和羊群被多汁的山草喂得滚瓜溜圆。白天我看见放牧的女人,随便摘下一枚树叶,就吹出一支支树叶一样朴素和清新的歌(有树叶,她就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莫名其妙地寂寞。山外那些百欲塞心的人能到这里听一听,该有多好)。晚上主人待客的饭桌上,蜂蛹、鲫鱼、腊肉、火烧辣子、小嫩瓜、萝卜菜、颇具风味的“鸡血丸”、三四种蘑菇,还有土产的苞谷酒,把一张阔大的椿木桌摆得满满当当的。而一只竹制的水烟筒也不闲着,被男人一双双带汗的大手传来传去。蜂蛹是从高高的松树上或从厚厚的土层里烧来的。葫芦蜂的巢筑在树枝上,土甲蜂的巢却深藏在泥土里。放牛牧马时,人们一天天眼睁睁地看着葫芦蜂的巢由拳头大长成脸盆大甚至磨盘大,就知道土甲蜂也长得差不多了,于是夜里就燃起火把,用火赶走老蜂,从高高的树枝或深深的土层里取下挤满蜂蛹的蜂盘;而鱼是从山溪里获得的,不用网捕,不用钩钓,不用手捉,而是用竹箭射。
弥勒的摄影家普佳勇家就是龙树村人。有一年,笔者到他家坐客。到那里的时候,已是繁星满天,普家摆上丰盛的饭菜,我们吃着喝着,他忽然放下手中的酒碗,说:“走,再去添道菜!”边说边从门后取下一张弓,又从一支淘空的牛角里抽出七八只一米多长的竹箭。龙树地处偏僻的山村,村前村后都是密密的林子。我们以为他要去射杀野物,连忙拦住他,说,“算了,你是记者,不知道保护野生动物?”他“嘿嘿”笑了,还是他妻子搭话说:“他要带你们去射鱼。”“射鱼?”我们带着一脑子的疑惑,跟他出了家门。
他一手操弓,一手擎着用当地俗称“刷绿刺”(一种荆棘)做的火把,领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村街。很快,我们就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不到两米宽,一米多深,清澈见底,溪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一路欢歌。山村的夜真美:水灵灵的蛙声此起彼伏,点点桔黄的萤火在我们的四周飘忽,溪边梯田里的稻子快要成熟了,散发着缕缕清香。沿溪边走不多远,鞋袜就被草上的露水打湿了。普佳勇忽然用手示意止步。他一指小溪的一个转弯处,只见三条手掌大小的鲫鱼正浮在水中央,在火光的映照下一动不动。他张弓搭箭,说时迟,那时快,竹箭射出,带着风声,“嗖”的一下正中鱼腰。中箭的鱼在水中忽东忽西不断折腾,血把身边的水都染红了。普佳勇上前一把抓住箭身往下一按,随即提起,一条金黄色的草鱼便到手了。那夜,我们走了不到三百米,他就用竹箭射了五条鱼。
吃着鱼时,普佳勇才说,村下的山溪是长流水,每年雨季,大雨把山上一些虫蚁、牲畜粪便冲下山溪,成了上好的鱼食,因而这里的鱼长得很快。多年前,阿哲人大多是狩猎的好手。而山溪弯弯曲曲,深深浅浅,用网捕不方便,钓又费工费时,这一带的阿哲人就重操旧艺——试着用竹箭射鱼,白天不行,鱼一见人就躲起来了。夜里鱼睡大觉,下手还真管用。我问他,溪里会有那么多的鱼?他答:“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只有来客时才射鱼待客。”
听着这些趣事,酒就下得特别快,饭也吃得特别饱,吃饱喝足,天就黑严实了。这时有舞曲从村中心飘来,竟是山外刚刚流行的。寻声走去,但见一间百年土屋的木楼上彩灯闪烁人影绰约,细瞅,只见男女老少皆舞,大家汗淋淋的,笑呵呵的,砍柴的脚板、牧牛的脚板、背草运肥的脚板、犁地的脚板、扛石头的脚板、撵狐狸的脚板,把厚厚的松木板跺得震天价响,使轻柔的舞曲融进一种明快和力量。
而走近另一个阿哲人居住的小村高甸,让人像读到一部史诗一样生发久违的激动。无边的森林郁郁葱葱,依山排列而又错落有致的土掌房披着岁月的风尘:绿色的苔藓。村头的石辗静静地睡着,走进了似能闻到成熟庄稼和泥土的气息。打场的连枷和收割的镰刀在屋檐下看着日渐逼进的收获。虽说已是晚秋,但山寒使庄稼较山外推迟一至二个节令成熟。8个水塘,仿佛阿哲姑娘手捧的镜子一样明净,一座座深绿的山,就映照在这潭潭碧玉上,在正当中,像一幅拼花图案的主题一样,坐落着 100多户、500多人的彝村下高甸。在山外已难得一见的皂角,在这里还依然披挂着她那犹如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扭曲的镰刀一样的果实,山风中发出密集的声响。一株株树上叶子正由黄过度到红,由青过度到甜蜜。一只只羽毛朴素的鸡在安静地寻食。家家房前屋后都码着小山般的柴堆,整整齐齐,显出山里人过日子的仔细。这里称得上地广人稀,但阿哲人惜土如金。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林子、庄稼、房屋和水。有的人家连土墙墙面也不放过,在上面漫不经心用牛粪一糊,就成了蜜蜂的家园和生产甜蜜的作坊。而在离村一里多路狮子山的石壁则被阿哲先人当作大画板:随手刻划下在当时也许是通用的象形文字,太阳、月亮,奇形怪状的人和物。村里人一再对我们说,谁能破译,他就能找到价值连城的珍宝;而不远处的玄武洞,也忠实地保守着许多今人不可知的秘密。一大座浑圆的山,在顶部出人意料地陷下去篮球场那么大一块,里面长满了松树和其它杂木。里面有一个足够 100人开会的大厅,据说当年曾有抗战的英雄在此养精蓄锐。现在只有一位古代装束、相貌高古的老者正悠然地骑着一条大蛇,不知将漫游到哪里。人在里面呆久了,就恍如远离人间。这还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早年,蒋介石的参议长姜绍鹤,就住这里,现在办事处和完小,就在姜的大开大合的府邸,如今的残壁断墙,仍掩不住过去的豪富。
之所以将这些文字抄录在这里,是想说明我们对这方水土的最初的感知。同为彝族阿哲同胞居住的地方,乌崩肯定大致会有龙树村一样的情形。
2013年 5月的一天,我们从城里前往乌崩采访。关于村名“乌崩”,《弥勒县地名志》是这样解释的:“乌崩”,彝语意译为“乌为脚或下边;崩为旁边。乌崩即山脚旁边的村子。而在当地的传说中,乌崩因有五块风水宝地,把这些风水宝地的位置用线条连接在图画上,其形状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乌鸦,因此得名“乌崩”。彝族阿哲人崇尚黑色,他们秉承古老传说文化以乌鸦为吉祥物,乌鸦反哺在民间传唱,乌鸦喝水在民间流传,乌鸦能“看尽人间不平事,洞悉红尘龌龊人”。所以,在阿哲人的心目中,乌鸦是孤独而勇敢的自由象征。在乌崩的纵深山岭处,五座突兀的山巅,还真像一只展翅欲飞的乌鸦。
那天,我们的车穿过五山乡满山满山的直杆桉,一进入巡检司镇辖区,总算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云南松、大青树及滇南土著的灌木。我们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工匠,用专业的眼睛打量着一切,用敏感的心捕捉着一切:花朵、土地、道路、阳光和村落的主人。
在乌崩村委会,尽管久旱无雨,但大山多,仍葱葱郁郁;尤其是山谷底部,数十米高的青松比比皆是。据介绍,地处南盘江河谷地带的乌崩也是当地攀枝花树最多的地区,全村委会 9个村民小组有攀枝花 1200多棵,房前屋后,田头地角,不时能见到火红的攀枝花开如火。攀枝花树与世居的彝族阿哲人的生活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花不但可以吃,成棉后是做枕头的上好原料;粗大的树干做成甑子,蒸出的饭远比用其它炊具要香。在这里,闻到了久违的土地的芳香,它是如此之浓,之鲜。而在城市,充盈我们肺腑的是汽油味,脂粉味,更多的是铜臭气。是的,在喧杂之上,应该有这么一片净土,清洁我们的精神。
生态可以没有人类,而我们的快乐和幸福须臾离不开良好的生态。
多年前,乌崩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每一坐山都是绿色的,遍山都是云南松,村里长满了高大的椿树、黄羊木、万年青、黄粟树、野椿树、酸浆树、核桃树、梨、柿、李、杏等等,浓荫蔽日 ,村边四围环绕着挺拔的栎树和松树,护村林、神树林、密枝林,古树苍天。大条小条的溪涧一年四季清流潺潺。现在由于一些地方砍伐过度,再加上连年干旱,好多山都露出了红土,溪流、池塘大多干了。以前山间豺狼虎豹众多,野鸡三五成群,唤伴觅食;林间麂子、野猪成批成群,至于松鸡、班鸠、黑头翁、黄鹂鸟、松鼠、野鸡、狐狸、大黑蛇、乌梢蛇、青蛇、麻蛇、绿蛇、青竹蛇、蜈蚣、穿山甲、蛤蚧等,它们与村民早不见晚见。龙潭、山溪,一年四季流水不断,有的村寨人家种的稻谷吃不完,还可出售大米。山林里还盛产鸡枞、摆衣帽、青头菌、牛肝菌、谷黄菌、扫帚菌、香菌、鸡油菌、冻菌、铜绿菌、火筒菌、土馒头、荞面菌、松毛菌、奶浆菌、干巴菌、老人头、松茸、树花、黑木耳、白木耳、灵芝、细木耳、青苔、地卷皮等上百种美味山珍。
这里还是鲜花的世界:玉荷花、棠梨花、小酸花、老白花、苦刺花、棕花、红花、板兰花、火草花、野麻花、柴花、石花、金银花、老鸦花等几十种。其中不少花可直接烹调食用。四季花事装点着朴素的大山。有花当然就有果。多依、鸡嗉子、棠梨果、桃子、梅子、山楂果、山樱桃、软枣、李子、杏子、花红、枣子、柿子、红果、黑果、杨梅、芭蕉、橄榄、火把果、黄泡、黑泡、红泡、紫泡、椎栗果、地石榴,各种草莓、麻栗果、松子、核桃、板栗、刺栗等干鲜果会因时节挂满枝头。这些果实,使彝山的日子变得香甜如蜜。记得有人说过,生态有自己的逻辑,它体现了自然法则的节律与和谐。生态呈现的是自然的动态之美。生态显示的是蓬勃的本能和生命的律动。生态里藏匿着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生态里藏匿着动物、草木、菌类和许许多多微小的生命;生态里藏匿着灵感、激情、思想和信仰;生态里藏匿着定理、法则、传奇和故事。行走在乌崩,我们对这种看法更加心悦诚服。
由于早年为兴建房屋和烘烤烟滥砍滥伐,这里的植被破坏严重,许多溪泉断流,只要少雨的年份,便造成干旱,我们所到之处,山风一起或是车轮辗过,道路总是红尘飞扬,地里的庄稼,被晒得无精打采,猫狗鸡都躲在大树下或屋檐下。很多水田都无法栽种水稻,只好改种烤烟或包谷。至于“雷响田”,更是指望不上了,大多农户只好卖了包谷、烤烟,买米吃了。
当我们几个月后又到这里采访,在大寨村,看到有一户人家在屋顶育好的秧苗因雨水太少无法移栽,像一片秋草样,稀稀拉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绿林中,不时能看到松针发黄的云南松。村委会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全村有 2000多棵云南松都干死了。后来问到这几年的经济收入,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直摇头,天太干了,收入不值一提。为此,有的村民还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者有夫妻,有母子,有兄弟姐妹,有的人家一把锁锁了大门,举家外出打工。牛厩房村民小组 38岁的护林员薜文彪,妻子张哨珍带着 17岁的大儿子薜梅贵到深圳打工,留下他与 78岁的老母亲李凤仙和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薜金润。他每星期与妻子儿子通一次电话。问起他的收入时,他说:“天老是干,没有办法,再干三年,怕是在不住了,光靠我干护林员一月几百块钱,还不够开支,为了供孩子读书,为了生活,我只有让媳妇到深圳打工了。”有人说,这个猛汉子每晚因想媳妇睡不着觉,大冷的天,也会把自己脱个一丝不挂,从水窖里打水从头到脚猛浇。
同样由于大旱,拥有广袤土地的乌崩要吃点新鲜菜都不容易,但这给虹溪镇一对夫妇带来了商机。这对年轻的夫妇从山外采购了肉食菜蔬,用小货车拉了,走村串寨叫卖。采访期间的一天,村委会召集小组干部,指导他们做好扩面新增农村低保相关表格的填写,当晚办了伙食。小货车开来了。我们看到,车上拉的货色还真多:菜蔬类有白菜、青菜、番茄、大葱、生姜、青辣椒等,肉类有猪肉、牛肉,还有用水箱养着的大江鳅、草鱼、活鸡,此外,还有香蕉、苹果等。当然,白酒更是少不了,都用大塑料桶装着。
当然,小夫妇的生意也有竞争者:盘溪一位体重 120公斤的壮汉,骑一张大摩托,载着煮好的猪血、卤猪头猪脚,还有豆腐等,每天下午就在村里叫卖。他真的是声若洪钟,站在村头一声吼,连在山地里干活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还是有自己的市场:猪血三元一大碗,人家连佐料都给你备好了。还有另一个人也曾开车送货上门,但后来大家都不买他的东西,原因是,他不讲卫生,往往车门一开,苍蝇随着一股怪味就会扑鼻而来。
初夏我们第一次到乌崩,从五山进村里,久旱无雨,按理路况不会太差,但村路羊肠般狭长,左弯右拐,我们乘坐的越野车的底盘不时重重地与密布在道路中间的乱石土包摩擦,让人心痛。几里路,车“爬行”般走了差不多两小时。后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所到村小组和相连道路,很少有水泥硬化过的,连毛石路也不多见,大多是土路。雨天,人踩牛踏车辗,到处泥泞,简直无从下脚;晴天,却尘土弥漫。
7月末的几场阵雨,大大缓解了彝山的旱情。我们吃过饭,从五山赶往乌崩。走进大山深处,山风冷凉,一派雨意,满山遍野的绿绸绿缎在风中起伏摇曳,空气清新得像刚出水的尖尖小荷。但道路泥泞不堪,车子行驶在林间山路上,就像大象走钢丝,让人提心吊胆。怪不得村“两委”领导张口闭口都在议论修路的事。
但山村的夜景却让我们开了眼界。路上,有人忽然手指着前车窗惊呼起来:“这是什么?”一看,在车灯的映照下,一道一米多长的白光在车头前一闪而过,快得如同雷电。坐在前排的张光友主任见怪不怪地对我们说:“你们看到的是‘夜鸹子,我们本地人叫它“地恨呼”,白天睡大觉,晚上出来捉蚊虫。”一起采访的普佳勇是当地人,他向我们说了好多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鸟类,什么晚上会学孩子大哭大叫的鸟 ,爱在行路的马帮后高叫着“走走走”的赶马雀,还有一种鸟,站起来差不多有人高,却没有半斤肉。
呆在这里的时间越长,让人想得越多的是“农耕”。
有史为证,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对土地的坚守。翻开《史记》第十卷《孝文本纪》,读到汉文帝刘恒的一句话:“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觉得一定要亲自耕作,打出粮食并且用来祭祀,才对得起土地神明和黎民百姓。他说到做到,一做十年,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十年后他又说了一段话:“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想起在一座山岗上的看到的事:一株桃树下,一只刚出生的小羊在认真地寻食,一朵桃花在风中落下,把它吓了一跳。一只老羊却从容地走近,一口衔起落花,有滋有味地咀嚼,等又一朵落花下来时,小羊急步上前,抢食桃花了。桃树下,一位闭目养神的老人被我们的脚步声惊醒。攀谈中他告诉我们,这里离城区虽不过几十公里路,但一年他只上三五次街。他说,城里有什么好,光是人和车,挤得要命,冬天也是一身的汗。人挤人远没有人挤树和石头有意思。在不远处,几头牛在吃草,嘴巴被草汁染得绿汪汪的。老人说,守着牛也比守着人好。就是老人这样的淳朴和生气,散布在整个大地上,才使乡村简单纯洁而饶有诗意。梭罗说:“我步入丛林,是因为我想从容不迫的生活,仅仅面对生命中最基本的事,看看我是否掌握了生命的教诲,而不是,在我临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老人肯定没有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但他无意中做到了。
采访中,尽管那几天时雨时晴,使一条条红线似的山道泥泞不堪,但大家的兴致很高。夏天的乌崩,是最富丽最美满的季节:绿树、青草、野花爬满了一个又一个山坡。清风过处,彩浪滚滚,阵阵清芳沁人心腑。散落其间的牛群羊群马群,幸福地啃食着被今夏旺盛的雨水和过剩的光照催肥的青草和杂木,身披棕衣、衣着朴素的牧人像一位位行吟的诗人,偶尔一展歌喉,使我们听到了一种别样的歌唱。那歌词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让我们闻到了青草和野花的气息,那曲调因悠长而让我们进入一种无限,让人进入一种梦境。一片一片的土地,人们在采烟叶、摘小米辣。我们看到最美的当数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朴实健壮的小伙,美丽沉静的少女,满脸刻划着岁月沧桑的老者,就像那画卷般美好的山野一样,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报以满怀的敬意与祝福,同时他们回赠我们已经久违的心灵折射的恬静,尽管就如我们不打听满山野花的芳名,我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责任编辑 李泉松